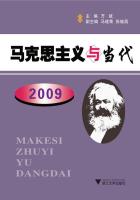老子的《道德经》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老子那里,“道”玄妙之玄妙、深奥之深奥,是开启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一切奥妙变化的门道。正因为宇宙之道为人的心性开启了一个具有超越性、创生性、无限性的“众妙之门”,人就应然与宇宙之道保持密切的关联并时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始终怀抱着对自然神圣的敬畏之心。因为无极衍化、生生不息的创生精神是宇宙之道最基本的属性,所以“道性同构”范式就理应要求人的实践活动要尽量按照有助于衍化创生的自然精神而循理举事;又因为人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其生命运动能量是有限的,所以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安身立命的角度出发来对生存境界的思考和行动。
从总体上说,老子生态美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与无为,即诠释一体万化的宇宙之道和无为和合的人类之德,而道与德的终极旨归是“生生”的自然法则;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的核心则为齐物与逍遥,即阐述万物平等的理念和游心太玄的理想,齐物是庄学的理论基石,逍遥是庄学的超然境界。基于此,构筑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范式,应充分彰显自然、无为、平等、自由的特性。
一、自然:一体万化之道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生态哲学与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精神,它既是对天地万物本然状态、通常状态和理想状态的一种肯认,更是一种价值判断与生命的守护。在老子那里,相当于西方“自然界”概念的“自然”是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关系,且此关系可以和合于“天道”。自然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宇宙之道,效法自然并作为自然精神的气象以无极衍化为宗旨、空寂独立为特性、安时处顺为价值观和大象无形为存在方式贯通于整个宇宙时空之中,以显示其一体万化的生生之德;而人类同样要效法自然并依照宇宙之道,以无为创生为天职、持一守中为德性、循理举事为行为准则和上善若水为最高品性参与自然万物和合共生的衍化过程之中,以显示人性的生生之美。老子认为,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至美的德性是师法自然衍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正是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才能体悟与通达自然一体万化、万物和合共生、生命永续衍化的大美境界。
老庄认为,“天道”作为一种既超然又实在的“万物之母”,为自然万物和人类共同分享。人与万物同源于自然,因而在德性和美感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来自对自然的直观审美和对神圣的自然精神充满敬仰之情的心性体验,这是一种渗透进人的心灵深处的类似宗教信仰的生态情怀。自然之“道”与人类之“德”通过审美而接通,这就意味着人的道德心性与万物所固有的生命天性有一个共同的自然来源,顺应自然之道与依照人类之德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因而也必然是统一的,自然而然的宇宙精神同时就是无为而为的人类品性,宇宙之道与人类之德也同样在“自然”这个形而上的境域里通过审美而获得了沟通,从而克服了传统生态哲学与美学将自然理解为“一体二分”导致人类与万物相斗争、价值准则相对立、审美观念相分离的学理悖论。老子“道”的一体万化的宇宙生成观表明,生态哲学与美学应然也必然要将尚且停留在知识层面的生态理论提升为一种精神的形而上境界,并形成“道性同构”的生态审美存在范式。范式的构筑无法脱离人类的生存意识,但人需要尊重自然万物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微生物的生存与审美的话语权,用包容与谦逊的心态聆听来自无限广阔的生命世界应有的言说,通过置身完美生命世界的参与和体验来确立正确的生存与审美的价值观。
在老子生态美学思想中,“自然”有着最明了也最深邃的含义,即生生之道、生生之德和生生之美,禀赋着自然精神的生存意识与审美情怀正是对“生”的认同与赞许,它表明了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先哲对于生命最深切的关注与眷恋。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在强调事物的“自然”天性之美外,进一步把自然与追求精神解脱的人生智慧联系起来,自然成为在乱世中安顿人生的终极价值依托。受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诗人与艺术家把自然作为一种朴真自由的生命境界,一种逃避世俗束缚而安置心性的家园,一种寄托精神抒发情感的世界,这是对自然之美禀赋了灵性的理解与拟人化的神交。总之,老庄生态美学关注与思考的并不是现代自然科学视野中的自然问题,而是如何在动荡烦躁的现实中保全脆弱的生命和短暂的人生中充分体验生存乐趣的问题,是一种审美生存的终极问题。老庄为有限人生寻找可以通达无限境界的审美路径和价值根基,正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自然世界与人类境界不期而遇,“天道”与“人性”归于同构。
在老子看来,人类要安身立命,“人性”就要效法永恒存在的宇宙之道,即“法自然”。老子讲“道法自然”,其实是在强调人法自然,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心性配合宇宙之道。老子对“人性”效法“天道”的论述,不仅仅是为了颂扬宇宙之道无极衍化的自然之美,更重要的是在倡导“人性”无为创生的德性之美,这才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深层次的哲学价值和审美意义。
二、无为:生生不息之德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是以至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自然现象和无为则无败、无执则无失的因果关系中,得到了“无为”生存之道和审美之维的启迪。在老子看来,正是因为“道”的“无为”之美才使宇宙亘古常新,自然万物各自顺应天道生存而衍化出生机蓬勃的大美气象;也正是因为人的“无为”之美才有可能通过直观自然而体悟宇宙之道美的内涵,通过涵养自然精神而修养和提升“人性”之美,从而臻及“诗意栖居”的人生至美境界。
在老子生态美学思想中,“自然”意味着“生”,自然之道则“生生之道”,自然之德则“生生之德”,自然之美则“生生之美”。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他认为:“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天道则生生之道,顺天道者则生。人只能顺应自然,人道只能以天道为准则,人的实践活动不能违背“天道”,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根基和审美的空间。庄子发展了老子以“无为”为基础的“生生”哲学思想,提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庄子·至乐》)的论述,认为“无为”是天、地、人和万物发生与发展的根据,“无为”乃“生生”,“无为”乃“衍化”,有自然的“无为”之美才有万物的生生之美。
老庄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无违”之意,则违天道之不为的美德,这是治人事天的重要行为准则,也是人性之美的崇高境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无为”是放弃主宰者或占有者的行为,以守护者的姿态参与生命和看护生命的自然衍化。老子“无为”思想中的修身之道,就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涤除玄鉴”,从而“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最终使“人性”达到与宇宙之道接近的最为自然本真的审美之境。碌碌无为、无所事事并不是老庄所推崇的人性之美,人的生存只有以“道”为原则,“人性”以宇宙之道为参照而循理举事,无为而无不为才是真正的人性之美。老子循循善诱地劝导人们要“上善若水”。一个德性美的人,要像水一样滋养万物(有为)而不争(不为),在人性表现的层面上,即与人交往仁慈关爱,言语真实坦诚,为政清静廉明,做事德才兼备,行为择时而动。以这样一种处世哲学来修身,就会像“赤子”一样纯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对于人的精神生活,老子的理想的审美境界是“恬淡为上”、“燕处超然”,只有以“无为”为准则持守恬静淡泊,不为世俗所羁绊,行动顺乎“天道”,精神合乎天道之美,才能成为得“道”之人、纯粹素朴生活的人、超然脱俗的人、真正审美生存的人。
以工具理性为特点的现代文明在面对世界时则采取了绝对而片面的“有为”,此“有为”不是依照自然规律和天道之美的有所作为,而是违背天道、与自然相对抗而为,意味着生命的异化与审美的摒弃,将对物的占有作为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人类把向外部世界的不断索求、掠夺和占有当作文明进步的表现,结果既导致了生态有机系统失衡,同时也造成了现代人放纵欲望、沉溺自我、疏离自然的非自然审美生存状态。现代文明将人从自然生命世界的整体中分裂出来,把自我当作存在的中心,个体以攫取尽量的权位、财富、名利等外部资源满足自我需要为目标,结果是导致了人类与自然、自我与他者、身体与心性的对立冲突,最终造成当今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的心性生态的“三大危机”——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此伏彼起,人的心性浮躁困顿,人成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老庄主张的人类无违于自然的“无为”审美思想,是建立在对自然、社会和生命本体透彻理解基础上的宽容平和的心境,是从一个更超越、更广阔、也更符合审美存在本真的生命视角来确立自我的行动方式。这对于深陷于“三大危机”困惑的当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剂救治心性的良药。
三、平等:齐物和合之境
《齐物论》说万物平等,《逍遥游》谈游心太玄,“齐物”与“逍遥”也即“平等”与“自由”是庄子生态美学的两大思想基础。庄子继承老子“自然”、“无为”的道学审美思想,并把“道”的精神引向万物“平等”、众生“自由”的至高审美境界。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与人类并生共存,万物与人类合而为一,天、地、人、万物同为自然的产物,那么人与天地是可以并生共存的,人与万物也应该合而为一的,庄子的这一千古哲理之思辨是无可置疑的。庄子齐物思想是建立在老子“道”创生万物的自然生成论基础上的,人与万物同是自然之子,这就有了同源性和亲缘关系,那么人与万物的物性相同、存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等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庄子的思维逻辑是无障碍的。庄子齐物思想中的“齐”,则有平等、相通、共识、统一、完美等意涵;“物”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万物既然是同源的那么就必然是平等的,推而言之万物的个体生命虽然千差万别却是可以相互会通的。《齐物论》立论的基础“万物同源”观,阐述的重点是虚明的心境,最高的要求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也就是“物我同一”,即人与自然的和美之境。在庄子那里,“物我同一”,就是天人和美之境,也即“人与天一”、“物无贵贱”的平等和合审美观。
庄子认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本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万物之一。“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庄子·大宗师》)自然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人只是其中一个被自我充分书写却又至今无法真正认识的部分,万物是相互蕴含与依存的,自认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在自然“生生”天道中也同样要遵守生命的自然法则。在庄子看来,“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庄子·天地》)“人与天一”的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人既离不开天地也离不开万物而应当“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 庄子·齐物论》),这样就达到了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 庄子·马蹄》)的大美之境,即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的审美生存境界。
庄子的万物“平等”的和美观,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情怀之源,其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齐一、互为钟情与倾诉对象的审美旨趣。李白“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审美情怀就是最典型的写照。万物平等的和美思想使人重新回到自然、回到诗性,从而构筑了中国美学“和美”的情怀与基调。万物平等的和美思想,以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和异质同构为基础确立了一种诗意化的物我合一的关系,使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同时,万物“平等”、“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思维,使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特别强调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合一。
庄子的万物平等的和美思想,对现代生态哲学与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里,你忽然发现有几个生物考察队员,树与人孰美?不言而喻。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你忽然看见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人与树孰美?不言而喻。其实物性之美是相等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不同的审美视觉而已。怀特海把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理解放到了一个以“和美”为审美原则的广阔背景中,认为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共存关系,任何个体必须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合作才能够完善个体生命。这种“和美”的审美原则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每一种事物内在生存与审美价值是完全平等的,人类也只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的大生态中的普通一员,完全没有理由自视为宇宙的中心而违背宇宙之道成为自然主宰者。
现代生态美学认为,只有超越主体性,超越主客对立,进入主体间性,才能达到审美生存的境界。主体间性美学把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看作是主体间性关系,是一种“我与你”有生命、有亲缘、有感情的关系,是本真的审美存在的实现。这就恢复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同一性,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奈斯认为,人与万物都处于“生物环链”中,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卫· 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提出,自然是与人息息相关的生命体,现代生态美学需要否定启蒙时代的主体性“祛魅”,而进行“世界的返魅”且这一“返魅”是在更高水平上对人与自然同一的回归,这种回归是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的,有利于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深受庄子齐物观的影响,中国古代人处世尽可能与自然、社会不异化、不分裂、不对立,从而使源远流长的和合思想孕育出的中国生态美学具有包罗万象的亲和性和包容性。现代生态学认为,尽可能保存生物的差异性才能最有效地维持整体的生态和谐。自然生态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人文生态,社会人文永远处在融合与差异的平衡关系中,消解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的心性生态“三大危机”,首先应营造一种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心性平和沟通对话的空间,从而使大家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珍视对方的生命价值和联手守护共同的诗意家园。
四、自由:游心太玄之域
庄子继承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把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理解为个体生命超越尘世、顺应自然的过程。庄子将自然适意的“游”看作是人性解放的审美之境,看作是“而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大宗师》)的人生观,看作是对“性命之情”深刻体验后所获得的自由生命的理解。只有充分“游”的人,才能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身临其境于自由精神王国,成为“乘物以游心”的审美生存的“至人”,才能进入“无为”、“无执”、“无待”的精神至美境界,从而感受无限自由的人生乐趣。在庄子那里,通过“逍遥游”将人生的认识和生命的体验融为一体,以心感物,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使人性在非异化存在中变成人对生命的最本真的体验,将有限的人生引领到无穷的宇宙精神中去,从而在逍遥游中化解世俗生存的困顿并体会到生存的自由自在,最终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游心太玄”的大美境界。
“逍遥游”的过程就是涤除玄鉴、清心寡欲和见素抱朴的过程;“逍遥游”的境界就是放下所有、精神解放和燕处超然的审美之境。庄子的“逍遥游”按照心游、梦游、神游的三个境界而步步提升,最终臻及游心于太玄的至美境界。
首先是“心游”,即心理之游。庄子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庄子·骈拇》),“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间世》)。在庄子那里,身心是不分离的,心为身体之核心,“心游”则全身心之“游”。庄子的“游心”既可以将外部物质世界通过眼看、耳闻、鼻嗅、手摸、脚涉等身体感觉内化到心性深处,也能将内部心性世界通过身体的中介外化到世俗社会之间,整个世界幻化为任心性自由往来的广阔天地。“心游”是人性对天道的一种仰望与诉求,是人的心性指向遥远世界的一种单向活动。“心游”集中体现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深层的心理活动,是心性自由的一种单向的表现形式。
其次是“梦游”,是恍惚缥缈的潜意识漫游。庄子曰:“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梦是一种通过假借来表现心迹的潜意识活动,为的是借助于假设的梦境去表达某种现实中不能或难以实现的美的憧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逍遥游”是个体内在的精神活动,因而决定了“逍遥游”是缥缈而不是现实之游,“梦游”凭借梦幻的手段,与生命力充盈的生物体合为一体,使“非现实”引渡为“虚现实”,从而达到生命的转移而走向永恒的存在。奥地利著名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说:“梦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梦可能是清醒状态的易懂的精神活动的延续,也可能由一种高度复杂的智力活动所构成。”“梦游”是人性对天道的一种潜意识的交流与融合,是人的心性指向遥远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双向活动,在这种近于神秘状态的体验过程中,人与飘然灵性的蝴蝶化为一体,不知谁为谁的梦境,各自的生命获得虚幻的转换,人的生命借蝴蝶羽化而指向永恒的审美存在。
最后是“神游”,是自然神圣之游,是游的至美境界。如果说“心游”是对现实尘世的一种反思,“梦游”是对现实尘世的一种出走,那么“神游”则是对现实尘世自由的一种超越。庄子之道乃“天道”,由此决定了作为“体道”的“逍遥游”的至美境界必然是自然神圣之游——神游。自然神圣境界就是无为的境界,无为就是“回归自然”,即是逍遥自由的境界。“神游”是一种绝对无功利的自由感性活动,一种根本审美的人生态度,一种与天地同体、与万物合一的彻底解放的自由精神活动,一种超越此岸却非往彼岸的纯生态信仰的至美境界。庄子曰:“游乎天地一气”(《庄子·大宗师》),“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山木》)。庄子在悟道式的生命体验中解脱一切外在束缚,进入到自然神圣、逍遥自由的境界。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深受庄子逍遥“神游”自由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 神思》中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对“神与物游”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使意象创造理论开始趋于完备,从而为意境理论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实存在是不自由的,然而只有自由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也只有本真的存在才是审美存在。所以,庄子认识到只有超越现实进入逍遥游的境界,才能达到自由的审美存在。这与格里芬的“世界的返魅”、海格德尔的“诗意地栖居”所追寻的生态审美生存之路是相同的。现代生态哲学与美学所宣扬的“主体间性”在非现实的“在遥远的地方微笑着”的存在。在现代社会里,现实存在是主客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心性都是主客关系,只有在超越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人才进入了主体间性关系与那个“在遥远的地方微笑着”的诗意之神知会,从而克服主客对立,实现人性自由。在本真的存在中,在更高的水平上恢复人与自然的同一,自然重新拥有生命和灵性,成为可与人交往、对话、沟通、神交的另一主体,这正是庄子游心太玄的逍遥之境和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审美存在之境。
§§第五章“天人合一”——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终极旨归
在老庄美学思想中,“天人合一”是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美的韵味,是人类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律,人不仅在从自然界得到物质供养时要遵循自然规律,且道德修养与一切审美活动都要同自然达到高度的统一。所以“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秉持的基本思想,是生态审美的终极旨归。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周易》最早提出“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八卦孕育的思维模式、卦爻辞的思想内涵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周易》的“天”以天地、阴阳、乾坤并举,“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系辞下传》)。天是自然之天,人只是天地自然“化醇”的结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易·序卦》)。人只是万物中的一物,自然万物和人类具有同等地位都受制于天,人应顺应天道而安身立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干》)。
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易学基础上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老子提出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把思维直接追溯到“天人同源”的宇宙生成论源头,从而一劳永逸地回答了天人“何为合一”、“为何合一”、“如何合一”等形而上问题的追问。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道法自然”,认为人应该在遵循自然法则、不违天道的前提下主动地循理举事、安身立命。从而从本体源头上避免陷入“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和“人定胜天”狂妄观的人类生存思维怪圈,从而开出人与自然和合的审美新境域。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以万物齐等和追求精神自由、回归自然为旨归,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审美境界。“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庄子·山木》)。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及自然万物同属一个宇宙,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应该相互依存、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万物相处的优态境域是“与麋鹿共处”(《庄子 · 盗跖》),人审美生存的至美境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