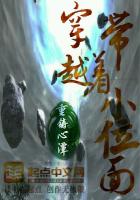她还申明:“我就是一个小市民。”她解释说:“‘俗’这个字在中国文字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有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粮食岂不是一个美好世界?”(程永新、池莉:《池莉访谈录》,见《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这种解释再鲜明不过地表达了池莉的世俗立场和乐生意识。她关心的是底层民众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不是精神上的超越。有吃有喝,其乐融融!池莉要解构的是精神神话和形上神话,要认同的是物质神话和世俗神话。池莉视野中的底层民众是安于现状的乐生群体,而方方视野中的底层民众是陷入生存困境的迷惘个体。方方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池莉是一个快乐主义者,她们的底层意识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同古希腊哲学史上皮浪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的区别一样。皮浪是古希腊著名的怀疑主义者,而伊壁鸠鲁则是快乐主义者。伊壁鸠鲁最早提出了“一个人被鞭挞的时候也可以幸福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的命题。对于池莉笔下的底层人物来说,活着最重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哪怕是艰难的活,苟且的活,被奴役的活,被鞭挞的活,人也要在活着中苦中作乐。
这种苦中作乐的乐生意识,正是池莉底层叙述的核心。人们经常所说的池莉的平民意识,或者市民意识,其核心正在于这种世俗的乐生意识。当然,池莉笔下的底层人物活着也会有痛苦和困惑,但在池莉的世俗视野中,这种生存之痛被苟安之乐遮蔽了。如果说阅读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中经常会冒出这样的念头:“生活就是好!”,那么在阅读池莉新写实小说的过程中,另一个念头也会不自觉地蹦出来,即“生活就这样也好!”所以,池莉底层叙述中的乐生意识中也隐含了无奈情绪。正如池莉近作《生活秀》中所说:“只有日子是最不讲道理的,你过也得过,你不想过,也得过。”在这种被动的生存中,女主人公来双扬的“全部生活就只是卖鸭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来双扬被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所纠缠,如无能的哥哥,可怜的侄子,堕落的弟弟,风流的嫂子,隔膜的父亲和继母,还有个人的情感纠葛,老屋的产权问题等等,生活远不是一场卖鸭颈秀那样的风光。不难想象,同样的题材在另一个作家的笔下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样子。那样的来双扬将是一个痛苦和忧郁的来双扬,一个被生存之重压得无力承受的来双扬。而池莉笔下的来双扬是一个知足乐生的底层女子,她泼辣精明,干练爽快,快乐主义是她的基本人生哲学。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尽最大可能满足自己的物质和心理需求,这是来双扬一直以来的处事原则。她对继母态度的变化如此,她对九妹的亲事处理也是如此,中间体现了来双扬的快乐利己主义的人生理念。至于妹妹来双瑗,小说中一直是作为嘲弄和调侃的对象来勾画的,来双瑗的知识精英姿态被池莉无情地消解了,但她唯独对来双扬的世俗乐生安命意识保持着足够的宽容、理解和欣赏。
三、后革命语境中的底层叙述:
救赎意识与抗争意识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到四十年代的延安解放区文学,再到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相当显赫的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新启蒙话语的确立和后启蒙话语的兴起,建国后的主流革命话语几乎丧失了自己的位置。九十年代以来,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和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物质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相当严重。农村经济凋敝,工厂破产倒闭,曾经当家作主的工农大众逐渐在失去主人公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一度退隐的革命话语有了复兴的迹象。
革命话语不同于启蒙话语,它们之间存在着“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区别。启蒙话语强调文学的人性本质,而革命话语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和阶级性。启蒙话语主张通过文化批判和国民性的重建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革命话语致力于政治批判和阶级革命来谋求民族独立,建构新中国。历史证明,革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也可以把中国带入“文革”浩劫。因此,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左翼话语,并不是对曾经主宰中国一切的主流革命话语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话语的一种扬弃和超越。一方面,新左翼话语主张直面社会的两极分化和阶层分化,呼吁关心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强调继承中国革命文学的人民性传统,另一方面,新左翼话语也并未忽视革命的负面的历史教训,所以并不主张通过阶级反抗和政治革命的激进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建构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秩序,来改变底层被奴役的处境。至于依旧固执于激进革命立场的左派声音,并不是真正的新左翼话语。真正的新左翼话语是一种后革命话语,强调的是阶层而不是阶级,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是和谐而不是对抗。
湖北作家刘醒龙,是九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一直以关注农村和关注底层著称。虽然八十年代的刘醒龙也曾在新启蒙语境中创作过大量的寻根小说,被誉为“大别山之谜”,但只有在九十年代的后革命语境中,刘醒龙的创作才真正找到自己的话语位置。《村支书》和《凤凰琴》在九十年代初的大放异彩,《分享艰难》在九十年代中期之所以对文坛构成“冲击波”,潜在的原因,正在于这些小说和日趋成型的后革命语境之间相契合。刘醒龙的后革命话语,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中已经初现端倪,及至新世纪的长篇大著《圣天门口》,更是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深切反思。这种后革命文学话语,既重视文学的“人民性”,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同时又强调“社会和谐”,主张通过道德劝诫来净化社会的风气,提升公民的精神品格,以期最终消除社会的不公正,从而化解底层民众的苦难。《圣天门口》中梅外婆的德性之美,感化了终日沉浸在阶级斗争和暴力杀戮中的无数人的良知。这使得刘醒龙的小说带有强烈的老托尔斯泰色彩。事实上,俄苏文学对刘醒龙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气质的形成,有着鲜明而深远的影响。老托尔斯泰的道德救赎意识和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直暗中支持着刘醒龙的小说创作。
刘醒龙说:“我们有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公民。‘公民’与‘平民’并不完全一样。公民的言行必须有责任。作家的内心是自己的,作品却是社会的,要对社会负责,责任感很重要。平民意识是个阶层的划分,公民意识不是这样的。”(刘醒龙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大家谈》,《新华文摘》1997年第3期。)刘醒龙不用平民意识而强调公民意识,主要就是为了避免阶级(阶层)对抗而带来民众的苦难,他强调的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具体到他自己的创作中,这种社会责任感的达成,主要是通过道德救赎来实现的。如《村支书》中因公殉职的方支书,正是他克己奉公的道德人格,最终感化了自私敛财的村长。
《凤凰琴》更是一曲关于良知的忧伤歌谣。在穷山区的那所小学里,虽然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张英,包括最终死去的明爱芬,这几位小学民办教师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庸俗的一面,但这是苦难的现实处境扭曲的结果,而且他们凭借自己的良知,最终战胜了苦难的重压,救赎了自己的灵魂。在《分享艰难》里,作恶多端的暴发户洪塔山,还有忍辱负重但又苟且纵容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最终都被一个宽厚的老农田细伯所感化,孔太平跪在舅舅田细伯的面前,洪塔山把桑塔纳卖了给镇上发工资。尽管田细伯的女儿被洪塔山强暴,虽然起初老人忍无可忍,但最终还是以德报怨,净化了两个俗人庸人的心灵。在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出身底层的农民陈老小、陈东风、翠翠、玉儿,他们有的是老劳模,有的是农民工,有的是打工妹,但他们的高尚人格力量,最终一一化解了城镇工厂包括厂长和书记在内的一干人等,如陈西风、徐快、段飞机、汤小铁、方豹子等人丑陋鄙俗的灵魂。正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刘醒龙给政治化的革命话语重新灌注了道德救赎的内涵。
和刘醒龙一样,陈应松也是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一开始也受到了寻根文学的影响。大器晚成的陈应松直到新世纪以“神农架系列”才赢得全国性的声誉。很多人疑惑,为什么陈应松突然一夜成名,而且作家本人也存在类似疑惑,因为他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如既往地走过来的,并未刻意求变。其实,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之所以普遍为人关注,主要不是因为时下的“生态文学”热潮,而是由于它们的内核契合了新世纪以来越来越成熟的后革命语境。如果说刘醒龙的底层叙述是温情的、悲哀的,那么陈应松的底层叙述就是愤怒的、激烈的。尽管陈应松的底层叙述中也有道德意识,但他的阶级意识似乎更加显著。陈应松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富人阶层和中产阶级话语的不满,他说:“我讨厌城市、富人,有着华丽居所的电影和小说,我认为他们的所有表演都是矫情的。他们的痛苦极不真实,他们神经质、变态、令人恶心。只有农民和小人物的感情才是真实的,他们的痛苦优美无比,幸福催人泪下。”之所以有这种比较绝对或偏激的看法,作者自己分析说:“我之所以如此,可能与我的生活,我出生在乡下有极大的关系。这也许是一种写作的宿命吧。”“我虽然走了很远,但没有走出我的内心,没有走出我坚持的东西,我依然一如既往,热爱农民和下等人,也就是说,热爱我童年接触到的一切,热爱我的阶级。”(陈应松:《后记》,见《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获奖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陈应松的这种宏大阶级意识,在他的底层叙述里,主要表现为人物对现实苦难的抗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