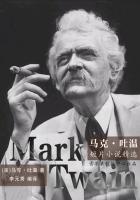绽放与飘零
樱花啊,樱花啊,暮春时节天将晓,霞光照耀花英笑,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任风飘。去看花,去赏花!赏花要趁早。”这是一首日本家喻户晓的歌谣《櫻花》。其澹定、凄美的歌词和轻盈的旋律,如初春里的櫻花一样,淫浸在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里。只要一提到日本,就禁不住想到这首樱花歌谣,就对神秘的日本有一种向往。直到那年留学日本,我才亲眼目睹了櫻花,也逐渐认识了日本人对櫻花的情愫。
日本人把櫻花奉为国花,櫻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有名的神社每年都要举行一些民俗活动,以乞求樱花神的保佑。这种信仰也渗透到农业生产中。很久以前,民间就流传‘樱花催人播种”的谚语,人们相信櫻花神可以带来丰收。每年初春,櫻花绽放的讯息随着南来的春风一路北上,如是一年一度的赏櫻仪式,从南到北整个东瀛列岛沉浸在一片粉红白色的花海之中。樱花在日语读音是“Sakura”,“Sa”的意思是“田野之神”,“Kura”意指“出现”,是否可以说樱花的意思是“田野之神的出现”。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位住在天宫的櫻花女神来到了坂出这个荒芜的地方,觉得坂出这地方只要略加开垦就可以变成美好人间,于是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自己的一双玉腿随着一口气腾空而起,随即满天闪着耀眼的白光,并滑落遍野,一排排的开着櫻花的櫻花树出现了。之后,又一道白光闪过,从女神身上出现了一个英俊的男子和一个美丽的女子。当他们回眸时,女神不见了……望着一树树开满淡雅的樱花,不由得就想到日本《武士道》一书中的赞美:“樱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民喜欢的花,是我国国民性格的象征……在它的美丽下面并不潜藏着刺和毒素,任凭自然的召唤,随时捐弃生命,它的颜色并不华丽,它的香味清淡,并不醉人。太阳从东方一升起,首先照亮了远东的岛屿,樱花的芳香洋溢在清晨的空气中,再也没有比吸入这美好的气息更为清新爽快的感觉了。”就连曾经留学日本的鲁迅曾经也有过对它的描写:“上野的櫻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緋红的轻云。”(《藤野先生》)是啊,櫻花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她终将是会飘去的,一般都是在七天左右就将如雪花般从树上纷纷飘落。人们赞美樱花,在赞美他生命的绽放的同时也赞美她的生命的凋零。这种以赞美樱花为主的日本审“美”中似乎总是飘逸着一个神秘的影子,甚至在日常生活及性爱世界里也有,可以说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就有它的存在,那影子是什么呢?就是对“死”的咏叹。
对“死”的态度,确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审美情结。
日本古代的武士更以樱花自比,将那“瞬间美”的观念转变为视“死”如归,为生命之极。他们的殉死,其意义也在于追求瞬间的生命之闪光,企图在死亡中求得永恒的静寂。正如《武士道》一书中所写道的,樱花在它的美丽下面并不潜藏着刺和毒素,任凭自然的召唤,随时捐弃生命……”
日本的文艺作品有许多悲情的经典,虽然有些是虚构的悲情,却也道出了那种视“死”如归情怀。日本的作家、诗人多自杀,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有意思的是日本作家也格外热衷于描写自杀,三岛由纪夫是这方面的髙手,其作品基本主题就是自杀,死亡和流血,追求一种毁灭的美。川端康成的小说骨子里弥漫着一种死亡、颓废意识,一种病态的美被表现得绚丽和髙雅。日本原本就是一个自然崇拜的神国,号称天地神祗八百万,肉体的死亡不过是返回神国的一种方式,就像櫻花飘落返回自然一样。
日本文化中的矛盾现象让美国作家鲁恩?本尼迪克特吃惊而好奇,她在《菊与刀》中这样写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自杀已成为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态度,2004年10月13日《北京晚报》报道日本九青年集体自杀。根据日本官方统计,2003年发生了超过34427起自杀事件,比2002年高出7‰,19岁以下的人数比去年更激增到22%……2008年日本全国自杀人数为32249人,虽比前年减少了844人,但却是连续第11年自杀人数超过3万大关。从职业类别看,无业者最多,为18279人(占总数的56.7%);工薪族8997人(占27.9%);个体营业者3206人(占 9.9%);学生972人(占3%)。
日本国民对樱花的迷恋,实际上是对能够象征生命美的女人青春之钟情,是对生命瞬转即逝的讴歌。这一点,在画家加山又造身上尤为明显。他说“女人体我个人认为是樱花绽放与飘零最真实最完美的表现,作品名叫‘花瓣’,”加山其实是把櫻花盛开时的情感给了生命淀放着活力的人体,此时的人体是赏花时心情的物化,而这种心情是笼罩着飘零花瓣的氛围之中的。加山歌咏飘零的失落感伤。包括在日本《万叶集》诗歌中有许多感情纤细的诗歌,例:秋令姗姗来,芒草结露珠。飘忽爱恋情,恍若此清露。作者将恋情比作秋令芒草上的露珠,其美一展即逝,犹如生命之无常,以此寄托自己的悲秋之情。
视“死”如归,是日本人宿命观的显现;其“平常心”的生活态度就是对生的澹定。崇尚茶文化——茶道,就是日本民族心理中“对生之澹定”的一种流露。在日本历史上,就传说着日本武士古田织部在一次打仗时他忽然发现自己拿着的竹盾上有根很中意的竹条,于是便在作战中将其削制成茶勺,为此还负了伤。利休剖腹自杀时,在死前一直不断地削茶勺,说是要作为遗物留于后世。在日本,岂止是茶道,还有歌道、书道、花道、剑道、艺道、柔道、香道还包括色道,一旦上升到“道”的境界,就等于进人”禅”了。日本的这些“道”,是赏櫻后的觉悟;影响着日本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对日本人的文化、审美情趣、文艺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一位日本学者说:“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的美学支撑的。”
“死”与“寂”,是一对孪兄。生命因“死”而圆寂,故视“死”如归。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有着“空寂”和“闲寂”的情趣。日本汉字中的“寂”包含广泛深刻的内容:主要是表达一种哀和静寂为底流的枯淡和朴素的美。“空寂”的含义是闲、孤寂、贫困;“闲寂”的含义是恬静、寂寥、古雅。这是日本国民崇尚禅宗的生活写照,是直接面对大自然,开拓出与自然为一体的禅宗境界。但是日本的僧侣是在世俗的街巷中,把大自然唤到自己的身边,其代表就是禅寺的方丈庭,他们不像中国的禅师,从正面直接接触真正的大自然,认识宇宙,日本人是通过观赏石、沙铺建的庭院式自然景观来想像大海、群山和无垠的宇宙。
日本人欣赏樱花的清净无尘,鲜而不艳。他们追求纤细、轻盈、恬淡、清逸、静穆之境,这种直观的文化现象反映了日本人特有的审美心理。櫻花比牡丹、月季雅洁,比蔷薇、玫瑰柔丽、纤细、单纯,有群吐群芳之美,又有不滞不沾,随风飘零、转瞬即逝之美。对于有着赏樱花传统的日本人认为,欣赏樱花的最佳时机不仅仅是满树櫻花的绽放,也包括满地樱花的飘零。从日本人赏樱花的讲究可看出,他们欣赏残缺之美的境界,是这个民族对死亡的壮烈之美和衰败的悲壮之美有独特的理解和追求。确实,日本文化现象确实充满着矛盾双重性,在那典雅、明快中确体现着生命与活力,然而,在那世俗虚无中又体现着对死亡、自然的超越。日本大部分的文化艺术现象留给人们回味和难以忘却的却是那淡淡恬美的和谐、轻清感伤的静穆,而这种视觉效应和视觉体会正是吻合了赏花、叹花的自然心境和暧昧、和谐的审美情趣。
我认为,櫻花具有纤细、凄美、芳心、雅性、禅境,充分体现了一种日本特定的审美心理和情趣。对于喜欢感性认识世界的日本人来说,通过具体的“物”去考虑和认识问题是他们的特点,也构成了他们的审美特性。在日本,无论是物还是人,无论是川端康成的审美情趣、还是加山的形式趣味,我们似乎都能找到一个视觉审美的共同点:日本人欣赏櫻花绽放时的明快轻盈、宁静优雅,弥漫着一种淡淡甜美的朦昽神秘,而又仿佛渗透着樱花飘零时的潇洒飘逸、悠怨迷茫,似乎也能体味到一种无奈的豪情感伤的凄凉。
黄山拜师
黄山为天下绝秀,千峰万嶂,干云直上,不赘不附,如失如林。幽深怪险,诡异百出,晴岚烟雨,仪态万方。其一泉一石,一松一壑,云涛风海,飞流倾搏,或潇洒,或淡远,或润秀,或怪险,或繁复,或浑苍,或壮阔。历史上的多少文人墨客在黄山留下了无数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
这次去黄山,一则是带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去黄山写生、采风,二则是要寻师访友。
因为几年前我有幸结识了新黄山派的程乐萍先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黄山作品时,我感觉到我注定要和这个人有缘。
这次到黄山,又见程先生的大作,其情更真,其神更精,其意更逸。站在他的画前,我久久不愿离去。我特别欣赏程先生自然天成的特殊技法。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袁运甫教授曾对他的技法大加赞赏,台湾的刘国松先生也对他的技法充分肯定。
程先生的黄山作品,一时黑压压一片,咄咄逼人。一时透明清淡,心旷神怡。一时深远浩渺,无我神游。一时光撒云开,醒悟生智。特别是那虚虚实实的萌动,使观者不知梦里人间之感。
北宋画家郭熙在《山水训》中曾有如下感受:
“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洽,夏苍郁,秋疏薄,冬黯淡……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东山惨淡而如睡。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见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阳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
程乐萍,1945年生于黄山,自幼喜欢绘画,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常在山中凝神烟云变幻,夜而忘返。几十年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1995年春,他首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自己独创一格的黄山画,令首都观众耳目一新,三十余家电台、报刊作了大量介绍、报道,颇为轰动。当年十一月底,又在深圳博物馆展出,并出版“程乐萍画集”。1996年进中央工艺美院深造。1997年在著名壁画家袁运甫指导的装饰壁画研究所从事壁画创作。1997年初为中国科学院贵宾厅创作大型胶合亚光壁画《日月同辉》,并在北京为民革大厅、总参谋部、长城宾馆等多家单位绘制壁画,深受好评。其作品广为流传,同时也为美术馆、博物馆、企业、私人收藏。
程乐萍绘画,不限材质、画法、画种,力求艺术效果,能创新。画法与众不同,优以刻画黄山为绝,人称“裎氏黄山”天下一绝。难怪袁运甫教授称“神笔乐萍”,著名画家白雪石书赠“惊奇艺术”,著名画家刘迅誉为“黄山奇中奇”。
中华大地,江山多娇。五岳之尊,黄山之奇,华山之险,青城之秀,峨眉之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程乐萍是黄山之子,他从小生活在黄山脚下,几十年的黄山生活,几十年的山魂体验,使他的黄山梦境整日飘荡在黄山的峰岚之上和幽谷之中。
程乐萍先生童年生活在黄山时,就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他谈不上如何去表现这个世界,只是如痴如狂地陶醉在这个世界之中,常常沿山登临,从天都峰到玉屏峰,从莲花峰到鲫鱼背。他累了,也醉了。在峰岚和蓝天之间,有时也昏然地睡去,这一睡却做了一个没有止境的梦。
正是这个童年的梦使他掉进了苦海,那茫茫的艺术苦海。梦里寻她千百度,他在苦海中遨游,在梦中追寻那黄山的魂魄。
几十年个寒暑过去了,程乐萍以他对黄山的一腔情怀,以他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歌咏了黄山。他是一个聪颖而勤奋的山水画家,他的路完全是一条蹒跚而爬行的路。正是因为自己独特的崎岖,使他获得了与人不同的艺术天地。正是因为自己独特的梦境,造成了他别具一格的东方审美境界。正是他独自在苦海里的淹呛,吐出了他气吞洪荒、深邃脱俗、清幽莫测的云山呼号。
“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意味淡,故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故初看平平而终见妙境。”——黄宾虹程乐萍的特殊技法的黄山作品,从直观感受和理性审思,谁都会脱口而出,啊,东方的,东方的天,东方的云,东方的空气。
程乐萍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油漆工,对于油漆的性能和工艺非常精通,油漆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什么视觉效果,他都了如指掌。他把油漆工的这套技法,充分运用到了他的作品之中,成为了他作品技法的重要视觉特征。
程乐萍也曾画过水墨画,他对水墨的技法也有充分的理解。特别是以水墨画的气韵来表现黄山石、黄山松和黄山云,在他的作品中都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他尤其善长画黄山松,那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黄山松的精神,为他作品的感染力增色不少。
黄山的情怀和技法上的独到综合的运用,造就了程乐萍的独特风格特征。
“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画继》邓椿语。
“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石洲诗话》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钟碌语“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语
这些话从某一点上来说,反映了东方艺术家面对大自然的艺术感受,也就是文艺家认为的“物情说”。
一个满怀情感而又满腹绝技的画家在他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却存在着一个再创造人化自然地艺术经营过程。同样是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感受之差异,也是艺术格调之差异,越是基于什么文化背景的感受,也就产生什么特色的艺术境界。以此反推,什么样的艺术境界,作者就是什么样的自然感受。
这段话,纯然表达了东方人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对大自然的感受共性。基于这样的审美观察,程乐萍所苦心创作出的作品正好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情趣,应验了这种共鸣,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契合。
正是自然形象兼有千姿百态、意境繁密的属性,所以画家才能从千姿百态的物象中抉择自己独特的感受形象,借以表达自己对大自然,对人类,对时代的深刻感受,揭示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打上时代和个性的烙印。
程乐萍以黄山为家,家就安在黄山。他在时光的寒来暑往、阴晴雨雪之中观察自然,用艺术的心灵把他独创的特殊技法去升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