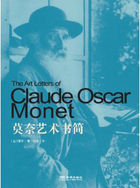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鸣凤记》以浓重的色调渲染出了一种悲壮美,上承《赵氏孤儿》,下启《清忠谱》,是中国戏剧史上那条表现浩然正气的长链中的一环。
剧情比较分散、人物比较驳杂,是它的一个缺点;但由于把正邪善恶两大营垒划分得非常清楚,人们仍然可以从分散和驳杂中获得鲜明的总体感染。
例如,“文华祭海”一出中,皇帝要宰相严嵩任命官员前去剿灭倭寇,严嵩怕哪位猛将征剿成功后很难管制,竟派了完全不懂军事的干儿子赵文华去。赵文华杀了一些无辜的百姓,冒充倭寇的首级到朝廷领赏,最后竟然要把诵经和尚也杀了,因为一颗头可换来五十两银子。这样的恶行,由戏剧家在舞台上集中表现,自然在观众心中构成了强大张力。
有时,一个小小的插曲都能激起观众的愤怒。例如剧中写到一个唱曲行乞的瞎女人,骨瘦如柴、哀声可悯,被人询问,这个瞎女人的回答是:
奴家原是扬州商人李氏之女,父亲在京开了个缎匹官店。严世蕃在店前经过,见奴姿色,强逼为妾。父亲既死,家财尽被掳占。今世蕃有一十六个爱妾,见奴色衰,万般凌虐。他正妻怀恨昔日宠爱,将奴刺瞎双目,赶出抄化。
由于把那个罪恶的巢穴表现得十分透彻,正面的反抗行为也就有了充分的情理依据。武将杨继盛因揭发严嵩的党羽反遭迫害,他的夫人在临刑前赶到,为丈夫满斟别酒一杯,然后取出祭文一篇,跪地而读:
于维我夫,两间正气,万古豪杰,忠心慷慨,壮怀激烈。奸回敛手,鬼神号泣。一言犯威,五刑殉裂。关脑比心,严头稽血;朱槛段笏,张齿颜舌。夫君不愧,含笑永诀;耿耿忠魂,常依北阙。
杨继盛被斩之后,夫人又托监斩官转达皇上,依杨继盛生前嘱咐,尸体不加掩埋,以“尸谏”感动君王。监斩官不敢转达,杨夫人立即自刎身亡,连监斩官、刽子手都大为震动。
总之,《鸣凤记》以政治纪实剧的方式展现了一支前仆后继、鲜血淋漓的壮烈梯队,裹卷了几代观众,因此也展现了戏剧在社会鼓动功能上所能达到的一种顶级浓度。
三、《浣纱记》
作为戏曲声腔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浣纱记》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作者梁辰鱼(约1519—约1591)是一位重要的戏剧改革家。由于他和其他几位杰出同乡的努力,他的家乡江苏昆山将要成为中国戏剧改革的重镇。
《浣纱记》的题材,是春秋时期吴、越争斗中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后来很多戏剧作品反复表现这一题材,都受到过它的影响。
《浣纱记》一开始就把范蠡投入到了理智和情感的两难之中。他知道要让越国反败为胜,必须对吴王实施最高等级的“美人计”,而自己的未婚妻西施则是不二人选。于是,范蠡为了自己的谋略,西施为了尊重夫君的意志,一起作出了可怕的牺牲。最后,一切如范蠡所预期,吴国败于越国,范蠡和西施功成身退,泛舟太湖之上,飘然不知去向。这对情人重新团聚在太湖扁舟上的时候各自从胸口取出当年的定情之物——西施所浣的一缕细纱,《浣纱记》的名目也就借以成立。
在梁辰鱼笔下,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爱情生活,都处于一种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过程之中,因此他没有花费笔墨去评述吴、越间的是非。剧中的所有人物,都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梁鱼辰对道家的这种逆转逻辑颇为着迷,并把它作为全剧的灵魂。甚至,他还让吴王的小儿子出现,来阐述“废兴运转”的道理。
吴王:孩儿,你清早打哪里来,衣裳鞋袜都是湿的?
吴儿:适到后园,闻秋蝉之声,孩儿细看,见秋蝉趁风长鸣,自为得所。不知螳螂在后,欲食秋蝉。螳螂一心只对秋蝉,不知黄雀潜身叶中,欲食螳螂。黄雀一心只对螳螂,不知孩儿挟弹持弓,欲弹黄雀。孩儿一心只对黄雀,不知旁有空坎,忽堕井中,因此衣裳、鞋袜通被沾湿。
吴王:孩儿只贪前利,不顾后患,天下之愚,莫过于此。
吴儿:爹爹,天下之愚,又有甚于此者。
在群雄争霸之隙,在至高权位之侧,引出一派稚声,用童话和寓言来锲入极不和谐的哲理——这几乎可以直接呼应现代艺术了,可见古今艺术,相距不远。
四昆腔的改革
在叙述这三大传奇的时候,还必须面对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它们之所以可以组成一种趋向于兴盛的戏剧现象,还因为一次重大的声腔改革——昆腔的改革,也在那个时候完成。
《浣纱记》是第一个用改革后的昆腔演唱的剧本,自它之后,昆腔在中国戏剧舞台上,一直兴盛了很长的时期。
此事不妨稍稍说得远一点。
中国戏曲离不开演唱,因此,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也包含着戏曲音乐的发展,而且一向以戏曲音乐的递嬗作为整个戏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上文早有论定,杂剧和南戏的盛衰荣枯,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北曲”、“北音”与“南曲”、“南音”的较量。
我们已经说过,北曲在元代发展了那么多年,传到南方之后曾把南曲压下去过很长时间;而南曲也有自己“清峭柔远”的特点,占据丰富的地方声腔资源,在吸取北曲长处的基础上,渐渐兴盛起来。
南曲之中,代表性的声腔很多,有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原先与产生地域有关,后来也各自流布四处,热闹一时。相比之下,流布在吴中一带的昆山腔影响较小,但它有“流丽悠远”的特点,(徐渭《南词叙录》:“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唯昆山腔止行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终于被戏曲改革家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看中,作为改革的对象。
对于由魏良辅领头的这场有很多人参加的昆腔改革,有一些具体的记载留了下来,例如——
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之南关,能谐音律,转音若丝。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之属,争师事之惟肖。而良辅自谓勿如户侯过云适,每有得必往咨焉。过称善乃行,不即反复数次未厌。时吾乡(这段记载的作者张大复也是昆山人。“吾乡”即昆山。)有陆九畴者,亦善转音,愿与良辅角,既登坛,即愿出良辅下。
梁伯龙(即梁辰鱼)闻,起而效之。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芋》、《浣纱》诸曲,又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陈梅泉五七辈杂转之,金石铿然。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焓之家,而取声必宗伯龙氏,谓之“昆腔”。
张进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辅校本,出青于蓝,偕赵瞻云、雷敷民,与其叔小泉翁,踏月邮亭,往来唱和,号“南马头曲”。其实禀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为均节,昆腔之用,勿能替也。其后仁茂、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问常为门下客解说其意。仁茂有陈元瑜,靖甫有谢含之,为一时登坛之彦。
李季鹰则受之思笠,号称谪派。(引自张大复(1554—1630)《梅花草堂笔谈》卷十二“昆腔”条。)
魏良辅……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盖自有良辅,而南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沈宠绥:《度曲须知》。)
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者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余怀:《寄畅园闻歌记》,见《虞初新志》卷四。)
这场改革,首先与伴奏的乐器有关。本来南曲诸腔,多用锣鼓,没有管弦伴奏,有时用人工帮腔,即李渔所说的“一人启口,数人接腔”。据明末宋直方《琐闻录》记载,在魏良辅准备对昆腔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叫张野塘的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张野塘是河北人,不知犯了什么罪,发配到江苏太仓。他弹着从北方带来的弦索唱着北曲,早就习惯了南曲的太仓人听他唱得奇怪,都笑他。太仓离昆山很近,一天魏良辅到太仓去,听到了张野塘的歌,十分吃惊,连听三天,大为称赞,便与张野塘交了朋友。当时魏良辅已经年过半百,膝下有一个女儿也善于歌唱,不久便许配给了张野塘。张野塘从此又学南曲,让弦素来适应南曲,并改造了三弦,称为“弦子”。在这之后,一个叫杨仲修的人又把三弦改为提琴,听起来柔曼婉扬,人称“江东名乐”。(叶梦珠:《阅世编》卷十“纪闻”。)
由此开始,昆腔形成了以笛为中心,由箫、管、笙、三弦、琵琶、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
伴奏效果大不一样,而昆腔本身也变得愈加好听了。大家把这种精雅、细腻的唱法称作“水磨调”。
但是,改变了伴奏方式的昆腔,开始还只停留在散曲清唱,演戏时仍然只以锣鼓伴奏,直到梁辰鱼写出了在文句唱口上适合新的昆腔演唱的剧本《浣纱记》,才算树起了里程碑。
昆腔的多方面改革,在演出《浣纱记》时作了综合性的呈示,梁辰鱼不仅把魏良辅的实验投之实用,而且以一种崭新的、完整的艺术实体流播开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昆腔改革的巨大声誉,是由梁辰鱼和他的《浣纱记》挣得的。(《渔矶漫钞·昆曲》载:“昆有魏良辅者,造曲律。世所谓昆腔者,自良辅始。而梁伯龙独得其传,著《浣纱记》传奇,梨园子弟喜歌之。”)
这真是一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昆山梁辰鱼家里,“四方奇杰之彦”云集,丝竹管弦之声不绝。梁辰鱼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剧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舞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鱼,自己也觉得不太像话。(参见徐又陵:《蜗亭杂订》。)过一阵,他们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赶到苏州或别的城市,参加定期举行的“声场大会”,赛曲竞唱,广会艺友,真可谓一片喧腾。
其中,最能表现全社会对昆腔艺术欢迎程度的,是万历年间一年一度的苏州虎丘曲会。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和张岱(1597—1679)对此都有激情洋溢的描写。八月中秋夜,等月亮上升,虎丘满山是人,万人齐唱同场大曲,然后开始竞曲,赛出优胜者数十人。二更时,竞曲选手只剩下了三四人。至三更,只剩曲王一人了,只听他“声出如丝,裂石穿云”。除唱曲外,新编的传奇也会在那里演出,据说曾出现过“观众万人,多泣下者”的情景。
至明天启、崇祯年间,昆腔更成为官僚士大夫痴迷发狂的对象。以苏州为中心,南京、北京、杭州、常州、湖州一带,家庭昆班和职业昆班林立,有些人几乎到了“无日不看戏、看戏无日夜”的地步。职业昆班在城乡间演出时的轰动程度,有些记载简直很难让后人相信。然而,不管怎么说,昆腔昆剧在社会各界造成的长时间痴迷,肯定是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