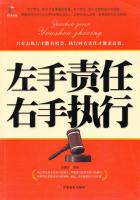②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第6页。
另外,在制度与人格的相互作用中,两者的地位在不同时期是不等的。个体人格在发育过程中,制度给予人格的影响较大。当个体人格成熟、定型之后,并呈现出创造性一面时,它往往会对制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制度内的人格与制度外的人格
面对制度施加于人格的可能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个体人格就有一个生存策略的抉择问题:是选择生活在制度之内还是之外?这个问题为我们划分不同的平民化人格类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现实的角度看,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总是生活于现实世界中,而制度作为一种抽象系统已经遍布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度,包括惯例、习俗等,在某种意义上与存在、生活几乎属于同层次的范畴,因而个体人格总是处于制度之中,在制度框架内活动。但是,从个体的生存策略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在理论上区分两种类型的人格,即制度外的人格与制度内的人格。这两种类型如果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就变为制度外的知识分子人格与制度内的知识分子人格。把知识分子区分为制度内与制度外的说法可以借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的观点。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把知识分子区分为圈内人(insiders)与圈外人(outsiders)。
萨义德说,圈内人完全属于那个社会,没有感受强烈的异议。与此相应,制度内的知识分子人格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人格服务于、依附于制度,人格的独立性体现在对制度的论证上。他们常常为制度辩护,替制度说话。这有两种情况。第一,新制度创建初期,一些知识分子为新制度的产生呐喊助威,写文章作讲演,为制度的现实性辩护。第二,在制度建立和成熟之后,知识分子成为制度的一份子,成为一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他们享受着制度给予的种种好处,成为制度的受益者。自然地,他们就会加倍为制度辩护。有时候我们称这类人为“御用文人”。
置身于制度之内的个体比较容易失去人格或自我,成为制度的精神奴隶,用巴金的话说就是“奴在心者”,成为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①摆脱这一现象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挣扎过程,巴金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②巴金的心灵挣扎过程可以看作是走出制度内人格而走向制度外人格的过程。
上述例子表明:制度内的知识分子人格有时候面临人格扭曲的境地。一方面,他所属的制度灌输给他一整套意识形态或标准语言,他必须运用这些公共语言来论证制度的正当性,为制度说话。在此处境中,他几乎无法逃遁,尽力使自己的语言和思想符合一定的格式和制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可能又有自己的思考和语汇,每一个个体都是具体的,有血有肉有生机的,在长期的灌输或服从中多少产生些许厌倦或怀疑意识,但是制度又不允许他自由地表达,甚至不允许他自由的思考或按自己的方式行事。长此以往,两方面的冲突会越来越加剧,使其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从而使其人格变形乃至扭曲。
所以,萨义德指出,“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他说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提醒自己,“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或权威来引导之间选择”,③时刻保持警惕性,避免完全陷入体制而成为一个体制的环节或零件。
①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第169页。
②同上,第173—174页。
③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第100—101页。
从列奥·施特劳斯的视域看,摆脱制度与人格之间矛盾激化的一个好方法是尝试两种写作方式,在同一个文本里使用两种语言:即俗白教诲(theexotericteaching)与隐讳教诲(theesotericteaching)。俗白的教诲不会使制度内的知识分子遭致制度的过度压抑,隐讳的教诲既曲折地表达了真理,又可以使知识分子的人格不致于过分变形。
萨义德在谈到圈外人(制度外的人格)的特征时,使用了“流亡”这个隐喻。此隐喻揭示出作为圈外人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生存状态:“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①这类知识分子人格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永远无法与新环境融合为一体,时时处于煎熬之中。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是这类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不妥协的批评意识。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保持对既定社会制度的批判。
萨义德关于两类知识分子的分析虽然深刻,但是过于简化。如果我们仔细检视圈外人的生存策略与人格取向,作为圈外人的知识分子人格或制度外的知识分子人格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类指批判型的人格。这类人对制度持批判态度,往往直面制度的弊端,或激烈或温和,当然很多时候他们成为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人格的独立性体现在对制度的批判上,鲁迅大概可以算是这类人格的代表。
①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第48页。
②同上,第14页。
Ju1ienBenda按照班达的看法,这类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心,“他们必须是具有坚强人格的彻彻底底的个人,尤其必须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②即处于批判状态。班达的观点过于极端,相比之下,萨义德的看法比较中肯。一方面,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批评意识,他说:“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乱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①一般来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接近决策层,服从于权势,“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相当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精神的;而这种精神在我看来却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贡献”。②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的角色是质疑提问而不是顾问。另一方面,除了批判意识外,知识分子要有一种代表(rePresenting)意识,往往是公理正义的代表,是弱势者的代表,“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③同时,知识分子的代表功能不仅呈现为意识,而且要化为行动,应该“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④只有这样,知识分子的代表功能才得以真切的实现。
第二类指旁观兼辩护型的人格。这类人虽然游离于制度之外,但仍然被视为制度的辩护者。他们常常以一个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为制度说话,甚至粉饰。例如胡适多次拒绝参加政府工作,他申明的一个理由是:站在政府之外,可能更好地为政府服务。
第三类指独立型人格。这类人真正站在制度之外,几乎不与制度发生关系,守卫着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人格操守,做一个人格的自我实践者。这类人往往不具有公共的角色,似乎表现出不承担社会与历史的责任的样子,守护着自己的良知。
这类人有点类似萨义德所言的边缘人的角色。他说,“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因为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⑤边缘人具有自创性,常常依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不跟随或附和别人的意见,把孤独当作自由,把自己的兴趣当作人生的指引。
①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第25页。
②同上,第75页。
③同上,第16—17页。
④同上,第17页。
⑤同上,第14页。
二、习惯与制度
上文从含义、相互作用、人格类型等三个理论视角解说制度与人格的关系,这里以梁漱溟关于习惯与制度的论述为个案继续分析两者的关系。视角有所转移,但论述的主线不变。
梁漱溟在思考社会文化问题时注意到制度与习惯的关系。“习惯”在梁漱溟那里可以作多重理解。一是从普通意义上理解,“习惯”指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固定的做法、路子、方式等。如一个人写字有他自己的习惯,一笔一划与别人不同。二是从深层的角度看,“习惯”更多与内在态度、精神、人格联系在一起。同时,“习惯”是可见的,具有在场性。“习惯”所表现的正是内在精神自我与外在的规范的统一。他说:“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①这里的“习惯”从精神、思想与规范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可能更恰当。所以,他对制度与习惯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制度与人格(及其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
这一界说并非没有学理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习性”(habifus)的概念,和梁漱溟的“习惯”概念大致相当。布尔迪厄所说的“习性”指的是内化了的社会性的行为、感知图式,是积淀了的社会规范与文化模式,“是知党、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二系统,它共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②。布迪厄是在社会学的语境内使用该术语,如果我们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看,这个“习性”也可以理解为人格。作为习性的人格指的是人的精神领域中比较固定的、连续性的内在自我,同时也指以规范形式出现的外在自我,是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统一。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借此界定梁漱溟的“习惯”概念。
①《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20页。
②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71页。
在制度与习惯的关系上,梁漱溟的认识经历了几次转变。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他认为中国的振兴有必要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后来他放弃了这一思路,他“深悟到制度是依靠于习惯”。①认识到中国人的态度和文化精神与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适合的,两者属于不同的类型,因而他“不再去热心某一种政治制度表面之建立,而完全注意习惯之养成”。②如果没有培育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心理基础或习惯,整套制度是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这是第一次思想转折。
后来他又觉悟到上述看法仍然有问题。不仅西方制度在中国建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中国养成与西方制度相匹配的习惯或人格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民族精神是不同的。这里的民族精神包括传统习惯和内在文化精神两层意思,落实到个体上就表现为人格特征。人格特征之间的差异构成东西方制度之间最为根本的阻碍。基于此认识,他认为应该另求民族自救的途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乡村建设,觉悟到应该在乡村培养适合新制度的习惯,但这是中国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一切西方制度都用不上,“吃现成饭是不行的”,只有靠自己的创造。这是第二次思想转折。
从这两次转折中,可以看到他的基本观点是:习惯或人格构成制度的价值基础,习惯的缺失意味着制度建设的不可能。正如其所言:礼俗制度“大抵出在人们的心理习惯之间”。③“西洋近代制度之辟造,虽有种种条件缘会之凑合,然语其根本,则在其新人生态度。”④人生态度或人格构成制度的根本。
他对制度与人格关系的另一面即人格的发展也有赖于制度也有一定的认识。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制度或形式中,生活在真空中的人是不存在的。制度或形式对人格的培育和养成具有深远的导向性作用,制度总是包含着具体的规则或要求,这些规则与要求对人的行为和思想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久而久之,它们可能内化、积淀为人格的基本因素。因此,人格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度为基础的。
①《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19页。
②同上,第21页。
③《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670页。
④《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147页。
上述两方面的结合形成制度与人格(习惯)之间的相互作用。犹如布迪厄的看法,作为习性的人格不仅是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系统塑造的结果,同时他也在改变着生活世界,创造着新的社会文化。两者之间形成互相建构的作用。因此,人格具有成长性与可塑性,同时又具有创造性。
立足于制度和习惯(人格)的相互作用,梁漱溟对民主作出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或习惯。所谓民主精神主要有五点,即承认旁人,彼此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①这些习惯的养成比任何一个制度都重要。“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②现代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是公共空间话题,对民主习惯问题注意较少。梁漱溟在这里谈民主的精神或习惯,无疑具有前瞻意义。对民主的理解也比同时代人更深刻。当时不少人认为民主就是普选制、政党制等,从制度层面看民主。
不过,梁漱溟对道德人格过于相信。以为靠人的道德约束力就可以达到制度监督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长在于伦理观念,伦理约束的观念和西方的制度约束观念有着根本的差异。因此在中国没有产生权利制衡机制的理论基础和条件。“由伦理关系的推演,而在中国政府与其人民之间,乃无由形成相对抗衡的形势。从而更不能有拥护权利平等的法律,维持势力均衡的制度。”③他认为西方的权力制衡机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在中国,人们更看重的是对礼的维护,礼更多表现为道德规范。
更进一步,他相信贤者的道德人格可以引导团体生活的进步。“在这样的团体生活中,天然的不以法为最高而以人为最高,因为他是从人生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一个动机来的,所以自然要尊尚贤智而不以法为最高,不以多数为最高。”④法或制度不是最高境界,而他所谓的政教合一就可以帮助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①政教合一中的“教”兼有教育与教化的意义,突出的是道德与人格的教化。这个说法表明梁漱溟把人格精神置于制度之上。
①《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444页。
②同上,第491页。
③《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160页。
④同上,1992,第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