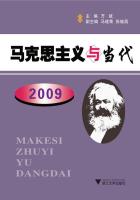在他的观念里,中国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始终是连在一起的。他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不仅是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也是解决人生的问题。他的政教合一的制度设计最终是想帮助解决人生问题的。如果把这一想法放到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下来看,立即获得了后现代的意义。他看到了现代人对人生意义探究的忽视和现代人格的裂变。人生境界提升是一个被现代人遗忘的话题。梁漱溟拾起现代人生意义和人格问题,提醒人们注意制度背后的人格精神和人生态度问题,不要沉溺于制度的民主性和合理性之中,而忽视了人格的整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所设想的现代中国社会首先是一个人格健全的社会,而不仅仅是有一套完善民主制度的社会。
如果把人生和政治看作满足人的欲望,西方法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是有效的,如果把人生看作是向上追求的,那么采取人治的办法是有效的。人群中有智愚等差别,遇到人生问题需要求教于贤者,走政教合一的路,这是“少数领导的路,而非多数表决的路”。②在他看来,在西方,民主与法治结合,但这不适合于中国,在中国,人治与民主是可以调和起来的,他称为“多数政治的人治”。他把贤者作为引领众人的民主斗士,以贤者的人格风范和人生体验来指引众人。
上面在理论层面上阐释制度与人格之间关系,并以梁漱溟的相关论述为个案。回到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人格层面,随着现代工业化和民族革命的发展,现代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就制度与人格的关系来说,在古代儒家社会,圣贤人格与制度的密切关联表现在:圣贤人格是制度的立法者,提供理想价值目标与精神动力,平民只是顺从或模仿圣贤人格,向他靠近,没有制度的立法权,只有遵从制度的义务。在现代社会,人格图景倒转了,圣贤人格逐渐遭冷落,平民化人格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一个表现是:圣贤人格丧失制度的立法者地位,平民化人格成为制度设立的参与者和阐释者。平民不再外在于制度,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他们或者他们的代表始终是制度的设置、执行与实施的参与者。平民不仅在道德上有人格的尊严,而且在法权上有人格的地位。平民化人格不仅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且还获得了社会政治哲学的意义。因而平民化人格与现代制度有着更为直接和内在的联系。
①《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690页。
②同上,第283页。
如何更好地揭示平民化人格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呢?笔者在此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抓住妇女制度和教育制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制度对人格的影响。在现代中国,这两个制度的变革都对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具有典型的思想史意义。例如,现代妇女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生存方式,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迫使人们反思女性人格与女性的真正价值。又如,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不仅改变了知识的生产、传播方式,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且改变了普通人的世界观———人格结构和生活方式。
下面将通过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来阐释传统妇女制度的变革对妇女人格的影响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对平民化人格的影响。
三、妇女制度变革与女性人格的话语
在“五四”前后,妇女解放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妇女人格问题是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讨论的社会问题。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表达了对传统的妇女制度的不满。他们认为,传统的妇女制度极大地压抑了女性正当人格的成长。妇女的解放有赖于旧制度的解除和新制度的开创。联系制度批判来进行人格批判,是“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讨论的一个方法论特征,因而也成为我们解读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建构理路的一个基本视角。
具体地说,妇女制度问题关联到家庭制度、贞操制度、婚姻制度等,我们将分析这些制度对女性人格的压抑。最后还将讨论女性人格解放的几种途径。本节的分析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的文本与论说为依据。
一、家庭制度、男权话语与女子人格的挺立
胡适激烈地批判了传统的家庭制度对妇女人格的压抑。这种批判通过为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学生李超立传传达出来。李超的父母双亡,过继的哥哥逼她嫁人,她不从,以外出求学反抗来自家庭的威胁,从广西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但是她家里以断绝经济资助为由逼她辍学,她气愤不已,加上身体虚弱,最后患肺病而死。死时才23或24岁。
胡适破天荒地为这样一位弱女子作传。到底是什么吸引胡适的目光为李超写传记呢?是李超短暂而悲惨的一生?不完全是。胡适在《李超传》中说:研究李超事件的目的在于:“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①这里胡适提到了家庭制度与女权问题。胡适把李超看作是一个女权主义的代表,传统家庭制度是男权话语的代表。她对家庭的抗争,她对读书的渴求,显示出一个现代女权者的活形象,一个类似娜拉的、试图颠覆男权话语的形象。这个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女性独立人格的诉求。
胡适从李超事件中引出四个问题:家长族长的专制、女子教育问题、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制度的问题。第一个涉及家长在家庭中的专制制度问题。在旧式的家庭中,妇女必须听从丈夫或父兄,“三从四德”就是一例。服从是妇女的人格品格之一。第二个涉及的教育制度问题。在古代社会,平民女子基本被拒斥在教育之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就是一个写照。“无知”也成为妇女的人格品格之一。第三个涉及家庭财产的继承分配制度问题。在古代,出嫁了的女子一般不再享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兄弟全权支配遗产的处置。因此,妇女在家庭中不可能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在经济上妇女只能依附于男子,这决定了传统妇女的依附性人格。第四个涉及宗法社会的后嗣制度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相连,因为女子不能被算作是后嗣,所以不具有财产的继承权。在家族谱系中,没有女子的位置。在男权话语系统中,女子是无足轻重的,可有可无的。这种可有可无的地位也决定了妇女的顺从性人格。
①《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第564页。
这四种家庭制度代表着四种形式的男权话语,合起来构成男权话语中心主义。男性操控着家庭制度的制订、运作与解释。这些男权话语从不同的方面压迫着妇女,使妇女的人格得到扭曲,服从、“无知”、依附、顺从成为古代女性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表征出旧式女性的无人格困境。在男权话语及其制度的支配下,妇女成为传统家庭制度的牺牲品,这些制度日复一日地生产着依附性的、无话语权的妇女人格,由此,制度对人格的负面作用可见一斑。怪不得胡适感叹:“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至于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①胡适从李超事件中看到的恰恰不是李超个人的悲剧,而是所有妇女在男权制度下的人格悲剧,而是传统家庭制度对妇女人格的消极作用。
胡适在批评传统家庭制度对妇女人格压迫的同时,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因为李超毕竟是一个抗争者,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已经脱颖而出。她在抗争“吃人”的家庭专制制度,离家出走,四处求学。她也在寻求新的人格品格,试图挺立自己的人格。不幸的是,她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斗不过家庭专制制度的宰制而成为牺牲品。但是,李超的行动毕竟透露出一丝曙光,它将导向妇女新人格的挺立。这是李超事件留给我们的希望,也是胡适写《李超传》的希望。从李超身上,胡适看到了突破男权话语中心主义的希望。
①《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第564页。
陈独秀和胡适一样,也很关心李超事件。胡适从李超事件中看到了整个家庭制度及其男权话语系统对妇女人格的压迫。胡适所谓的家庭制度包括了家长族长的专制制度、女子教育制度、女子的财产承袭制度、宗法社会的后嗣制度。与胡适稍有不同的是,陈独秀直接从经济的角度来批评旧制度对妇女人格的压抑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石,经济制度决定着文化的、人格的因素。可以说,陈独秀的批评抓住了李超事件的核心和根本,因而其批评也比胡适的更犀利。
陈独秀从李超之死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是制度的局限害死了李超。一个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男系制相对于母系制。在远古时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着主要角色,外出劳动维持家庭的生计。这个时候母系掌权,盛行母系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作用日益凸现,男子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宰。渐渐地,女子的地位日渐下降,不仅不能与男子平起平坐,而且男子把女子变为了私有财产,变成了物。这样,男系制和经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陈独秀说:“自从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所以女子底身体便不能归自己所有......既是个人的所有物,便和别的动产不动产一般,所以他的物主任意把他毁坏,赠送,买卖,都不发生什么道德的,法律的问题。”①在古代男系制社会,女子是私有财产,是物,不是人,道德原则不适用。既然妇女不是人,自然就没有人格,只有任人处置的物权。
另一个制度是遗产制,这与前面的男系制密切相关。因为在宗法社会,妇女没有地位和人权,只有长子或嫡子才有继承权,妇女被剥夺了遗产继承的权利。遗产制度规定了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人格身份。
当时有不少人指责李超的哥哥,因为是他硬逼着李超弃学结婚,断了李超的经济来源。可是陈独秀却说,这事“不能全怪他”。李超之死“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②明确地说,是社会制度问题。制度压抑人格,最终把人害死了。这不仅是男权制度与男权话语中心主义的弊端,更是私有制经济的祸害。陈独秀见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透视李超事件,看到了人格悲剧产生的经济制度根源。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第579页。
②同上,第581页。
从对李超事件的评判中,陈独秀把妇女人格受压迫的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制度问题。他说:“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①经济是人格问题的根源。经济的不独立与男系制度和遗产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妇女经济地位不可能独立,人格也就不可能独立。李超是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社会上的女子,无论从父从夫,都没有独立的人格;靠父养的,固没有人格,靠夫养的,也没有人格。所以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②在传统社会,妇女的所有生计只能靠家庭。经济上的依赖决定了人格上的依附。可以说,李超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
陈独秀认为,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条件。新型的女性人格要求把女人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人,这需要从制度上得到保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提出要改革遗产制度和男系制度,解除压在妇女身上的旧制度,使妇女获得解放,获得话语权,不仅使妇女在经济上独立,人格上也独立。
二、贞操制度、夫权话语与男女人格的平等
在传统妇女制度上,贞操习俗对妇女人格的压抑深重。胡适对贞操问题的关注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嘉奖烈女的法律制度有关。当时报纸上报道了几件烈妇贞女的事件。例如,《中华新报》报道唐女士在丈夫死后,历尽9次自杀,终于成为烈妇。上海的报纸报道一位陈烈女殉夫的事件。这位女士才17岁,当其得知未谋面的未婚夫病死的消息,便服毒自杀,她死时距离未婚夫之死只有3个小时。上海县知事呈请江苏省长要求对陈女之行为予以表彰,授“贞烈可风”的匾额。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268页。
②同上,第269页。
胡适发现,官府的表彰居然是有制度依据的。原来民国政府曾经颁布过《褒扬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几种值得褒扬的行为,其中一种为“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那么,如何界定节妇、烈妇烈女和贞女呢?该条例的《施行细则》也作了详细的描述。例如,什么样的女人叫节妇呢?妇女守节年限必须从30岁以前到50岁以后。这等于说,30岁以下的寡妇不可以再嫁。什么样的女人叫烈妇烈女呢?遭遇强暴不从而致死,或羞忿自尽的女人是烈女,为亡夫殉节的女人是烈妇。这等于是鼓励遭暴的女子自杀以殉夫。什么样的女人叫贞女呢?未嫁女子必须为死亡的未婚夫守节20年以上才是贞女。胡适气愤地说,以上三条中国的法律“明明认三十岁以下的寡妇不该再嫁”,“明明鼓励妇人自杀以殉夫”,“明明说未嫁而丧夫的女子不该再嫁人”。在胡适看来,这些关于女子贞操的制度性规定,“没有成立的理由”。①
胡适于是通过三个角度批评传统的贞操制度。
第一,指出贞操制度不是亘古不变的,是可以讨论和推敲的。贞操的背后是人格问题。人格问题的讨论将把贞操制度问题的讨论推向更深层次。胡适说:“娜拉弃家出门,并不是为了贞操问题,乃是为了人格问题。”“人格问题是超于贞操问题了”。②这是说,人格是比贞操更重要的问题,是贞操制度的基础。
第二,提出新的贞操定义。他说:“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③这个定义包含两个意思,一指贞操是一种约束,是道德上的规约,体现人格的品格;二指贞操是双向的,对男女双方都起作用。例如,如果丈夫可以嫖妓娶妾,不守贞操,那么妻子就不一定要为这样的丈夫守贞操,而且,社会对这样的丈夫的惩罚,和对待不贞妇女的惩罚应当是一致的。
这个贞操定义具有两个意义:第一,它肯定了男女人格的平等性和相互性。男子对女子要守贞操,女子对男子也同样对待。而在旧的贞操制度下,男子可以不讲贞节,而女子却必须谨守妇道,为男子守节守名分。这样,男女的贞操关系是不对等的,是单向的。胡适对贞操制度的重新解释曲折地表达了人格平等的观念,无疑肯定妇女人格与男子人格具有一致性。第二,这个新定义也表明女性应与男性争夺贞操问题上的话语权。旧的贞操制度表征出夫权话语的至上性,夫权享有绝对的自由与权威,而女性成为满足夫权欲求的工具。话语权的丧失也折射出人格的丧失。新的女性应主动争取男性为自己守贞操的权利,至少和男性平等享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