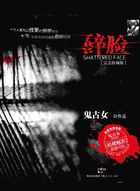我恐怕从来也没那么快地爬上这最后几级危险得要命的楼梯了,心剧烈地跳着,气也差点儿喘不过来。可当我到了瞭望台上,前面一下子出现耀眼的蓝天,我便身不由己地愣住了,目光越过了铁栏杆。我看见在自己脚下很深很深的地方,我的故乡静静地躺着,城中已呈现出一派春意。在一片屋顶的海洋中,这儿那儿地挺立着一棵棵高大的樱桃树,让温暖的春风一吹,便已繁花满枝。在市政厅小钟楼的对面,有一座山字形屋顶,它底下便是我那监护人的家。我眺望着他家的花园和园后的道路,心中充满了离愁别恨,情不自禁地长叹了一声。这当儿,我蓦地觉得有谁拉住了我的手,抬头一看,身边站着阿格妮丝。
“哈勒,”她说,“你到底来了啊!”说时她脸上漾起了幸福的微笑。
“我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我回答,“可我马上就得离开,你干吗昨晚上让我空等呢?”
这一问,她脸上的笑意全然消失了。
“我当时不能来,哈勒,我父亲不让我抽身。过后我跑进花园,可你已经走了。我等你,你没再来。所以今儿一早,我便爬到钟楼上——我心想,我总该目送着你走出城门去吧。”
我当时前途茫茫,但心里总算有个计划。从前我在一家钢琴厂里干过。眼下又希望找一个同样的工作,挣些钱,往后自己也开一家制造钢琴的作坊,那年头这种乐器正开始大兴其时。我把计划告诉了姑娘,并讲了我最先打算去的地方。
她的身子俯在铁栏上,怅惘地望着渺茫无际的天空。半晌,她慢慢地转过头来,声音低低地说:
“哈勒,别走啊,哈勒!”我望着她答不出话来,她又高声喊道:“不,别听我的,我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晨风吹散了她金色的发辫,把它吹到了她耐心地仰望着我的脸上。
“咱们必须等待,”我说,“眼下幸福存在于遥远的远方,我要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它回来。我不会写信给你,只要时候到了,我自己会回来的。”
她用她那对大眼睛望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握住我的手。
“我等着你。”她语气坚决地说,“愿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哈勒!”
可我并没有马上走。眼前这托负着我俩的钟楼,是如此孤单地耸立在蓝天下,只有那一只只铁青色的翅膀在晨曦中微微闪光的燕子,在空气和光的海洋中游弋。我久久地握着她的手,心里觉得自己仿佛可以不走了,仿佛我俩,她和我,这时已经摆脱了人世间的一切苦恼。然而时光催人,我们脚下的巨钟轰鸣着,告诉我们一刻钟又已过去。钟声还在塔身周围缭绕,蓦地,一只燕子飞过来,翅膀几乎擦到我们身上,毫无畏惧地在我们伸手就可抓着的栏杆沿上停下来。在我们像中了魔似的盯着它那闪闪发亮的小眼睛的当儿,小家伙突然放开喉咙,望着天空唱开了春歌。阿格妮丝一头扑进我的怀里。
“别忘了回来啊!”她喊着。刹那间,那只鸟儿便一振翅飞走了……
我已想不起,我是怎样从那黑洞洞的钟楼里走下来,到了平地上的。在城门前,我又驻足在大路边,回首仰望。在那阳光朗照的高高的钟楼上,我清楚地辨出了她那可爱的身姿。我觉得她远远地探身出了栏杆,不禁失声惊叫起来。可她呢,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终于,我转过身,沿着大路快步走去,再也没回头。”老人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她白等了我一场啊,我自此再没有回去。我这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您。”最初我在维也纳找到了工作,那儿有最好的钢琴厂。一年半以后,我从维也纳到了威腾堡,也就是眼下我定居的地方。我厂里一个工友的哥哥当时住在那儿,人家曾托他帮忙介绍一个可靠的伙计去。我去的这家主人,还是一对年轻夫妇。作坊虽很小,师傅却是一个和气而能干的人。在他手下,我很快便学到了更多的手艺,而在大厂子里,人家却总让我干些零碎活计。我卖力地干着,并把在维也纳积攒的一些经验也用上了,因此不久后,便博得了两位好人的信赖。特别令他们喜欢的是,我在工余还教他们两个男孩中大的一个学德语。没过多久,小的一个男孩也开始学起来。这时,我已不仅教他们语法,而是还设法弄来一些书,常常从书中念各式各样有趣而带知识性的故事给他们听。这样一来,两个孩子都很依恋我。一年以后,我独立造出了第一架音色异常优美的钢琴。这成了全家的大喜事,就像是他们的一位最亲的亲人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似的。可我呢,却想到自己该回家啦。
谁料想,我年轻的师傅这时却病倒了。感冒终于转成肺炎,但病根可能是早已在身体里埋下了的。作坊的营业自然归我照管,这一来我便脱身不得。我和这家人结下了越来越亲密的友谊,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深感忧虑。全家大小和睦而勤劳,可屋里却住进来了一个凶恶的第三者,善良的人们怎么赶它,它也不肯出去。在任何一个阳光暂时照不到的角落,病人都看见它蹲着——这家伙就是忧愁本身——‘快拿扫帚来扫它出去,’我常常对我的朋友说,‘我会帮助你的,马丁!’这时候,他多半会握住我的手,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凄苦的笑意,但过不了多久,他又会在所有的东西上看见黑色的蜘蛛网。
可悲的是,这并非纯属幻想。他用以开办作坊的资金,原本就嫌少了一些。且不说头几年,他尽雇到一些拆烂污的人,吃了不少的亏,就说制成品的销售吧,也嫌太慢,再加上如今又来个一病不起。临了,我一个人不仅要为全家的生计操心,而且还必须安慰几个健康的人。师傅没多久便下不了床,每当我和孩子们坐在他的床沿上,他们就抓住我的手不放。病人呢,像是体力越衰竭,精神倒越活跃似的。他的头靠在枕头上苦思冥想,谋划着将来的事情。有几次,他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陡然一下坐起来,大喊大叫:
“我不能死!我不想死!”但接着,又合起掌来,低声地道,“主啊,主啊,如果你要我死,我也愿意!”
解脱的时刻终于到来,我们全都聚在他的床前。他对我表示了感谢,并一一与我们诀别。可后来,他像突然发现面前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便猛地一把将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儿子揽到身边去保护起来,眼神凄惨地望着他们,发出大声的悲叹。我于是劝他:
“别再发愁,马丁,把他们托付给上帝吧!”可他却绝望地回答:
“哈勒,哈勒,这已经不是忧愁,而是贫困本身!它马上就会从我尸体上爬过来。我的老婆,啊,还有我可爱的孩子,他们都将逃不脱贫困的魔爪啊!”
“人在临终时的情形是很特别的,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一层,年轻的朋友。当时,我便答应我那奄奄一息的师傅,我要一直留在他妻儿身边,直至这个使他咽不下气的幽灵再也不能侵害他们。我的话一出口,死神马上溜进了房间。马丁手一伸,我还当他想和我握手哩,谁知却是让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使者攫住了。我还没来得及碰着他的手,我年轻的师傅已经一命呜呼。”
我的旅伴脱下帽子,放在怀中。正午温暖的微风吹动他的白发。他默默无声地坐了好一会儿,像是在哀悼他那早已亡故的友人。我不由得想起我的老汉森有一次对我讲过的话:“除去死亡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使人身不由己的事情哩。”然而,这使活着的人不能见面的,仍是死亡啊。很显然,我对坐在自己旁边的这个人是谁,已经一清二楚了。半晌,老人才慢慢戴上帽子,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他说,“可我在许下这个诺言的同时,却把另一个诺言给毁啦。情况很快表明比我一直想的还糟得多。丈夫死后没几个月,老婆又生了第三个孩子,一个女儿,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真是旧愁之上添新愁。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一年年过去了,境况仍不见好转。我不只尽心竭力,而且把自己几年来的积蓄也填进去用掉了,却还是没能战胜贫困这个幽灵。我清醒地看到,只要把我换成任何一个稍微不那么忠实细心的人,这归我保护的无依无靠的一家子便毁了。”自然,我常常干着干着活儿也想起家来,阵阵乡愁便会咬噬我的心。不止一次,我自己手里的凿子停住了还不知道,直到好心的主妇来叫我才猛然一惊,回过神儿来。要知道我的心那时已飞回故乡,耳际正响着另一个女子的声音。梦中,我常看见自己故乡城里的大钟楼:开始时是在阳光朗照下,周围飞着成群的燕子;后来再做梦时,却看见它黑糊糊的兀立在苍穹之下,被狂风暴雨袭击着,眼看就要倒了似的,耳边还听见大钟在一个劲儿地敲响,敲响。但不管开始也罢,后来也罢,阿格妮丝总是俯身在瞭望台的栏杆上,仍穿着为我送别那天穿过的天蓝色裙子,只是已经破烂不堪,一片片地在风中不停飘动。‘燕子何时再归来呢?’我听见她在呼唤。我听出这分明就是她的声音,然而在狂风吹打中,它听起来是何等的凄惨哟!——每当天蒙蒙亮,我从梦中醒来,多半都会听见有几只燕子,在我窗前的屋檐上呢喃。头几年,碰上这种情况,我总要撑起头来谛听,一直听到我的整个心田让乡愁给塞满;到后来,我就再也受不了啦,不止一次地拉开窗户,把那些啁啾个没完没了的可爱的鸟儿轰跑。
“就在这么一个早晨,我突然宣布现在我必须走了,现在终于到了该我考虑考虑自己生活的时候。我的话刚一说完,两个男孩顿时大哭大叫。他们的母亲则一言不发,只一下子把女儿塞进我怀里,这娃娃马上也伸出小胳膊来,把我的脖子紧紧抱住。我心疼这些孩子们啊,亲爱的先生,我丢不下他们。于是想,‘好,我再留一年吧!’这样,在我与自己青年时代之间形成的鸿沟,便越来越深,到最后,过去的一切都似乎再也不可企及,恰如一些不堪回首的旧梦。终于,我应已成年的孩子们的请求,和他们的母亲,这个长期以来以我为唯一依靠的女人结了婚。当时我已经四十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