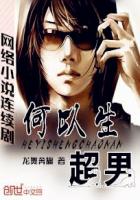四
第二天,各路使臣秉承密旨,一齐出京,乘传驿快马,分赴各地。
原来,当年像这样涉及全国的钦定大案,圣旨颁布的也十分机密。明初,各行省衙门分为三司:布政使司主管民事和钱粮;按察使司主管刑狱和督察;指挥使司主管军旅,互相制约,各自听命于朝廷。空印案因发在布政使司系统,所以密旨便降到主管刑狱的按察使司衙门。
这天,朝廷圣旨到了湖广按察使司,按察使司佥事郑士元暗道:“空印一事,由来已久,天下谁不知道,岂能为此大开杀戒!”然而朝廷圣旨,谁敢说个不字!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可巧此时胞弟郑士利来衙探亲,见兄长不似往常,询问究竟。起初郑士元碍于衙门的规矩,不肯说明,后来禁不住弟弟一再询问,只得叹了口气说道:
“如今朝廷发下一桩大案,牵涉天下各级官府千万人的性命,为兄为这些官员惋惜,因此才坐卧不宁。”
郑士利年方弱冠,秋闱时刚刚中了举人,来兄弟这里准备功课,好参加来年春天朝廷举行的会试。听兄长如此一说,不由吃惊,越发刨根问底起来。郑士元这才把空印案一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末了又说:
“当今圣上对官风看得极重,乍一听说,定然震怒,若日后醒悟过来,必然后悔。”
郑士利不解,说:“圣上或许一时不明真相,那些朝廷大臣们为何也不提醒。”
郑士元摇头:“朝廷内情,谁能知道!”
郑士利却问:“像兄长这样明白事理的命官,岂能无动于衷?”
郑士元叹道:“不是为兄贪生怕死,圣旨既降,便是舍身赴死,恐也难更改。”
郑士利越发争道:“难道就眼看着朝廷冤杀无辜不成?”
郑士元不由训道:“你年纪轻轻,晓得什么人情事理!还不回房念书!”
郑士利本是个才子,又年轻气盛,只想建功立业,却愁报效无门。如今听了兄长一席话,怎么也难以平静,心说,前不久朝廷还降旨命臣民尽可进京言事,要是将内情禀明,圣上未必不收回成命,果若这样,不是为天下办了一桩大事!激动之情,一时难以按捺。忽又寻思,人传圣上威严,若是触怒朝廷,降下罪来,那还了得!又有些犹豫。却又想,真要是得罪被杀,能救下千百无辜,也能落个流芳百世。当时一腔悲壮,连夜奋笔疾书,写成了本章,在灯下细细读了一遍,十分称意。第二天醒来,又重读一遍,却又由不得心惊肉跳。原来,这本章不是指摘时弊,却是匡正天子之失,若是圣上不容,不但自身难保,还会诛灭九族,不由真得犹豫起来。大凡那些才子多有的自信,反复展读了数遍,见自己说的都是实情,想到自古以来,多少仁人志士舍生赴死,不都是为了忠义二字!想到此处,将心一横,在表章下款郑重签了自己的籍贯姓名,装入信袋,沉甸甸托在手中,却禁不住泪往下流。欲救天下,舍我其谁!郑士利激情在胸,向兄长谎称赴他处游历,匆匆忙忙离了武昌,雇船顺流东下,直奔京师而来。一路人急船快,这天,早早来到午门跟前。正愁进不得宫去,忽见一旁架着一个大鼓,两个官员模样的人相对而坐,守在鼓旁,便想起朝廷门前原设有登闻鼓,不论是谁,均可击鼓奏事,况且自己这有了功名的人。于是上前抡起鼓锤,猛敲数声。两名御史果然殷勤上前问道:
“何方人氏来告御状?”
郑士利答曰:“在下是宁海人氏,无冤可诉,不过递一表章。”
御史见此人言语爽利,落落大方,又是书生打扮,不敢怠慢,说道:“有何表章,本官均可代奏。”
郑士利却道:“在下奏得事关重大,不见朝廷,不可明言。”
两个御史见此人有些来历,只得说:“如此容我等上殿奏明。”
两人一同去了。不一会儿,其中一个回来迎道:
“圣上有旨,即可上殿。”
郑士利见这般顺利,喜出望外,当下随引荐的御史进入午门,径直来到华盖殿前。只见满朝文武站在两厢,当今圣上影影绰绰坐于御座之上,虽看不清脸面,却已感到朝廷的威严。郑士利少年得志,又有才情,平素十分自负,此时此刻不由也生出几分怯心。见前面引导御史早早跪在阶下,连忙跟着跪倒,就听御史奏道:
“他就是击鼓的书生。”
朱元璋听了,传旨命击鼓人禀明身世。
郑士利连忙奏道:“书生郑士利,本宁海人氏,此番千里来朝,有一事欲奏明陛下。”
朱元璋点头。问:“欲奏何事?”
郑士利忙奏:“为空印案阐明真情。”
朱元璋皱起眉头,朝廷刚刚降旨,有什么本奏?冷冷问道:“有何言语?”
郑士利鼓足勇气:“小人有表章在此。”
朱元璋更不耐烦。这时,早有内侍下来,从郑士利手中把表章接了,捧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待内侍将表章摊开,就见上面写道:
“陛下重罪空印之人,不过唯恐奸吏使用空印纸为害百姓。然而官府文书必加完印方可生效,今核定钱粮的薄册,用的都是骑缝印,绝非一纸一印,纵然不良之人蓄意为奸,亦不能行文,何况常人难以获得。再者,钱粮钱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不许有任何差错。而省、府离京师远者数千里,若一旦不合,重新用印,往返一趟,有的非数月不可。因此各地先用印后书写,不过权宜之计,且此情由来已久,何足深罪!何况国家立法,必先告示天下,而后才绳之于得罪之人,因其明知故犯也。而自从立国至今,不曾有空印之罪,历年相承,不知其谬。今一旦诛之,何以服人!朝廷虚位求贤,本来不易,位至郡守,非数十年不可成就,今一概奢戮,绝非草木今刈而明日复生。陛下为何以不足之罪坏足用之材?故此窃为陛下惜之。”
朱元璋勉强看完,记不得内中的言语,只觉得小小孺子,竟敢如此对朝廷指点数落,简直大逆不道,一时忍无可忍,一迭声降旨:“大胆孺子,年纪轻轻,竟敢无视朝廷,真真一个乱臣贼子,还不拿下!”
郑士利呈上表章,心里七上八下,见圣上果然发下天威,顿时凉透。当时身不由己,不容分说,被武士掳出殿外,捆了手脚。
朱元璋忍着怒火,又匆匆将表章看了一遍,心中纳闷,一个书生,对空印案何能知道得如此详细?必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当下又追了一旨:
“御史台与刑部仔细审问,务必究出背后唆使的恶人。”
新任左都御史詹徽、刑部尚书吕宗艺忙出班接旨。
朱元璋吩咐完毕,含怒将郑士利的表章发给殿前文武依次传看。恨道:“朕鉴于胡陈乱党多年来祸国殃民,决心整肃天下,为民除害,谁知孺子秉承他人之意,竟敢抗拒朝廷,巧言惑众,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时,站在武班班首的曹国公李文忠已将表章看完,再听朱元璋的话,颇不以为然。李文忠自幼以公子身份长在朱元璋帅府,熟读经史,教养颇好。后来戎马倥偬之余,仍攻读不辍,因此是本朝一员儒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为天子至亲,又是开国功臣,却能礼贤下士,爱与文人交往,平时耳濡目染,大有君子之风。大明开国后,他受命掌管天下军马,但对政事也十分关心,圣上追究空印一事,起初并不明内情,后来听了自己府上几个门客的述说,方知道圣上有些小题大做。如今看了郑士利的表章,见里面句句全是实情,心想,岂能因言语尖刻就治人以罪,长此以往,谁还敢言是非?心中虽然如此,在朝上却不敢奏明,待散朝之后,才随朱元璋退居便殿,小心奏道:
“朝上的事,臣有所虑,不敢不奏明陛下。”
朱元璋一听便知道是为郑士利一案,含怒不语。
李文忠鼓足勇气:“臣以为郑士利奏得不无道理。”
朱元璋勃然变色:“空印一案,可知始末?”
李文忠小声奏道:“臣略知一、二。”
朱元璋冲口责道:“上下官府通同欺蒙朝廷,朕登基以来,闻所未闻,如今败露,罪有应得,岂能听信腐儒小人之言?”
李文忠只得奏道:“臣在先已有所察,以为此人说得大都是实情。”
朱元璋盯着李文忠,心卜卜直跳,尽管他是自己的亲外甥,如此忤旨 ,也难容忍。
李文忠看得明白,心里着急,不得不犯颜奏道:“臣虽是武臣,身边也有些晓事的人,臣早已听他们对空印一案议论颇多,以为此旨一降,杀戮必多,国家事大,不可不慎重行事。”
朱元璋忍气听着,心想,早就知道你爱与文人交往,府上养了许多门客,果然如此!想那些人聚在一起,必然专门议论朝廷是非,朕亲定的大案的还敢说三道四,何况其余!你成天与他们混在一起,久而久之,能不听信这些腐儒的教唆?当时强压着怒火,冷冷说道:“朕借空印一案,匡正胡陈乱党之恶,有些小人为此案鸣冤叫屈,是何居心?”
李文忠被吓了一跳。近年朝野上下对胡陈党案谈虎色变,圣上尽管是自己的舅父,当面说出这样的话来,能不哧人!李文忠心中委屈,奏道:“臣以为空印一案,难与胡陈乱党相连。”
朱元璋终于怒道:“大胆!身为重臣,朝廷至亲,竟为他为所惑,还不听指点,如此忤旨,若不念往日的功劳,定治以重罪!”
李文忠见圣上如此暴戾,心中凉透,只得陪罪。
朱元璋看出文忠并不心服,心想,他如今功成名就,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心,莫非要借此挣个开明的名声?
李文忠见圣上一脸疑云,难忍的冷淡,万般无奈,只得告退出宫。回到家里,想起圣上当年何等英明,近来竟越发偏执,由衷地惋惜。又想,也许正值盛怒,难以听进别人的言语,事后未必如此。忽又想,若奏明太子,求太子从容奏明圣上,或许还能听进去一些,当即打定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