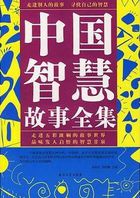我的上海朋友怕我做出愚蠢的决定,坚持要陪我去看琴,并义正词严地对不遗余力向我推荐高端琴的销售代表强调:“你不能再让他花一两万冤枉钱了,他在北京已经有两台雅马哈(钢琴)了。”
我挑琴程序非常简单,就是把琴行里的所有琴都摸一遍,或者说叫弹一遍。销售代表都眼力极好,几下就知道鄙人对声音手感极其在乎,盯着高档琴爱不释手又花不起四五万、七八万。
就这么着,2002年我的北京新房耗尽资金,连空调都要等着天气热了再买,结果竟让那抓住了我弱点的琴行卖给我一台两万三的合资珠江雅马哈。当我最终装上了空调,在夏日凉风中弹上一首小曲时我就想,要是贝多芬这么舒服,他也许就创造不出那些不朽的作品了。
我的另一台雅马哈是日本原装的。2004年我的经济略有好转时我去了一趟琴行,果然就被卖琴的套住了,开价四万八,我砍到四万,老板痛不欲生的表情让我多少有些安慰。这琴放在岳父岳母家,女儿在那里住,平时练琴。这琴一直在培养我不急不躁的性情。多少父母对着孩子喊: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买琴还请老师你还不珍惜,你这样做对吗你对得起父母吗你?我可得忍住,琴是你自己要买的,小孩子都是不爱练琴的,天经地义,有什么好急的。
上海朋友终于制止了我的不理智行为,最终我竟极富创意地租了一台琴,每月250元。尽管是旧琴,但却是日本原装的KAWAI。我对KAWAI低音区的磁性一直极为着迷,但新琴价格都在四五万以上,我现在竟能在我的江景房中享受磁性的、二百五的KAWAI,你说我有多幸福。
我对钢琴之业余令人发指。这两年看着女儿学,就跟着她去考级。考场外面总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是家长和孩子。我们钢琴组十分利落,等着叫号就是了,那些民乐的琵琶二胡什么的都自己带琴,在等候大厅里吱吱呀呀地练个不停。一个老师抄起那种导游用的喇叭喊:“同学们,同学们,我们这里已经够乱的了,请你们不要再练了,请你们不要再让手里的乐器发出任何声音,不要再发出任何声音。现在开始进考场,我从钢琴组开始叫……”
我跟着一群一二年级的学生进场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揪住,“哎哎哎这位家长,说了多少次了家长不能进去,赶快出去!”我得意地一亮准考证:“我是考生哩。”
考三级的时候工作忙,的确练得不是很熟,当我把音阶、练习曲、巴赫的《加沃特舞曲》、库劳的《C大调小奏鸣曲第一乐章》、《乒乓变奏曲》磕磕绊绊地弹完后,用无助的眼神回头望着考官。考官——一位50多岁的女教师,跳起来激动又好奇地问:“你,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这么大岁数还练琴?)我说:“我在外企工作,没时间练琴,下面进来的是我女儿。”我其实并没有靠“父女共同追求艺术携手考级”这种炒作获得考官的同情分,但是考级通过证书上评语中的“成人学琴,精神可嘉”字样,还是让我感到是人家照顾我才通过的。
我十岁开始学手风琴,在考大学、工作等种种表格的“有何专长”一项中,都写过“拉手风琴”。后来觉得这一表达过于肤浅和功利,特别是到外企工作后总写英文简历,就把“专长”一项填为“keyboard”(键盘)。后来发现这种描述真的很酷很能唬人。一项调查表明,在15—25岁年龄段的女性中,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人将她们梦想中的“私奔对象”定位在“乐队吉他贝司或键盘手”,没有人会愿意跟一个“会拉手风琴的傻小子”有什么事。可见“拉手风琴,会弹电子琴”只是一种匠艺,而keyboard则是一种情感的文化的符号。
我开始玩手风琴之外的keyboard是上大学以后。那时跟现在已成为超大腕的刘欢是同学。在学生会负责文艺的刘欢不仅自己什么乐器都能玩,还狂热地为学校购置各种先进乐器,比如那种80年代那会儿还很罕见并且超贵的大型电子琴。我们经常靠那一台雅马哈电子琴给整个在食堂举行的舞会伴奏,刘欢累了或不在或喝多了下不来楼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弹。有一次舞会场面特别大,人特别多,我会的曲子差不多卖弄光了却还有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学生会的人就在一边嘀咕:“这小子撑不下去了,赶快去找刘欢。什么,喝多了动不了了?给丫灌点醋,怎么着给抬下来。”
后来刘欢开始弃乐(器)转唱,我推着那台大琴四处为他伴奏,直到1985年那次我们参加在北大举行的外语歌曲演唱大赛。在台上他捣鼓一架大钢琴我操一台大电子琴,我们整个玩转了北大。从此刘欢被电视台盯上走入音乐圣堂,我回到现实世界用我的keyboard继续神游。
我的键盘风格异类,就是不照谱子只凭旋律自己配和声弹。有时你看我在那里如痴如醉,其实都是自己在胡乱演绎名曲,大师听了痛心死但现实的听众往往都会喜欢。
尽管我一直强调钢琴的自娱功能,但也特别崇拜那些在音乐表达或肢体表达上比较夸张的大师们。小的时候羡慕殷承宗将小分头一甩的感觉,还有刘诗昆淋漓地砸的味道,今天的郎朗更是将表达弄到极致。但是音乐更在于内涵。不仅这些钢琴大师擅长内涵的表达,身边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比如上大学的时候,刘欢跟一女生闹了别扭,怎么解释都不行,于是把女生拉到礼堂,夜半时分用钢琴猛砸了一段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协奏曲,女生就哭了。这就是内涵。
我也特别崇尚这种感觉,但上钩的人非常有限。我的第一台钢琴,就是我说的两台雅马哈和一台KAWAI之外的那台,是1990年苏联的“旋律”牌,那时正是卢布贬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用美元买下来并从莫斯科运回才合200多美元。但正是那台琴营造了我的钢琴梦想,或者说乱买钢琴的臭毛病。记得在我家小型演奏时,一个长着赵薇式的大眼睛的女孩有点恍惚地说这声音太美妙了。后来在美国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又见到大眼睛,我们在胡扯别的什么的时候她又提起,“你家的钢琴还在吗?什么时候再听你弹?”我的心怦然一动,想到了拉赫玛尼诺夫、刘欢还有内涵。
几天前,我又翻出波兰斯基的电影碟片《钢琴师》。主人公在饥寒交迫中为德国军官的那段演奏荡气回肠,在片尾他又回到波兰电台,演奏中他的小提琴家朋友在录音室外向他挥手。他微微地一笑,琴声在继续,随后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钢琴就是这样将人生最简单或最复杂的情感从指尖娓娓道来,让你在现实和理想的空间自由地诉说和宣泄。
玩了这么多年的keyboard,除了考级绝对被看出破绽,一般场合都能对付,也听惯了周围大眼睛们的感叹和揶揄,总的是比较飘然。上星期几个同事闲聊,他们说我们部门的实习生,上海某高校的高材生,是学校乐队的鼓手,而且她什么打击乐都会玩,凡是能响的东西在她手里都变成了好听的玩意儿。
我接过去说,凡是黑白相间的东西,在我手里都能变成美妙的音乐。
几个人听了咯咯地笑。
我一想,坏了掉进去了。这帮人肯定在想,在一个我恍惚的时候牵一头斑马过来,然后看着我对那可怜的动物疯狂地发泄。
如果姐夫是一个品牌,那么这个品牌的logo一定是:一头斑马拉一辆破车,车上载着四架钢琴。
我就永远生活在这黑白相间的世界里。
中国“五更泻”与印度“德里肚子”
医治迷失的灵魂和拉稀的肚子
凌晨两点,我提着一瓶东航飞机上发的崂山矿泉水,第一次踏上了印度——这个神秘的唯一让我产生“文化的激动”的国家。
去印度前,我得了烦人的腹泻,就是拉稀。吃了各种药都没有效果,一位老中医说:“你这是典型的‘五更泻",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奔厕所,没错吧。”
用了老中医的祖传秘方,不见好转,又开了一副某河北名医上世纪20年代用过的神方,还是不管用。“养肝、补肾我都给你用过了,不行下次我再加几剂健脾的药。”老中医为对这种看似普通的病束手无策而深感郁闷。
周围的人又开始将印度的事无限夸大,什么水不能喝,去了就拉稀,街上找不到厕所,找到了厕所又没有纸,等等。
借我们500强公司开会的光,住在350美元一晚的印度首都德里的帝国酒店,我惬意地享受着英式早餐。一位来自东南亚的同事过来问:“你刷牙用的是瓶装水还是自来水?”
刚刚平静的心又被揪紧,想起临行前朋友们说在印度洗澡时不要张开嘴。天哪,印度的水好像都是下了毒的。
我决定不再顾及这些夸张但也许并非虚无的建议,我需要感受真实的印度,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已拉稀我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