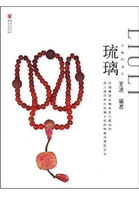苏婉灵做了一个梦,梦里是孙朝阳出征的前一天,她向她爹闹着要和大军一同出征,被她爹训斥胡闹。
孙朝阳就站在一旁坏坏地笑,然后在她一脸怒容的瞪视下,笑着走了过来,揉乱她的发髻,不怀好意地道:
“阿灵你笨手笨脚的,带你去战场岂不要拖我后腿?”
她顿时大怒,正想发作,男子的笑容便蓦然变得温柔似水:
“好了别闹,我请你喝酒。”
而后便是孙朝阳提着孙将军珍藏二十年的女儿红找她,两人坐在大院外的杏花树下划拳喝酒,笑闹行酒令,好不畅快。
她记得那天的月亮好大好圆。两人喝到酣处,孙朝阳便定定地看着她,黑黝黝的眼眸似含了三分醉意,七分羞涩。他说:
“阿灵,等来日战胜归来,我就披着战甲娶你过门,你说好不好?”
“切!谁稀罕呢!”她不屑地白他一眼,小小的一张脸,却若天边晚霞,烧过了一切,最终尸骨无存。
孙朝阳,你说过,你要披着战甲,娶我过门。你怎么可以食言?!
苏婉灵醒来时,发现自家亲哥坐在她的床榻边。见她醒了,似松了口气:
“小妹,你哪里不舒服?”
她摆摆手示意并无大碍,见房里只有她哥,便问道:
“爹呢?”
“爹入宫议事未回。”
“那朝阳……”
“小妹你冷静听我说。”苏寒山似怕她承受不了,语气也温和了许多,带着几分小心翼翼试探的味道,却只让苏婉灵越发烦闷。
怔怔地点了点头,便听见苏寒山有些迟疑地道:
“我军这次大败秦国,但孙将军因过于轻敌,中了敌军埋伏。已经以身殉国。而朝阳……”
“朝阳他怎么呢?”苏婉灵觉得自己的耐心已到了极致,见她哥说话吞吞吐吐,忍不住便吼出声来。
苏寒山看着自家小妹这副模样,心中不忍,却也明白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她一世,索性把他知道的全部和盘托出:
“朝阳那时正和孙将军在一起。战败后,秦军下令屠杀我代国士兵。朝阳他,下落不明!”
一狠心全部说了出来,却见自家小妹脸色恍惚。他一怔,忍不住便轻声唤她:
“小妹,你没事吧?”
苏婉灵却是不言不动,一双杏眼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良久,才面无表情地道:
“那朝阳他是,死了吗?”
面对她如此的轻描淡写,苏寒山只觉得自己也变得心惊胆战起来。想到孙朝阳和自家小妹这些年的情谊,也不由升起几分唏嘘。
伸手将她揽入怀中,他抱着自己这个从小就最疼宠的妹妹轻声安慰着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语:
“只是下落不明,说不定没事的。”
“……”
“朝阳那小子从小就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你别太担心。”
“……”
“小妹,你还好吧?”
“哥,我难受……”苏婉灵淡淡地说着话,声音却嘶哑得厉害。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似的,她只能像小时候受了委屈一般把头埋进她哥的怀里。
却还是没有丝毫好转,没有丝毫缓解。心里很痛,痛到极致,便只有一个黑糊糊的洞,不断地灌着冷风。苏婉灵甚至觉得,自己几乎痛得快要死掉。而耳边回荡的只有她哥温暖如风的声音:
“小妹,没事的,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可是哥,你知不知道。
孙朝阳他明明答应过我,战胜归来,必娶我过门。
他明明说过,要娶我过门。
他怎么可以,他怎么能够,食言而肥。
孙朝阳,你怎么可以负我如此?!
苏婉灵在她哥怀里哭了一阵后,渐渐倦了,便睡了过去。
苏寒山直到看见她安然入睡后,才放下心来。出了房门,他的贴身小厮便来禀报说苏大人已经回府,现请他去书房一趟。
他不敢耽误,匆匆去了书房,却见他爹正襟危坐在紫檀木制的书桌前,手持朱笔,却迟迟没有下笔。
“爹——”他轻声叫了一句,苏子亭才回过神来,放下手中朱笔,淡淡地问他:
“婉灵怎么样了?”
“现已经睡下了。只是哭了好一阵,想必是真的很伤心。”
“她对朝阳,倒真是情深义重。”苏子亭说到这里,似有些不忍,蹙眉叹息一声。苏寒山也有些唏嘘,犹豫了片刻,还是不死心地问道:
“朝阳他,是真的死了吗?”
“只怕是凶多吉少。”苏子亭说完这句,便止住这个话头,开口说起旁的事,“今日被婉灵这样一搅和,三王子看来已经是夺嫡无望。”
“爹……”
“陛下本来就属意大王子,只是老夫心有不甘,想勉力一试,无奈天命不可违。现而今,也只能尽力辅佐大王子,只盼他日后也能成我代国的一代明君。”
“爹为代国鞠躬尽瘁,是小妹她还年幼,不懂爹的苦心。”
“罢了罢了,这也是命。天命不可违啊。”苏子亭说到这里,似有些感慨地低声叹了口气,沉默半晌才道,“总之我们为人臣子的,只有尽力辅佐君王。天命虽难改,但只要尽心尽力了,也对得起我们为人臣的本分。”
“是,爹,孩儿受教了。”苏寒山垂眉应了一句,却听他爹又道:
“你这些日子看着些你妹妹。她今日此举,已经引起了陛下的注意。刚才在宫里还问我她的生辰八字、可许人家。”
苏寒山一愣,顿时有几分心惊地道:
“陛下是想……”
“我也只是猜测。”苏子亭淡淡地打断他下面的话语,长眉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蹙成一团,“总之小心一点没有错。”
“是,爹。”苏寒山垂眉应了一句。想到自家幼妹如今的处境,不由也有些头疼。
且不论陛下他现在究竟是什么心思,而今婉灵她能不能从孙朝阳那件事里走出来还成问题。
情深不寿,慧极必伤。
他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妹妹,他比谁都明白。
婉灵有多喜欢孙朝阳,她现在就有多疼。
可是可惜,多可惜。
她和孙朝阳,明明该是最幸福美好的一对。
偏偏情深缘浅,终不能得成眷属。
然而令苏寒山没有想到的是,他和他爹的猜测,竟很快就成为现实。
当宫里来的宣旨公公站在他家前厅时,他就明白大事不好。苏家一门众人由苏子亭率领着跪在前厅接旨。
苏婉灵虽身子不大爽利,也还是挣扎着起身,一同跪下接旨。而后便听那公公宣道:
“苏家长女婉灵,温柔贤淑,得宜服众。大王子拓跋寔早慕佳名,多有神往。朕怜其忠恳,特赐此大好姻缘。望两人共结连理,百年好合。钦此。”
话音落下,苏婉嫣就仿佛被雷劈了,俏脸上顿时就露出几分恼怒的模样,下意识地望向苏婉灵,却见她亦面色难看。而那宣旨公公只是笑眯眯地看着跪在苏寒山身边的苏婉灵道:
“苏小姐,还不接旨?”
苏婉灵却仿佛被闷棍打蒙似的不敢相信。若不是苏家长女就是她,若不是公公红齿白口叫的都是她和阿寔的名字,她几乎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梦,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
可公公的声音还在继续,他说:
“苏小姐,你怎么还不接旨?”
接什么旨?接她和阿寔百年好合、共结连理的旨吗?可是她想百年好合、共结连理的从来就不是这个人!
从来就不是!
苏婉灵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一场无止无尽的噩梦中,冷不防却被身旁的哥哥推了一下。
苏寒山淡淡地看着她,眼神虽悲伤,语气却不容拒绝:
“小妹,快去接旨。”
她依旧只是呆呆地没有反应。公公的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好在苏子亭毕竟在宦海沉浮多年,立时就笑着道:
“我这女儿没见过世面,约摸是被乐傻了,公公不要见怪。”说罢,便从怀里拿出一块上好的羊脂白玉递了过去。
那公公也是有眼色的,见有台阶可下,自然乐得下来。安安心心地接过羊脂白玉,也陪着一同笑道:
“苏大人客气了。以后您就是皇亲国戚,前途不可限量啊。”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苏婉灵却似突然反应了过来,竟是冷冷接口:
“谁稀罕当什么皇亲国戚!谁稀罕谁去嫁!”
“婉灵!”
“放肆!”
苏寒山和苏子亭的声音同时响起,苏婉灵却丝毫不惧。那公公似乎终于看出了什么门道,一双小眼睛微微眯成一条缝,颇有些精光四射。
然而看见苏家两父子有些尴尬的神情时,他转瞬便又笑了,不再看苏婉灵,他只对苏子亭道:
“令爱果然是乐疯了头。咱家还有事在身,就先回宫复命去了。”
“那公公慢走。”强笑着送走这尊大神,苏子亭回过身来,脸色就顿时黑如锅底,“苏婉灵,你是想让整个苏家给你陪葬吗?”
苏婉灵只是抿着唇,倔强不语。偏一张脸,苍白得过分,显出几分萧索的薄弱意味,却再惹不起一向疼宠她的爹爹半分怜惜:
“苏婉灵,这是陛下金口玉言下的圣旨。你就算再不甘愿,也得给我嫁!你若想抗旨,便是拉上整个苏家给你陪葬!你知不知道?”
“那爹您现在是想卖女求荣吗?看见阿寔得势,便知道自己投靠错了主子,押错了宝。现在就急巴巴地把女儿嫁过去,好再次笼络住他吗?”
她话音一落,一个耳光就随声重重响起,打在她的脸颊上,力气大得几乎要把她打晕过去。
苏子亭这次真的怒到极致,连嘴唇都不由得哆嗦着,声音却仿佛带着冷冷的笑意:
“老夫卖女求荣?若不是你那日在前厅胡搅蛮缠如此锋芒毕露,陛下又怎么会注意得到你?若不是你执意要帮大王子,破坏老夫的局,陛下又怎会想把你和大王子凑在一起?婉灵,你自作孽不可活,你究竟明不明白?”
“我不明白!”苏婉灵却终究是放声哭了起来,在她爹面前,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爹,我不想嫁!你帮帮我,我不要嫁给旁的人,你帮帮我啊……”可即便她哭得再惨,所能得到的也不过是她爹的一声叹息。
苏子亭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自小就最骄纵的女儿,竟也忍不住老泪纵横。可答应不得,如何答应?所以最终也只能淡淡道:
“这次,由不得老夫,也由不得你。”
可是恍惚中,是谁尚且年少,殷殷笑语。
只说我此生非卿不娶。
非卿不娶!
苏婉灵自那日领旨后便生了一场大病,气势汹汹,病如山倒,就连当今圣上也被惊动了,特御赐了医术精湛的御医给她来看看,又赏赐了不少补品药材,当真很是疼惜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
贺兰氏见苏婉灵能得如此荣宠,更是不忿,苏婉嫣这些日子身体亦有倦怠,但苏家所有人一股脑心思都在那个即将成为代王儿媳的苏婉灵身上,根本没有人在乎自己的亲女婉嫣。
明明婉嫣也是堂堂苏家的大小姐,怎的老爷就这么偏心?
贺兰氏越想越恼怒,更是恨极了苏婉灵,巴不得她就这样一病不起,死了正好。
却说苏婉灵自病后便一直淡漠,即使面对如此皇恩浩荡,也并不见得有何喜悦。宠辱不惊,淡漠如水,却更是得了当今陛下的赞誉。
她对这些都丝毫未觉,有的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就这样死去也未尝不失为件好事。
至少这样,就守住了当年非君不嫁的誓言。
至少这样,就守住了你。
朝阳,孙朝阳。
她只要一想到这个名字就痛得直不起腰来,可是每日还是要想好多好多遍。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勇气将那些方才灌入喉中的药再次催吐出来。
只有这样,才会觉得,即便是死,亦不是太可怕的事情。
苏婉灵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实是急得苏府上下乱成一团,上到苏老爷大公子,下到伺候的下人,个个看着苏婉灵日渐消瘦,心急如焚,却也皆是无计可施。
虽然大公子苦口婆心劝过这个小妹,苏大人严词厉色训斥过这个不省心的长女,就连下人们也都一一哄劝过自家的宝贝小姐。
但苏婉灵的病情依旧是未见好转,反而日渐消瘦,瘦得几乎都只剩一把骨头。
苏家人都无计可施,苏大人的眉越蹙越深,大公子脸上已没了笑容。苏家一片愁云惨雾,好不压抑。
这时却仿佛有人嫌他们不够麻烦,还来添乱。
当苏寒山听见拓跋寔来访时便是这样的感觉,苏子亭入宫议事未回,他也不能把堂堂大王子拒之门外,只能勉强硬着头皮将人迎了进来。
坐在前厅里东拉西扯了好一通后,终究是拓跋寔先忍不住道:
“大公子,阿寔此次来访,是听说婉灵病重,想过来看看她。”
“难为大王子有心,只是舍妹她方才睡下,此时只怕无法招待大王子。”
“不妨事,我只看她一眼便可。她若睡下,我便不吵她就是。”
他语气虽浅淡,话语间流转的却是不容拒绝的气势。苏寒山心中为难,却也明白必是挡不住他的,只能苦笑着点头将他带到苏婉灵闺房。
雕花的朱门紧锁,苏寒山象征性地叩了叩门扉。见里面的人无心来应门,便只能自行推开。
苏婉灵却并未睡下,只是坐在木兰雕花的窗前,怔怔地看着窗外的景色。听见有人进来,也不回头,只淡淡道:
“哥,不是说了我没事嘛。”
苏寒山正欲答言,却被身旁拓跋寔淡淡制止。俊美无双的男子轻轻挥手示意他先退下,他愣了愣,终究还是转身轻轻离开。
拓跋寔怔怔地看着坐在窗前一手支颔倚栏而望的女子,竟有些心疼。婉灵是真的瘦了,憔悴了。
可她还是苏婉灵,他想了这么久,终于就要嫁给他的苏婉灵。
这般一想,蹙紧的眉才微微松开了些,解开身上披着的白狐皮袄,一股萧瑟的寒意便随着寒风掺杂而来。
此时时令已过了晚秋,北国的秋日总是掺杂着寒风冷到人骨头里面去。而婉灵只披一件单衣坐在窗前,一定也很冷。
他怔怔想着,手中的白狐皮袄已经轻柔地披上女子单薄的肩头。他说话,连声音都不自觉地带了几分宠溺的疼惜:
“不说病了吗?怎还是这般胡闹,单披着衣就坐在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