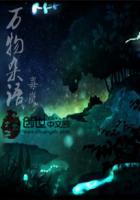1968年冬天,临近春节,一辆大卡车开到礼县城鹿家街巷口,几个年轻人破门而人,装载了我们家的所有东西,父母被赶上车,车子开到距离县城两公里的燕子河边,这些人把车上的东西扔到白雪堆里,车子“轰”一声掉头开走。
听母亲说,那天的雪很大,路都被雪盖住了,他们蹲在燕子河边,等啊等,等到两眼昏花,看见大表哥牵着两头骡马,从漫天雪花后面蹒跚走来,大表哥全身冰雪,见面没说上两句话,家当由骡子驮一些,父亲背一些,母亲骑上马,怀抱两个孩子,踏着积雪向八十华里外的固城乡走去。当时,父母都不知道,脚底的雪层下面,是一条拐了七十二道弯的河流,每走一步都是陷阱。1968年的固城河,是一条横空出世的癖龙,在永坪峡独断专行。走在河流表层的一家人,无论怎样都想象不到下面是一条凶险的河流,一家人糊里糊涂走了两天一夜,第二天黄昏时分走到固城。我们家的狗——阿黄首当其冲跑进固城街,灰黄天边悬挂铅色云朵。分给我们的三间泥瓦房深埋着头,向落山的夕阳,无声的迎接疲惫不堪的一家人。
按下放政策,我们住进大队分好的三间瓦房里,瓦房朝街且在街道中央,院落有间茅草屋,窄小的菜园边隆起一畦野草梗,另一边是李家爷的两间房。左边住李家爷的本家“丫丫”(固城话:阿姨丫丫”家往左住“丫丫”的小叔子一家、刘二胖家,陈维雄家到水井边的田根生家,水井以上是上街村,房屋修至街口的粮站,再往前为西山一带的一个个村落,延伸至遥远的分水岭。
李家爷孤单一人,夜晚常听见他发出的叹息。整夜,李家爷醒来一次叹息一声,天快亮时,他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惹得我家的大公鸡还没醒就打鸣。天不亮,父母随村民下地,措手不及的熟悉农事。两年后,母亲生下小妹,邻居家的“丫丫”,生下期盼已久的儿子。听着墙里墙外两个婴儿的啼哭,我们走进了上世纪70年代。
日子过得极慢,大人们都把过日子说成推日子,一天一天往前推。村庄所有的人家,与我们一样贫穷,不同的是他们早巳习惯艰辛的耕作,父母还没有习惯,母亲很快进人耕作状态,父亲却总在发牢骚(下放前,父亲是一位中学的英语老师),动辄拿起包要回县城去,每次父亲出走,母亲追到下磨河坝将父亲拽回来。时间久了,父亲掉头要走,母亲不再去追,父亲跨过固城河,母亲泪花闪闪地说这回真走了?在母亲的念叨声里,父亲又悄悄返回来。父亲通常四五天时间,就要大闹着走一次,每一次都没有走出固城河。年终,给固城拉回销粮的大卡车,开到我家门前时,父亲急切地请司机下车吃饭,陌生的司机吃母亲特意做的臊子面时,父亲像看到了久别的孩子,眼神里满是亲切友好。当大卡车卸下一袋袋粮食,碾着积雪开出村庄,父亲常常满脸迷茫,黯然神伤。20多年后,国家有政策可以回去,母亲曾多次劝父亲回县城老家,不知为什么,父亲却不走了。父亲80岁那一年与母亲才回到城里的老房子里。几乎每天早晨九点钟到长途汽车站,等候从固城开往县城的班车,只要看到车上走下来固城村的人,父亲赶忙上前迎接,请人家到家里去歇息吃饭。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春天。我摸索着向篱墙走去,旧年的黄花叶干枯腐烂,酸刺枝头几只麻雀跳来跳去。石头墙壁另一边李家爷的院落,荒草丛生,积雪成堆,李家爷低头坐在众多豁口的门槛上,等待阳光温暖他。春天的阳光,落在他头发稀疏的脑门,雪花在他松大的棉布鞋旁一点点融化,然后长出青草,草一发芽鸟就飞来了,飞到他的大棉鞋上,再跳下去琢吃鞋边的草尖。我过去是为了能捉住一只麻雀,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摇摇晃晃地跑过去,麻雀便飞到大柳树上去了。我看大柳树上的麻雀,看得久了,大柳树冠出现一层白色烟雾,雾一天天散漫、上升,看起来要与云朵接上了,可还是掉回地面,掉下来的那片雾生出一片又一片的绿。
一年年,固城河冰雪消融,河流一天比一天清澈,树叶一天天葱绿。我家的后院墙壁生出蒲公英;茅草屋顶,经常在早晨或傍晚冒出绿荫,绽放几枝艳丽花朵,麻雀们从中觅食,野鸽子飞来又去。夏天,金色麦浪随山野高低起伏,麦香飘溢,洋芋花白。晚霞将尽的傍晚,山坡上走向村庄的人和牛羊,身后跟随串串红色光芒,光芒越来越红,越来越远,看着看着,所有的地方忽然暗了,天地连在一起。秋天,树叶金黄,河流闪耀金光。田野赤黄相间,山峦色彩斑斓,鹰飞长空,谷物成熟,大地醇香。冬天,大雪封山,河流结冰,千树雪花盛开,飞鸟归巢,动物蛰伏,天地宁静。
这一切好像都是为我们一家人的到来准备的。
小妹能走路了,到野地里拔猪草时,我将她背在背篓里,回家时哄她跟着小伙伴们跑,不知不觉,妹妹们长大了。
李家爷高兴的时候,坐在石墙上给我们讲故事:“以前有个阴阳先生,想给自己村里修一座山神庙。于是,他拿上鞭炮香烛到固城村的山神庙里去请示,摇完签,签上的山神爷说:我刮东风,你的小船能向南吗?阴阳先生跪对神龛后的山神爷说,我修一座山神庙,自己管自己。签上的山神爷又说:你修十座庙,山神爷还姓柳。固城河边大大小小的庙,哪怕是一片瓦搭起的庙都是柳家的山神庙。阴阳先生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修了座庙,可庙刚修起来就倒塌,他再修,修起来又倒塌,修了三座庙都不声不响地倒了。阴阳先生彻底灰心了,他逢人就说,这都是老秦先人在后梁放马吃光了他们的草,前川里饮马喝干了他们的河,三千年前就占尽他们的风水,怪不得他没本事。李家爷说阴阳先生修庙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要炒一碗豌豆到山神庙去给山神爷鼓劲,生怕一座庙里坐两尊神,将祖祖辈辈积起来的美德善行一分为二,再随风吹到固城河下游去。可毕竟阴阳先生不是神,他活到70岁过世后,倒头纸刚烧毕,就被山神爷的门卒挡在门外。他几次回生几番拼打,给山神爷上三道高香才拿到通行证闭上了眼。”
后来,山神庙在破“四旧”时拆掉,山神爷日夜蹲在后头崖上的瓦片下面,没有庙坐的山神爷,依然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母亲起早贪黑劳作,经常在夜晚抑或凌晨到山神庙去请求山神爷接纳我们一家人。父亲每当看见母亲手里的蜡烛,一把夺过去扔到门外骂山神爷,李家爷听见了,气得脸颊通红,指责父亲活该下放农村。父亲骂李家爷老地主,李家爷骂父亲小土地出租。母亲赶紧关闭门,生怕被人听见,可还是被一墙之隔的“丫丫”听见,她亮起嗓门,大骂“外来户”欺负他们李家人。李家爷就故意骂大柳树,村里人都说大柳树底下有沙毛神,夜里出来想抓谁伸长胳膊就抓走了,可李家爷一点不害怕大柳树,愤怒的时候抓起石头甩向大柳树。有一次,他和母亲吵架,跑出去提了根棍要打大柳树,母亲喊:“胆子大了打啊!”李家爷后退两步打自己的脸,扔掉木棍撞得土墙咚咚响。
和平共处的日子里,李家爷从我家后院扫一背篓干树叶,烧热大火炕,从坑柜里取出一掬豌豆,隔墙喊:“我的娃,暖热炕来,吃豌豆来!”我们兴高采烈地跑过去,从他粗大的手掌中抢一把豌豆,边吃边踩得他家的木头地板嗵嗵响:“踢毽子,过格年了穿缎子,织木子,过格年了吃麸子。”
李家爷背靠炕墙,抹着厚嘴唇下边的灰白胡须,笑眯眯地看我们玩。
夜晚,河流的另一边愈发神秘,猫头鹰蹲在吊沟梁上,敛收内气叫夜魂的声音秋千一样荡到天亮。
进入腊月,林子里打柴的男人陆续背柴回家,外出的木匠、泥匠,打零工的人们日夜兼程回到家乡,平日里借出去的一只竹筐或是一只背篓,借方都会记得还给物主。而回娘家帮助母亲腌菜磨面的女儿们,却要在歌谣声里背起儿女回到远或近处的公公家去。腊月里很少晒太阳,雪花飘洒的时间占去白天夜晚的多半时间,夜深人静时,听得到雪落地面的瑟瑟声,和栖居在大柳树上的鸟儿发出的冻僵了的叹息声。凌晨时分,常常听见低沉的模模糊糊绕屋顶盘旋的呼唤声,那声音像一层气压,重重包围住即将发白的夜空,尔后越来越多的呼唤声像要密封夜空一样涌向屋檐,待大公鸡一声高昂的鸣叫,那层模糊声仿佛被打破一个口,朝黎明的光亮塌陷下去,掉进来的地方去了,模糊声回去之后,天便亮了。李家爷说那是逝去的魂灵夜里探完亲后,搭乘白昼的第一缕光亮返回时发出的依恋声。
依恋声夜夜响起,朝朝离去。
初来乍到的父母,对农事、乡俗的生疏,常常招来乡亲们的讽刺,甚至辱骂。收麦、晒麦的日子里,村民聚集一起,往往有人叫:“外来户。”母亲装作没听见,父亲却要争个高下,父亲的学识在漫骂声中自然无用。母亲苦苦劝父亲做好自己的活,千万别跟人家争,可父亲控制不了自己。二哥只要听到有人叫“外来户”“反革命”,随地拿起石头,圆睁眼睛上前拼命。
“外来户”成为我们一家人的名字。跟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嘴里不时蹦出那个词。学校的老师、同学动不动叫我“外来户”。夏天晚饭后,劳累一天的乡亲们坐在戏楼前,男人抽着两分钱一片的水烟,说一些天高地远的事,女人做针线纳鞋底,欢声笑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间,说着闹着就会扯到“反革命”“外来户”的话题上,父母听见做贼似的悄悄离开。有一次,有人要将母亲栽的树要锯掉,二哥拿起斧头,顶住他的脖子吼:“锯,你锯树,我锯你!”锯树的人吓得抱头痛哭,求二哥手下留情,母亲上前阻拦,二哥抡起斧头砍向脚下的石头,吼道:“谁来我砍谁!”母亲当场晕倒,二哥才作罢。
二哥像一位英雄,震慑住了经常骂父母的人。成年以后的二哥,有过出去工作的机会,因家中缺劳力,上班半年毅然回家种地。改革开放后,二哥秉承父母的“若要富,开水铺”的传统理念,继承父亲的食醋作坊,开起醋坊,供应固城十里八乡,二哥因勤劳憨厚赢得村民敬重,赵氏食醋因此名扬固城河畔,二哥成为村里备受敬重的人。
1982年9月,我去县城读高中,报名时,没有城镇户口,年轻的女老师和蔼地问我:“是黑户吗?”我看着她无言以对。当晚,问大姐什么是黑户?她说:“就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年底放假回到村庄,问父亲什么是黑户?父亲说:“既没有城镇户口,又没有农村户口的人。”我站在牡丹树前,仿佛才明白,我们一家人,在村庄是“外来户”,在城里是“黑户”。
我一直向往回到老家,可没有想到,我们早就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