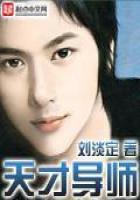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
父亲仍然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被带走,1976年的风中刮着阴冷与潮湿,在“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的大时代背景里,父亲首当其冲成为村庄反面人物的代表。
春耕时,父亲与遂心到苟家沟去耕地,晚上遂心向公社汇报父亲说反动话。当天晚上,大队开始声讨父亲的罪行,4月下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村庄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父亲的批斗会越来越多,白天到其他村庄去轮流批斗,晚上在村子里批斗。母亲屡次吐血,夜夜咳嗽到天亮。在全校师生面前,大田老师数次告诫学生,如不好好学习,就像赵某某一样拉出来批斗。我站在全校学生面前,作为集合学生的代表,差点昏倒在地。放学后我背着大妹回到家,家门紧闭,屋内昏暗,饥饿充斥了缺少温暖的家。土墙挂的小黑板上有父亲的留言:“我们去苟家阳坡收菜子去了,你们放学回来去水泉湾拔猪草,不能走得太远!”
学校的集合时间,大田老师仍然不断提起父亲的名字,然而这远远不够,一天下午的语文课上,他用“反动”一词造句,在句子的前面加上我的名字。同学们笑了,老师也跟着笑了。我站起来,径直走出教室,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回到家。土墙上的小黑板上写着父亲的留言:“放学后做饭,今天不拔草!”做好饭后,坐在火炉前睡着了,醒来已是次日早晨,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还是背起沉重的书包去上学。晚饭后,从前门传来咚咚的脚步声,父亲被两个民兵推搡着带走了。我听见站在蓠墙边的母亲,身体的颤抖惊醒了园中的花草。我站起来,拉开门跑出去,被站在屋檐下无声的母亲拦住。黑暗的前门外,孩子们唱着歌谣割啊割,割韭菜,割了三担五口袋,你的啦,我的牛娃吃上了,我的啦,我的塞进老鼠窟窿里了……”
我站着,听他们的歌声,母亲身体颤抖,抬起一只胳膊将我拦在篱墙边。我返身回屋,收起作业本,坐在炕沿边,两个妹妹在孩子堆里唱歌,二哥也在其中。母亲悄悄走向后院,打开院门出去了。我轻轻打开门,慌慌张张跑到高阿爸家,见大门紧闭,昏黄的灯光匍匐于门槛底下。我将两手扶在门前的石头台阶,把耳朵贴上去,听见里面乱嚷嚷的。突然,门开了,一个黑影走出来,我没顾上把手从台阶上挪开,只把身体躲在台阶下面。那人径直朝我走来,一只脚重重地踩在我的左手上——等到那人离开,我抽回手,一声不吭地回到家。母亲还没有回来,二哥和小妹还在唱歌。
我想不明白,当春天的柳枝抽打父亲的身体时,他为什么不反抗?
打开月光照亮的后院柴门去找母亲,在大柳树庞大的树身下走一圈,没有母亲的身影。妹妹们的歌声越过瓦房,在黑夜的空气中流传。
父亲是什么时候伤痕累累回家的?我不知道。第二天早晨,父亲背一背篓野草,喊我给他开门。我跑到后院给父亲开门时,他说我的手背有血痂,让我别用手剥,自己会好的。
“父亲的反革命帽子要戴在全家人头上。”这话是母亲说的,她嘱咐我们,要大家来戴这顶帽子,父亲是“反革命”,我们全家人都是“反革命”,这话也是母亲说的。我们全家人就是一棵“反革命”的大树,要长一起长,要死一起死。母亲说这话时,仿佛父亲是位革命英雄。
“反革命”又成为我们一家人的代名词。
篱墙后的菜园里,种一小块韭菜。每天晚上,母亲割一把放在炕头,父亲回来,母亲用韭菜汁给他的伤口消炎,目睹那过程的是墙台上的煤油灯和我们无声的梦境。
小黑板上经常写着父亲的留言,不是让我做饭,就是去坡里拔猪草,或者扫大柳树下的树叶烧炕等等。我留给父亲的有时是答复,有时不理。不管写什么,父亲都不生气,母亲不识字,从来不看小黑板。有一天,父亲写了一小黑板文字,好几天,小黑板没有擦,它是一首老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父亲睡觉时教我们唱歌,歌声盘旋在土炕四周,我经常在歌声里睡去。那种怀念的气息飘浮在破瓦房里,尤其悲凉哀怨。父亲在小黑板上教会我们《游击队之歌》《解放区的天》《白毛女》《天仙配》等等,教我们背唐诗王维的《送别》,李白的《静夜思》。
但我一直坚信,跟着父亲什么也学不会,除了忍耐和放弃尊严。
父亲的批斗会仍在继续。
固城河道不断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辆辆吉普车停在梯田边的红旗下,很快又消失在河流尽头。
腊月,父亲用县城爷爷捎回来的钱,买来红纸与墨汁,给村庄里的门扇写春联。父亲毫不吝啬地提起写好的春联递给打过他的人,除夕,家家的旧门扇上贴着父亲写的鲜红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