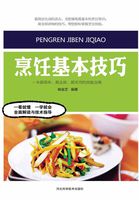5
飞机终于降落在省城机场。安然抓住华生的手腕,穿过拥挤的人流,很快冲出机场大厅,拦了一辆出租车。白兰跟在后面,气喘吁吁的,连声叫唤:“安然姐,等等我。”
到了医院,安然拖着华生一路小跑,华生的手腕被勒得很痛,边跑边哭。安然的心速“怦怦怦”地非常快,她脑子里一片空白,此时此刻,她只是想知道一个结果:白桦怎样了!
安然拦住一个护士,劈头盖脸地问:“白桦在哪个病房?”
护士吓了一跳,飞快地翻记录。“206”,话音未落,安然一阵风似地走远了。
安然推开病房,一屋子的人都惊异地看着她。白桦的母亲金枝,白桦的姐姐白玉,还有白桦的一些朋友同事。金枝惭愧地垂下头,用衣角拭去滚烫的泪水。白玉张大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安然一步步走近,躺在病床上的白桦已形容枯槁,与记忆中他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她都有些怀疑,是不是搞错了。但见到金枝与白玉,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白桦怎么变成这样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安然眼里掉下来。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将躲在身后的华生推到白桦病床前:“华生,叫爸爸。”
华生很害怕,扭过头抱住妈妈,不敢看白桦。金枝蹒跚着走过来,疑惑地看着华生。安然抚摸华生的头,内心酸楚,但还是对华生柔声道:“华生,这是奶奶。”
金枝听罢,老泪纵横,下颔抖动不止。几年不见,她已满头白发,容颜苍老。“这,这——是我的孙子?”金枝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是的,他叫华生,6岁了。”
金枝伸出颤抖的手,抚摸华生的头,“真是造孽啊!这都是我的错啊!”金枝将华生纳入怀里,华生赶忙挣脱,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金枝捶胸顿足,号掏起来,众人吓了一跳,急忙劝慰,病房里乱作一团。
也许是病房里太吵,白桦缓缓睁开了眼睛。“白桦——”,安然首先叫唤。那张曾经熟悉不过,而后日夜思念的脸,如今已形容枯槁,难以辨认。
安然坐在床边,白桦扭过头,一眼便能看见她。白桦眼里先是闪现一抹炫目的光,继而两行清泪从眼角滑下,无限温柔地看着安然,久久无言。
“华生,快要爸爸啊!”安然想起了这件重要的事,将华生推至白桦面前。
“爸爸。”华生虽有些胆怯,但还是很听话地叫了一声。他认真地看着白桦,眼中充满了好奇。
这是父子俩的第一次见面,没想到即将成为永别。白桦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似乎想起身坐起来,一旁的医生护士连忙阻止。
“这是华生,我们的孩子,6岁了,我爸妈把他带大。”安然拉着华生的手,放在了白桦的手里。
白桦的手指动弹了几下。华生感觉到了,吓得把手抽回来。白桦目不转睛的看着华生,嘴唇翕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却无法表达。
白桦已是命悬一线,目光渐渐萎黯下去。他最后的视线定格在安然的脸庞。他看着安然,目光里有爱,依恋,不舍,还有——与亲人的生死诀别。白玉白兰受不了,冲出病房,任泪水夺眶而出。
“白桦——”
“桦啊——”
亲人们都在呼唤他。但白桦的意识已渐渐走远,他仿佛又回到了熟悉的家乡,他和安然一起捉蜜蜂,一起打渔,一起上学,一起在湖边看日落,他一生中最爱的安然就坐在他身边,金色的晚霞映照在她的脸上,如天使般美丽……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安然终于忍不住,捂住脸,失声痛哭。
安然上学要经过白桦的家,便自然而然地结伴同行。这是一段快乐的路程。
从农场东大门出来,穿过那片法国梧桐掩映下的卵石小道,经过县城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小小的集市,每天清晨,附近的农民挑着一担蔬菜,希望能去集市换几个钱。也有几个肉摊,屠户无一例外地腰肥膀子圆,还一脸横肉。鱼都是用脚盆或篓子装着,活蹦乱跳的。鸡鸭都被捆住了翅膀,在泥时上徒劳地嘶叫、跳跃着。那时,猪都是农户自己养的,鱼也是从河里捕捞,鸡鸭是吃虫子石子小鱼小虾长大的,它们还不知饲料为何物。
除了主菜,农户自己腌制的各季坛子菜,以及栀子花、丝瓜囊这些生活的配角,也会拿来出售,生意还挺不错。顾客呢,主要是农场的干部职工,安然大多认识,有时厌倦了与熟人打招呼,安然就走农场西大门。小集市旁有个供销社,历史很久远了,大门头顶还有一颗五角星。供销社生意清淡,只有少数的农民在那买东西。农场的干部职工大都是坐车去县城集体购物的。但无论如何,这段路程都是值得记念的,梧桐树下小草吐露着芬芳,清新的空气萦绕树丛,有种沁人心脾的舒适。集市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过是一段悠扬的旋律中跳跃的音符,浩瀚海洋中欢快的波涛,恰到好处,完美无瑕。
只需走上一刻钟,就到白桦家。白桦习惯了等安然出现在家门口,然后一起上路。安然学会骑自行车后,经过白桦家时,会刹住车,站在大堤上喊叫:“快点呀,白桦,要迟到了!”等白桦出现,两人便一起朝学校奔去。
湖区的早晨,小草上的露珠还被太阳蒸发掉,晶莹剔透的,美得令人窒息。柔和的太阳升起来后,投射到湖面,形成一层雾气,微风一吹,是一种令人舒适的凉爽。河堤下,牛儿懒洋洋地吃着草,有时会有鸭群经过,鸭子前赴后继地赶路,不小心在草丛留下几只鸭蛋,安然和白桦很宝贝地把鸭蛋藏进书包,上课时总忍不住掀开书包查看,见鸭蛋还在,两人便舒口气,相视而笑。
寒露一过,湖区便浓雾弥漫。立冬前后,浓雾笼罩下的河堤5米之内浑沌一片。白桦在前头探路,车铃不停地响着,安然跟在后面,不必担心撞到人。下坡的时候,白桦让安然走前面,他在后面搭把手,拖住安的车后架,两人小心翼翼地走着,短短的路程至少要耗费半个小时。每当此时,安然真希望自己是颗圆石子儿,可以一路滚下坡去。
安然第一次去白桦家是一个雨天。快放学了,大雨却没任何预兆地倾盆而下。安然等父母来接她,左顾右盼的。有同学等不及雨停,脱下外套罩在头顶,冲进雨幕中。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安越来越烦躁,坐立不安。白桦在一旁心平气和地做作业,见状安慰道:“你父母应该不会来了,要不你共我的伞吧,我到家了,你就可以打我的伞回家。”
父母没有来,而雨却没有停歇的意思。不一会,瓢泼大雨便把天空浇黑了。万般无奈,安然只得与白桦一块走。
白桦的雨伞并不大,但他尽量向安然倾斜,自己的半边身子露在伞外。泥土很溜滑,像泥鳅,没走几步,安然就仰天摔了一跤。白桦说:“这样走不行,还得摔跤的,必须把鞋袜脱掉。”他边说边示范,脱掉鞋袜,用脚趾紧紧勾住地面。安然只得照办。
没想到赤着脚还是打滑,安然又摔了一跤。白桦叹口气,扶她起来,直接把她背到背上。白桦一手提着鞋,一只手护住安然的腿,小小的身躯勾偻着,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吃力。安然伏在白桦背上,双手撑起雨伞。很多年后,每当回想起这一幕,安然便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
他们走得很慢,到白桦家时,天已经擦黑。安然一身泥浆,又冷又饿。白桦一脸紫涨,身体负荷已近极限。白桦的母亲金枝站在屋檐下张望,见儿子背着安然归来,很是惊讶,但她很快将两人接进屋,什么都没说。金枝五官端正,脸颊饱满,隐隐约约可判断出,年轻时也是标致的美人。只是岁月不饶人,她额前间杂的白发出卖了她的辛苦与操劳。
金枝见安然脸上身上全是泥,狼狈不堪,笑着说:“这是书记家的千金吧,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怎么弄成泥人了,”金枝找来白桦姐姐的衣服给安换下,热情招呼道:“安然哪,就在我家吃饭,吃完饭身子暖和了再回家,就不会感冒。”
金枝满面笑容招待安然坐下,然后手脚麻利地动手做饭。
6岁的安不会想到,这将是她的家,是充满了欢笑与心酸,却永远无法与白桦共同生活的家。
白桦家的厨房与主屋分开,很长,后面一截隔成了猪栏,安然坐在灶台边,很清晰地感受到了猪的味道,她强忍着,不做声。
白桦家没有责任田,白桦的父亲在农场渔业队看管渔塘,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养了两头猪和几十只鸡。白桦的父亲话语不多,常年日晒雨淋的脸像风干了的腊肉——黑瘦而紧致。他一言不发地往灶台里添柴,身后是用围子围起来的已捆扎好的柴火。金枝从鸡窝里摸出两只鸡蛋,又从蓖篮里拿出两片熏鱼,不一会就做好了几道菜。
安然靠近灶台坐着,身体渐渐暖和了,粉嫩的小脸红扑扑的,在灯光的映衬下光洁非凡。金枝搬把凳子坐在安然身边,慈爱地看着她吃饭,不时感叹道:“安然真漂亮啊,以后得找个什么样的好人家!”
安然吃完一碗饭,金枝赶忙替她添满第二碗。安然想把鱼身翻过来,金枝制止她道:“安然,咱们家吃鱼从来不翻边的,人在吃,天在看,白桦的爸爸经常出湖打渔,图个平安、心安。”
安然冲金枝笑笑。她虽然不太理解,但她认为,白桦的母亲看上去既温柔又慈祥,说的话肯定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