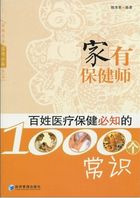荒原狼哈里作为典型的自杀者常常能把他的明显的弱点变成力量和支柱,在他的想象中,通向死亡的路随时都为他敞开着。因而,他多愁善感,充满幻想,不仅如此。他还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这样一来任何失望、痛苦、恶劣的生活境遇都会马上唤醒潜伏在他身上以一死而求解脱的愿望。久而久之,他把这种倾向发展成一套有益于生的哲学。他想,那扇太平门始终为他敞开着,这种想法给他力量,使他好奇,去饱尝各种痛苦和劣境,在他遭遇不幸的时候,有时他会有一种类似幸灾乐祸的感觉,他想:“我倒要看看,一个人到底能忍受多少苦难!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把太平门一开就摆脱了劫数。”47岁那年,他忽然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侥幸的、不无幽默的妙想,这个妙想常常使他兴奋。
他把五十岁的生日定为他可以自杀的日子。他说服自己在这一天他可以根据当天的情绪决定是否利用太平门。不管他还会遇到什么情况,经历怎么样的痛苦和辛酸,所有这一切都不再遥遥无期了。因此当他由于某种原因遭遇种种特殊的痛苦和损失的时候,他就对痛苦说:“你等着吧,再过两年,我就能主宰你们了!”
然后,他满心喜悦地去想象: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早晨,他拿起刮脸刀,辞别一切痛苦,走出太平门,随手把门关上时,信件和贺词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那时,一切都无所谓了。哈里最终有没有自杀,作者说他没有得知,这并不重要,因为哈里早在心里将自己的灵魂杀死了。
其实许多诗人就是类似哈里的人。他们的人格是分裂的,有两个灵魂,两种本性,他们身上既有圣洁美好的东西,又有肮脏丑恶的东西,既能感受光明和幸福,又能感受黑暗和痛苦,两者既互相敌视,又互相并存,犹如哈里身上的狼和人一样。他们生活极不安宁,有时在他们那极少的感到幸福的瞬间,诗人会体验到一种无比强烈、异常美妙的东西,这瞬间幸福的波涛有如滔天白浪高高耸起,冲出苦海,这昙花一现似的幸福绚烂辉煌,照亮了诗人的整个灵魂,于是这时苦海之上罕见的然而又是瞬息即逝的幸福之花——文学作品便产生了。因而他们不是通常意义的诗人,他们的生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是一种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犹如汹涌的波涛拍击海岸,永无休止。他们的生活是不幸的,有时超尘脱俗,有时又混乱不堪,而一旦人们不愿在那罕见的、超越尘世的生活而闪闪发光的作品中去探寻生活的意义的话,他们的生活便变得毫无意义。于是他们会认为整个人类生活也许是个大错,是人类之母夏娃的怪胎,是大自然粗野的、没有成功的尝试。他们活着也是个大错。于是成为哈里型的自杀者。
自古以来,人们最为赞赏的自杀恐怕还是英雄之死,人类自明确进化以来,英雄就一直是人类光荣和赞美的中心,人们对懦夫总是嗤之以鼻。因此英雄之死自然也成为诗人注目的重要对象,在英雄的身上寄托着他们超越死亡的理想。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人固有一死,或迟或早而已,但这时间上的差别却是人在死亡上的主要差别。唯其如此,非正常死亡才显得那么沉重。有的死亡甚至可以具有极大的意义,它是对人一生的最后的结论。尽管英雄不必都要有一个壮丽或轰轰烈烈的死,但是,凡能壮丽地死去者几乎都可以算作英雄。有的人,以前并未作出过任何奇功伟业,只是在某种紧要关头,他选择了一个非凡的死,从而把自己一下子提升到一个不平凡的境界,用死亡赢得了不朽。
中国古代自先秦时代就有为“义”不顾身家性命的“侠义”精神,发展到秦汉以后的“尽忠报国”的忠烈行为,尽管精神层次不同,其蕴涵的时代内容也有差异,但英雄主义的本色确是一脉相承的,不管是杀身取“义”,还是杀身成“仁”,都达到了舍生忘死、牺牲自我的精神境界。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那些杀身取“义”的刺客,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为报“知遇之恩”而不惜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无论是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的豫让,还是为报严仲子的知己之情的聂政,抑或是为报燕太子的知遇之礼的荆轲,都是信守诺言,情有所钟,矢志不悔,不负所约,不避刀斧,毅然赴死。他们的故事读来惊心动魄,让人感佩。特别是荆轲刺秦王,其行之壮烈在中国家喻户晓,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其悲壮的英雄气概流传至今。类似的故事在表现先秦时代社会生活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故事,石乞为白公而受烹,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不中而被诛等。不过写得最具悲剧色彩和英雄本色的还是司马迁笔下的楚霸王项羽的自杀。楚汉相争,项羽最后被刘邦大军围困于垓下,兵少食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一曲,唱出了流传千古的霸王别姬:“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天亮后项羽率领余部杀出重围,面对仅剩的27人,他不无感伤地说道: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觽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力拔山河的盖世英雄项羽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天意,又不肯渡江苟且偷生,愧对江东父老,觉得唯有一死才是英雄所为,于是从容自刎,甚至满足了敌人的愿望。
自古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但人们惟独对失败的英雄项羽是个例外,就连写惯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婉约派词人的代表李清照也为项羽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对他的自杀万分惋惜而赞赏有加,写下了豪气冲天、为人们广为传诵的五言绝句:“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倘若项羽的杀身成“仁”比先秦刺客的舍生取“义”要震撼人心的话,那么,“杨家将”的故事在宋、元以后的古代中国则更是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杨家几代人为保卫“大宋江山”,“尽忠报国”而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浴血奋战,其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感人的精神在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的作品中被传诵。“杨家将”的故事始于老令公杨业兵败被围,誓死不降,于两狼山碰碑而死。
《杨家将演义》(即《北宋志传》)描述了这壮烈的一幕:
时杨业与番兵鏖战不已,身上血映征袍。因登高而望,见四下皆是劲敌,乃长叹曰:“本欲立尺寸功以报国,不期竟至于此!吾之存亡未知,若使更被番人所擒,辱莫大焉。”视部下,尚有百余人。业谓曰:
“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可速沿山走回,以报天子。”众泣曰:“将军为王事到此,吾辈安忍生还?”遂拥业走出胡原,见一石碑,上刻“李陵碑”三字。业自思曰:“汉李陵不忠于国,安用此为哉?”
顾谓众军曰:“吾不能保汝等,此处是我报主之所,众人当自为计。”
言罢,抛了金盔,连叫数声:“皇天!皇天!实鉴此心。”遂触碑而死。
可惜太原豪杰,今朝一命胡尘。静轩有诗叹曰:
矢尽兵亡战力摧,陈家谷口马难回。李陵碑下成大节,千古行人为感悲。
杨业碰碑而死的“忠烈”行为,体现了他“尽忠报国”信念的执着,也显示了他在死亡面前所达到的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作者没有去渲染死的恐怖和痛苦,而是着力表现主人公的坚定决绝、镇定自若、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情状,让英雄主义的精神之光掩盖了死神的阴影,使读者在悲壮的情境中感觉到一种昂扬的情致,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教化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