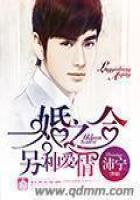玄霄呆呆坐在一只灰鼠搭子的红木椅子边上,只直直对着火盆里夹着蓝焰的银炭火上面葳着的那只煎药的银銱子,手边的红木小桌子上称过药材的小银称和当归、陈皮、芍药、紫苏、桔梗等等皆是一色纸包散着。
暖阁里满是药香。窗外的大雪片子,一片片划出绚烂圆弧蹁跹飘摇的翻飞,落的满院满廊。因着老太太自己是雪天里的生辰,且这洪都(南昌的明称)城中是极罕见落雪的,故而只命打扫了回廊人行处,其余一概留着。
那银銱子上浮浮的一层药渣沫子,玄霄在旁见了,便放下手里用来扇火儿的绘了四美图的团扇,拿旁边的铜片筛子小心滤了,又提起旁边风炉上一个滚水的紫铜壶儿,略略加了些水,继续煎着药。
身后厚厚的棉布帘子掀了起来,玄霄抬头看时,是大太太房里的一个小丫头,年纪身量尚小,并没有长成,只是浓眉凤眼,很是容易认。她带一对红豆镶银的耳坠子,绾着双髻,身上是春嫩青碧色交领绸缎短袄,下配着笋色马面裙,腰侧挂一个五福彩绣荷包。
身上面上还有没化尽的扑扑风雪,带进来一身寒气。
这小丫头见了玄霄,又向内里指一指,眼神询问,口中道“只玄霄姐姐一个人么?”
玄霄看了看火,用旁边的火钳子移了银銱子,又添上一块银炭,方又将银銱子架好,有些黯然的瞥了瞥那丫头,递过去一方棉帕,示意她擦擦头上身上,又拉过一只椅子与她坐,方道“二小姐不知何时遣了雪鸢去回了老太太,说是身上好多了,想去请老太太安,老太太准了,这便去了。谁知这一去,温言和老太太说笑一回,老太太便准了二小姐,前去二门内的那排针线上的工房院子,看问她的嫁衣嫁妆的事。”
说完自言自语的撇撇嘴,继续看向那银銱子中的药,心中叹道“真是变了,从前是不喜欢雪鸢那冒失性子的,如今却是冷了我,只不知是否疑我。”
那小丫头揩完了雪,又脱了两只溅半湿的绣鞋,靠近火炉嘻嘻笑道“二小姐不在,那我坐着烤烤火儿,与姐姐说说话儿,刚玩了会子雪,真是冷呢。”
玄霄看她烤在一边的半湿绣鞋,一戳她的脑袋道“叫你臭美,多早晚天气,还穿这么单薄的一双鞋子,”说着,又将她拉近了些烤着火,笑道“你可是来我这里偷懒的吧。”
正说话间,但见那银銱子上葳的药火候到了,玄霄便起身拿了旁边一个带着暖套的琉璃双儿葫芦样平底瓶儿将药汁子细细滤进去,方又旋上上面的一只浮球和外面的铝盖子,又套上暖套子,提起刚才加了热水的紫铜壶给暖套子和琉璃瓶儿中间灌上热水,合了上面的封子好做保温之用。
麻利的弄完了,又细细分类包好了药,收拾一众东西到一侧。方又对那小丫头道“文影你来的正好,小姐这是最后一幅药了,余下的你依旧包了给太太送回去吧,横竖也用不到的了。”
文影俏脸迎上来,笑嘻嘻道“我才不去麻烦那个,多这么一点子,姐姐自己留着吃便是了。”
玄霄又去西侧给旁边的薰笼添了火,一边将薰好的衣衫去下来,提起旁侧一个炭斗,添了炭,便等着炭斗热了好熨烫衣衫,一边又挪挪椅子,笑对那小丫头啐道:“药也是混吃的?仔细好人吃出病来。”
文影哈哈笑了,仍旧将绣鞋挪在火盆边烤着,道“二小姐出去多久了?看针线看这么大会子,从前二小姐从不管这些事的。”
玄霄兀自摇摇头,“这怎知道呢,别说是你了,便是我们几个跟着她长大的,也越发看不出她的行事了。”
她自然是看不出诸蘅玉为何要去看针线和绣嫁衣的,只因着诸蘅玉很是好奇,这古时美轮美奂的绣品宫装到底是个什么制法儿?
前一世病逝前,一直是同样学着考古的一个爱慕她的师兄照顾她,后来因着她的病靡费钱财,师兄才兼了职,违背考古着文化保护初衷的参与了为盗墓者设计定案的事情,双亲因着她的弟弟结婚又生了孩子,皆一股脑的前去照顾宝贝孙子,哪里还有谁理会她这个先天病弱的女儿,只有师兄,纵然因着她不愿拖累,始终未应允他结婚,却是陪伴照顾了她,直至她沉梦长逝闯入这个灵魂。而从师兄拍摄的一些明代嫁衣文物看,和如今真真实实的看着这一件件物品出自人工,那种激动之情是不为外人所明白的。
这里的雪下得一样美,几千年几万年,一样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一样的琳琅满目,琼瑶匝地,一样的涂抹树梢房垣,催开百花迎春,用透明洁白的灵魂,画一个万紫千红的世界。绕过玉泉和怡园的假山,又沿路过了一处竹亭,亭山都是张思宜的手笔,气势绵延,再燃上雪色,端的不似人间。
出了二角门向外看去,便是四合环抱在大院中的一个小靠院落,背面当南三间,正中一间大殿,东面一扇门开向西侧回廊,两列皆可通向大院,院子里几棵老桐树,还有几排竹子交叉的搭子架子,本是晾晒之用。竹搭子上的布匹因着下雪都收了进去,染缸子也各自上了盖子,旁侧一口水井,一切银装素裹。
“小姐,仔细路滑,”雪鸢穿着小麓皮靴子,打着油纸伞儿,两侧头发梳了鞭子又用丝带扎成髻子,上面别两只新鲜腊梅花儿,水桃色灰鼠皮衬里子镶边对襟的圆领儿中袖皮袄子,里面是竖领长袄和马面裙,只扶着诸蘅玉,眼神活泼的紧。
诸蘅玉则披了大红绣金梅花的貂鼠披风,衬着白绫袄儿,带了金钏玉佩,风帽压得低低的,一步步扶着向院中针线上的那间行去。
身后前不远还有两个婆子先前去打招呼的,皆是老太太房里的。
“小姐,”雪鸢忽的止了步子,面上有些微红,轻声道“小姐,那样做,针线上的人不会吃挂落么?”
诸蘅玉忙和她调皮的比划了一个嘘的口型,压低声音道“小厮们的衣袍最不费钱,你只留下一吊钱便是,偷偷裹了两套到披风里便是了,待你外头去买回一两套,回来时再偷偷送了来,一定无事的。”
雪鸢听的眉飞色舞,连连点头。两人方跟上了前面的婆子,一应人等跨进绣堂门槛。屋里十多个姑娘,还有四五个嬷嬷,见了这边两个婆子都起身笑迎了来。
其中一个婆子便对为首的一个嬷嬷道“房姑妈快坐,大家都做自己的吧,二小姐想来看看针线上置备婚事的绣活,老太太想着她也闷,便是来看个趣儿,大家都别拘谨着,我们几个且去外间茶房坐坐,待二小姐看完再跟了回去赴命。”
一众人等都笑说是,为首的嬷嬷招呼了两个婆子自去坐,诸蘅玉则绕着这班花枝招展的绣娘姑娘们看绣活儿。且看过她们身旁的一排针盒子,里面苏针,牛毛针,皖针,蜀针,针针各式型号足有七八样,一排子针盒子倒有百十来钟样式,针法自也是各不相同的。又看那丝线盒子,更是排的一列列,单单那绿色,便排了地绿、葵绿、豆青绿、灰绿、墨绿、水绿、油绿,湖绿、蓝绿足有几十种,红色,也是满满铺排了银红、粉红、水红、湘红、墨红、绛红、铁锈红、水密红、罗红、彩绘红、荷花红、牡丹红,一列列又是几十种。
从一边看一色色由冷到暖,从另一边看,一行行由浅入深。
诸蘅玉心中暗自赞叹,不过是一户大户人家的针线上,就是如此,想来当年那赫赫声名的江南织造上,真不知得是如何一个细致周详。
眼神再一仔细看过,便看到当中一个撑着一只一丈光景大绣绷子在做活儿的姑娘。那秀绷子上正是一色大红通袖的吉服样子。她身旁几人则各自执着小绣绷子,在那里绣着衣身上的云肩,通袖襕,膝襕等纹样。
看到这里,诸蘅玉不由移了步子,便堪堪走到那姑娘的大秀绷子旁边站住了脚。那姑娘穿着藕荷色的比甲,里面配了对开的杏色裙袄子,头发梳了一个堆云髻,插一支彩绣堆云花儿,紫丁香耳坠子,衬得那脖领子益发白腻。
见诸蘅玉过来,她便大方起针抿了抿鬓发,一边笑了笑,一边继续引针做她的一处鸳鸯戏水的活计,做到一处又比了色,一个个比了线,先绣出经纬,又用浅一些的同色系绣线在其中密密织绣,手上灵巧非常。
诸蘅玉见她将所有要镶嵌珠玉的绣物各自留出地方,便指了指问道“可是要登记造册前去统一支领了上面的镶嵌再统一补绣?”
那姑娘含笑点头道“姑娘聪慧。”
诸蘅玉看向雪鸢,但见她点了点头,便又笑向那姑娘道“真辛苦你们了。”一边说,一边移了步子向外去。
里面为首的嬷嬷见了,方叫了茶房那边的婆子,几人一径又送了诸蘅玉回到老太太处复命,兼之老太太晚上留了饭,大家也好一处吃饭。
诸蘅玉走到半路,便对雪鸢说,“回去取个手炉子吧,顺便让玄霄来伺候就是,你也忙了这半晌,回去歇歇,也暖暖身子。”
雪鸢笑眯眯回了“是,”便向一侧去了。
两个婆子则扶了诸蘅玉,向老太太屋那边继续走。
风雪刮着,调皮的雪花打在睫毛上,诸蘅玉不由的哈了热气向上吹那雪花,两个婆子见了也不由的笑了。
待到了老太太的暖阁里,秋萍,屏风几个大丫头皆已伺候在四周,中间一张八仙桌子摆了饭,几位太太立在一侧。
见诸蘅玉等回来,郭氏忙笑盈盈说道“好长腿子,正跟上端碗吃饭的时候。”
诸蘅玉解了披风,那边赶来的玄霄忙接了放在一侧,又为诸蘅玉整了鬓发。诸蘅玉这方才上前给老太太和各位太太一一行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