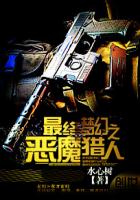平南的十月,是气候最宜人的季节,到处都盛开着各种鲜艳的花朵。但是在这个时节,最美丽的花朵要数蝴蝶花了。
蝴蝶花树高一丈许,不但绿色的树叶像蝴蝶,鲜艳的花朵更像美丽的蝴蝶。蝴蝶花有红色和白色两个品种。两种树木的叶子极其相似,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花朵的形状也一样,只是颜色不同罢了。若遇微风轻拂,白蝴蝶花、红蝴蝶花和绿色的树叶就像千万只白蝴蝶、红蝴蝶、绿蝴蝶在扇动着翅膀翩翩起舞。正是因为这种缘故,平南境内不管是达官贵人的府邸,还是乡村贫民的屋前,都喜欢种上几棵这样的花树。
平南县城东翠山脚下的旧罗城彭得贵驻军衙门前,也有好些棵蝴蝶树。红、白两个品种各有几株。彭得贵每天闲着没事。就叫他的两名舞女,一个穿着白色的舞衣,一个穿着红色的舞衣,在蝴蝶树下为他跳舞。
两名舞女还不到十五岁,因未曾受过专门的培训,舞跳的并不娴熟、优雅,歌声也并不优美动听。但那身姿和脸蛋儿还是不错的,足以让彭得贵神魂颠倒。彭得贵异想天开地给她们取了个名字,一个叫白蝴蝶,一个叫红蝴蝶。平常一个穿白色衣服。一个穿红色衣服。跳舞时,自然也是一个穿白色舞衣,一个穿红色舞衣了。
令彭得贵遗憾的是没有一支乐队,要是有那么一支乐队伴奏,两个妙龄舞女在美妙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他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美妙的音乐和舞蹈,那该是多么舒心的日子。眼前虽然没有这些东西,但坐在椅子上的彭得贵的脑海里却有这种场景。
两个舞女一边唱,一边跳。刚刚跳完一支舞,彭得贵就笑眯眯地拍起掌来。两个舞女便跑过去,一左一右地偎在彭得贵的怀里。彭得贵在白蝴蝶的脸上亲一口,又转过去在红蝴蝶的脸上亲一口,作为对她们的赏赐。
彭得贵亲了两名舞女,然后对她们说:“老子明年请一个能歌善舞的骚娘们儿把你俩好好调教调教。使你们的歌舞超过皇宫里的歌女,然后把你们送进皇宫,献给皇上,老子就是大功臣了。老子还要建一支乐队,专门为我的心肝宝贝儿伴奏,你们说好不好?”
两个舞女仰起脸来看着彭得贵,撒娇地说:“好!当然好!”
“那你们就得努力把舞给老子跳好呢!”
彭得贵搂着两个舞女正在得意,突然有个亲兵跑过来大声禀报说:“总爷,出大事啦!”
彭得贵仍旧搂着两个舞女,看也不看那亲兵一眼,慢声慢气地问:“啥大事儿,看把你急成这样?”
亲兵说:“有个叫石满山的百总爷,带着四个亲兵在宾至如归饭庄喝酒打人,砸了人家的店,被巡检司的人抓走了。”
“是不是将人家打死了?”彭得贵瞪着眼睛问。
“没有。只是打了许老板几个耳光。”亲兵说。
“这有啥不得了的?就是杀了人也没啥不得了。这里的刁民不杀他几个,你就镇不住。没有不得了的事。去传老子的话,叫他们放人!”彭得贵说完,又低头和舞女说起悄悄话来。
亲兵站着不动,欲言又止。
彭得贵发火了:“还给老子还站着干啥?羡慕老子的两个美人儿是不是?混帐东西!”
亲兵委屈地说:“总爷,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那石满山在县衙大堂上说的话对你非常不利。”
“他说老子什么坏话了?只要他有那个胆,老子把他抓回来给砍了!”彭得贵有恃无恐地说,“他到底说什么了,还不快吐!”
亲兵嗫嚅着说:“他说……他说总爷你克扣军饷,七八个月没给他们发饷了,吃的饭食很不好。吕知县叫他到朝廷去告你……”
彭得贵一听这话暴跳如雷,猛地把两个舞女一推,站起来大声说:“石满山他个狗娘养的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给老子编出这种话来!走,跟老子到县衙去要人!他吕廷云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凭啥审我的人!”
两个舞女皱着眉头,好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
彭得贵这个绿营千总是当年用三千两银子捐来的。这捐官的事情,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就是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从秦始皇“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之始,到西汉则形成制度。此后历代都有卖官之举。但在古代,朝廷实行“捐纳”制度主要是为了筹措军饷和赈灾。清朝初期也曾实行过捐纳制度。文官、武官都可以拿银子买得。捐官的到京城交银,叫做“上兑”,由户部填发取得某官资格的证明,叫做“执照”(部照)。在外省捐官的,由布政司先发给“实收”,作为收款的凭据,然后再咨请户部发给执照。但是这种捐官捐得的都是虚衔,只是买得一种荣誉而已。若要得到实缺,还要花钱捐“花样”,捐了“花样”就可以得到实缺,正儿八经地做官了。
彭得贵就是花了两笔银子买的个营千总实缺。捐实缺只实行了几年便废除了。彭得贵运气好,刚刚赶上了那种千古未有的机遇。虽然花的银子多些,但他这几年捞的银子早已翻出了好几倍。他克扣军饷,士兵们就去骚扰老百姓。或到饭馆里吃东西不给钱,或到城外老百姓家里去抓鸡逮鸭子。他明明知道也不去管,所以这里老百姓说他的兵是匪兵,曾经多次告到县衙里,但是以前的县令不敢得罪彭得贵。毕竟人家是正六品官员,是浔州卫千户所的营千总,当年平南县匪患严重,县城数次被攻破,县官被杀,才奉命移驻平南对付土匪的。县官哪里管得了他的事?所以那些县令千方百计把事情往外推,说什么士兵犯法,应该到驻军衙门去告状,地方衙门管不了军营的事。
偏偏就有那么一些老百姓当真就跑到驻军衙门去告状,彭得贵听了老百姓的陈述,反而火冒三丈:“吃你几只鸡鸭又咋啦?没有他们在这儿,土匪来了不但抢你东西,还杀人放火呢。今后再有这种擅闯军营告刁状的,一律五十军棍,再给老子拖出去!”从此再没人敢到军营去告状。
现在吕知县却大不一样,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管他天王老子,只要在平南境内犯了事儿,他都要管。彭得贵也知道吕知县是个铁面无私的人,认为他为了标榜自己清正廉洁(在彭得贵眼中,吕知县是为了标榜自己,落个好名声),竟然处处与他作对,当众把他克扣军饷,放纵部下祸害老百姓的事儿给抖落出来,还怂恿石满山去告他,心中十分生气。决定亲自前去要人。
彭得贵是大块头,个子和吕知县差不多,但他吃得太肥,走了不多几步路便有些气喘吁吁。吕知县得到禀报,早已走出府邸等在那儿。两人一见面,互相拱拱手,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客套起来。
在吕知县的客厅里坐下来后,彭得贵便迫不及待地说明他的来意:“明府啊,我的部下太不争气,尽给老子捅娄子。好歹这次是犯在你手里。你好好管教管教也是应该的。如果你已经责罚了他,出了你心中的恶气,就把他交给我,老子再教训教训他,看以后谁还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犯事儿。”
吕知县说:“这恐怕不妥吧。石满山是在本官地面上犯的事,理当由本官审判、定罪收监。然后上报朝廷,等候处置。若交总爷你去处理,便只是个挨军棍的处分,那就太便宜他了。”
“哎哟,这点小事儿,不挨顿军棍了事,还能怎么处置?”
吕知县说:“这还是小事?本县好不容易才把商家吸引到这里安顿下来。这里的商业刚刚才有了点起色,经他们这么一闹,大家纷纷嚷着要关门走人,这里不又将是一座空城?”
“好歹你把他们交给我,保证以后不再有人敢在你的地盘上生事儿。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
吕知县说:“不能交给你。谁不知道总爷你爱兵如子。一旦交给你带回去,立马就给放了,以后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到那时,巡检司的人想再抓他,就难了。”
“那么你想怎样处置他们?”
“还要关些日子。本县还要派人搜集他们的罪证。如果没有其它罪行,打几板子,关几天也就算了。如果还有其它罪行,本县便当堂审理,录了口供,画了押,再报刑部判处。”
“这么说,你一点情面也不讲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嘛。你这样固执下去,就太不够意思了!”
吕知县说:“这个情面不能讲,一切都得依照大清刑律办事。如果徇私枉法,上对不起圣上,下对不起老百姓。这样的事我吕廷云绝对不会做。所以还请彭总爷谅解。”
彭得贵紧紧盯住吕知县的眼睛问:“他都交待了些啥?”
吕知县避开他的目光,说:“他什么都不肯交待。他说,要银子没得,要命倒有一条。你看他横不横?所以本县得挫挫他的锐气,多关他些时间,让他尝尝坐牢的滋味。”
“如果真是这样,我倒也没什么可说。要是你耍什么阴谋,我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彭得贵见吕知县好说歹说都不放人,一脸的怒气。话没说完,人已站起来了。一边说,一边就往外走。
吕知县知道彭得贵前来要人的目的,担心他把石满山要回去后杀人灭口,所以不肯答应他的要求。彭得贵则以为吕知县一心想抓个有分量的证据在手里把自己扳倒,临走时便特意警告吕知县不要耍什么花招。
吕知县见彭得贵那怒气冲冲的样子,笑嘻嘻地说:“彭总爷既然那么舍不得你的爱将,等我调查清楚了,只要他们再无别的什么罪行,一定毫发无损地送还给你。”
彭得贵回到军营,他的军师高以显立即跑过来问情况怎样。
彭得贵忿忿地说:“他硬是不给老子面子。说什么还要调查石满山其它的罪行,以便严厉惩处。他说他怕老子袒护自己的部下,不肯责罚,使他们变得更加骄横,所以不肯交给老子带回来。”
高以显眨巴了两下小眼睛,凑上去说:“大人,晚生认为他是在糊弄您。他口上说要严厉惩处,实际上是待如座上宾。您想,县官审犯人,哪有给犯人搬条凳子让他坐着交待罪行的?你过去在许多事情上与他闹翻了。显然他是想用军饷上的事儿把你扳倒。”说到这里,高以显把声音压得很低,“他是想把石满山留着做证人,然后上报朝廷。皇上如果派钦差大臣来彻查此事,他手中就有了一张王牌。石满山这人是万万留不得的。既然他不放人,我们不如来个……”高以显做了个杀人的动作。
高以显是彭得贵新近聘请的师爷。彭得贵好几起事情都受制于吕知县。罗大拿建议彭得贵请一名师爷,以便随时给他出谋划策,彭得贵于是就聘请了高以显。
彭得贵听了高以显的话,点点头,说:“老子也是这么想的,常言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吕知县十分清楚,彭得贵没将人带走,决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件事情上又不可能妥协,石满山已经把彭得贵克扣军饷,纵容部下到处抢劫的事捅了出来,这事如果让皇上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石满山一旦被彭得贵带回军营,必死无疑。彭得贵当然不会公开杀害,不过让他永远消失却是易如反掌。吕知县要想治理好平南,不把彭得贵扳倒或将其人马“礼送出境”,也是办不到或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既然不能妥协,那石满山就成了吕知县手中的一颗棋子。这颗棋子必须牢牢抓在手中,不能丢失。县衙的三班六房人员众多,颇为复杂。只有吕悝、雷横、孟刚、郭仲书、黄景华等人完全靠得住,所以吕知县不得不处处小心提防。
那天快吃晚饭的时候,孟刚怀揣一只小狗来到牢房,对石满山说:“送给你们一只小狗,免得你们寂寞。每顿饭先给它吃一点儿,不能亏了它。所谓每人省一口,喂条大花狗嘛。”说完,向石满山挤挤眼睛,微微一笑,然后一转身离开了。
石满山虽然性格直爽,心里不藏贼,但也决非是个傻子。他当然明白孟刚的意思。当狱卒把饭菜送进来的时候,他便拨了一些在地上,装出对小狗十分疼爱的样子说:“宝贝儿,快来吃晚饭了。快吃,快吃。吃饱些,长胖些,长胖些才好看哟。”
小狗吃着吃着,突然就哀嚎起来,满牢房乱跑。跑了不到一圈,倒在地上挣扎一阵就不动了。
石满山见状,吓出一身冷汗,立刻大叫:“快来人啦!有人在饭里下毒啦!”
一个狱卒跑过来说:“不要乱叫。你们中一些人也装作被毒死了。我立刻就去禀报太爷。”
吕知县得到禀报,立刻派人叫来典狱长,和他一起去盘查。可是厨房里人多,饭菜盛好后过了许久,专责送饭的人才来送走。中途又转过一次手,一时竟无从查起。吕知县和典狱长等人又来到监狱,询问石满山是怎样发觉饭菜里有毒的。
石满山说:“吃饭之前,从外面跑进来一只小狗,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就没让它出去。饭菜送来的时候,我首先给他弄了些。见它吃得很香,我心里高兴,就只顾看,没动筷子。他们几个也纷纷凑过来看,要让小狗先吃一点。结果小狗才吃了几口,就哀叫起来,于是我就大叫饭里有毒,惊动了看守的官爷。”
吕知县听石满山说完,倒背着双手在屋内走了一圈,四处看了看,便默默地离开了。一行人跟在他的后面,谁也没做声。
夜晚的天空显得宁静而悠远。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天晚上天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大,特别亮。整个天空显得特别低,是往常所没有过的一种景象。这种天象也不知道要几十年,还是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总之,谁看了都会为之惊叹。到了后半夜,开始起风了。风力不大,树枝只是轻微地在摇晃,仔细地聆听,才能听出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呼呼声。街道上,商家的布幌子偶尔会发出几声“噼里啪啦”的响声,像有人在大街上奔跑一样。就在这时,平南县城监狱的房顶上,有一个黑影倏地一闪就不见了。过了片刻,又一个黑影倏地一闪也不见了。
傍晚才出现投毒事件,深夜又出现黑衣蒙面人,这平南县城真的不会平静了。
过了不到喝一盏茶的时间,又是一个黑影一闪,在牢房前巡逻的狱卒悄无声息地被放倒在地上。黑衣蒙面人从狱卒身上搜出钥匙,小心翼翼地开了锁,开了门,悄悄溜进了牢房。
牢房内地上的稻草上并排睡着五个囚犯。黑衣蒙面人手持利刃溜进去时,几个囚犯正打着鼾,睡得跟死过去了一般。黑衣蒙面人用利刃在一个汉子的脖子上轻轻一划,那汉子就直挺挺地失去了性命。当他手握利刃再去抹第二个汉子的脖子时,刚好那汉子翻了个身。利刃没割着喉管,却划伤了后脑勺。那汉子痛得大叫起来。他这一叫,惊得蒙面人一愣,也惊醒了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个反应最快,听到叫声立刻一跃而起,后退几步,揉了一下眼睛。当他看清了黑衣人的位置时,便一下子扑上去斗在一起。这个人正是石满山。其余两名汉子正要上前帮忙,见牢房门口还有一个蒙面人在望风,便躲在角落里先观察形势,再决定怎么做。
蒙面人手持利刃和石满山斗在一起,斗了多时,却不能把石满山怎么样。
石满山觉得眼前蒙面人的身形和动作有些眼熟,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来。他几次想冒险去揭掉蒙面人的面巾,但对方防守得很严,而且手中有利刃,占着优势,所以未能得手。他又想,要是对方能出声,或许也能分辨出是谁,于是一边见招拆招,一边说:“好汉,你为啥要来刺杀在下?在下犯了事,迟早也会被那些狗官弄死的,用得着你来取老子的命吗?你若是条汉子,就告知老子一声,让老子死个明白,你为啥要来刺杀老子,或者是谁派你来的。是好汉就吭一声,是****养的你就装哑巴!”
无论石满山怎样用激将法,怎样说出侮辱对方的话,那蒙面人只不作声。
石满山便说:“老子知道了,你是彭得贵派来的。彭得贵那杂种,早晚会不得好死。他克扣军饷,纵容士兵去祸害老百姓。老子的弟兄不愿去祸害老百姓,被饿得骨瘦如柴,做了些对不起商家的事。哪知却因此认识了一位好官。蒙面好汉,你不要再为彭得贵卖命了。他迟早要倒台的,不会有好下场……”
门口望风的蒙面人见他俩久战不下,心里非常着急。心想,这样下去,杀人不成,自己反而会身陷绝境,便跑进去助战。哪知他刚一动步,蹲在屋角的两名囚犯就截住他搏斗起来。他的武功并不怎么样,虽然手里拿着短刀,但两手难敌四拳,更无胜算。斗了一阵子,便渐处下风。心中一急,就喊道:“黄……快撤!”他本想喊“黄总爷快撤”,可是刚喊得一个“黄”字,就觉察到失言了,后面的“总爷”两个字才没喊出来。可是他们的身份还是暴露了。
石满山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彭得贵的爱将黄明海黄总爷!黄明海,你的官阶比老子高好几个等级,这武艺却并不怎么样啊!听老子一声劝,不要再死心塌地跟着彭得贵沆瀣一气了,不然,你也会跟着一起倒霉!”
刚才那个望风的蒙面人叫崔大鹏,也是彭得贵手下的一名正八品外委千总。他自知泄露了天机,回去要受罚,便一边招架,一边纠正说:“黄明刚大哥,快走。再晚一步可能就来不及了!”说完,率先就逃了出去。
石满山说:“崔大鹏,别扯谎了。老子还听不出你那嫩公鸡一样的破嗓音么?”
黄明海虚晃一刀,拔腿就逃。囚犯中追赶崔大鹏的唐义杰没追上对手,便回转身来拦截黄明海。黄明海一刀刺去,唐义杰侧身倒地躲了过去,但他倒地时却使出了一个钩脚,钩得黄明海一个踉跄,差点儿倒地。紧追而来的石满山正要伸手擒拿,结果还是慢了一点点,让他给逃掉了。
彭得贵见收买狱卒下毒,和派人刺杀石满山都不成功,心里十分着急。心想,这后脑上长反骨的石满山,一旦和冷面无情的吕廷云搅和在一起,他的日子就不会安宁。想来想去,暗的不行,干脆就来明的,自己好歹也是一个正六品武官,手里握着兵权,不信把你一个七品县官就没办法。
第二天,彭得贵带领全部人马一千余人,把平南县衙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骑着高头大马,率领一队亲兵来到县衙门外,大声吼道:“吕廷云,快把罪犯石满山交出来!你们堂堂一个知县衙门,竟然窝藏军营罪犯,要告到朝廷,你该当何罪你知道吗?”
吕知县在吕悝、黄景华、雷横、孟刚及三班六房吏员、衙役的簇拥下,走出衙门站定后,大声说:“彭千总你也太欠考虑了。这县府衙门代表的是什么?你动用军队围困官府,这不是要造反吗?你是不是还想进来搜查、抓人?你太胆大包天了!”
彭得贵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啥叫造反?下级冒犯上级才叫造反。你是哪一级?几品官?我把你衙门包围了,只是为了不让罪犯逃跑,我要拿他们绳之以法。你却千方百计护着他们。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是放聪明点儿,再这样和我们军队扳手劲,你要后悔的!”
吕知县不卑不亢地说:“本县这官再小,也是朝廷委任的。你所要的人现在已不在我这儿。昨天晚上他的同伙把看守的狱卒给杀了,然后打开牢门放跑了。”
彭得贵一听,火气更大了:“你有啥证据说是他的同伙给放跑了?依我看,肯定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到底跑没跑,凭你一句话我就相信?昨天要人你不给,今天要人你说他跑了,明天我来要人,你不会又说他畏罪自杀了?不管怎样说,你都得把人给交出来!”
“这么说来,你硬是不信?昨天晚上他的同伙潜入牢房杀了两个人。现在他的同伙正藏在你的军营里。本县正想前去找你配合,抓杀人凶犯呢。”吕知县说完,一双犀利的目光紧紧盯着彭得贵。
彭得贵心虚地说:“你凭什么说杀人凶犯在我的军营里?”
“凭什么?昨天晚上两个杀人凶犯逃走时,其中一个无意中喊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就凭这一点,本县就可以断定两个杀人凶犯就在你的军营里。”吕知县说话时,那锐利的目光盯得彭得贵心里直发毛。
彭得贵正无言以对,显得十分难堪时,他新近聘请的幕府军师高以显赶忙说:“没想到吕明府还会编故事。故事编得再好听,拿不出证据,那就叫做血口喷人。”
彭得贵终于有了根救命的稻草,立刻又得意起来:“对。我也正想说你是血口喷人,又怕把你得罪了。说严重点,那真就叫做血口喷人!”
吕知县笑了起来:“真是笑话!你几时怕得罪了我?这样吧,我们这样争论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你说石满山还在我的衙门里,你可以派兵进去搜一搜。不过你搜得着搜不着,本县都要把你带兵包围本县衙门和搜查本县衙门的事情上奏朝廷,这是千古未有的奇事。除非有人想背叛朝廷,走上造反之路,才会干这种事!”
彭得贵听了吕知县最后这几句话,不觉心里一惊。但他强作镇静说:“谁看见我派兵包围你了?谁说我要搜你衙门了?你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想把我怎么样?你尽管上奏好了,我彭得贵身不颤,心不慌,吃得好,睡得香!”
吕知县轻蔑地说:“我这七品芝麻官虽小,可是皇上任命的。我知道你彭千总的本事大。要不是当今皇上及时废除可以捐纳实缺的陋规,你怕早就是一个游击将军了!”
吕知县的这几句话如钢锥扎进彭得贵的心里。
“放屁!”彭得贵恼羞成怒,知道说不过吕知县,便转身向他的部下大吼一声:“我们撤!”
吕知县望着彭得贵的背影,大声说:“彭千总有屁尽管蛮起放,何必一定要说在嘴巴上!”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身后的吏员、衙役们也忍不住笑起来。
彭得贵的人马刚刚从县衙门外撤走,就有一对老年夫妇前来告状。他们是县城郊外的农民。看见吕知县一班人正站在那儿目送彭得贵的人马撤离,便快步跑上前去跪倒在吕知县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哭诉:“青天大老爷,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天啦,咋是这样的嘛。这叫我们咋个活啊!天啦,他们咋能这么做啊……”
吕知县弯腰扶起两位老人,温和地说:“别哭,别哭。先把事情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出来本县听听。”
陈天奇老头先止住哭,抹着不断涌出来的眼泪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前年我和二弟两家人共同出钱买了一头小水牛,好不容易养大,今年刚刚教会拉犁。往几年没牛犁田的遭孽日子终于结束了,我们两家人好不高兴,都把它当做心肝宝贝儿。哪知上午彭千总手下一伙当兵的,二话不说就给牵走了。他们说嫩牛肉好吃,要牵回去杀了改善生活。这段时间牛是兄弟家在喂养。他们夫妻二人赶上去论理,那伙当兵的把我们兄弟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乡邻们把他抬回去放在床上,会不会死现在还说不清楚。我们那兄弟媳妇儿人还年轻,长相也很不错。那伙当兵的说,这娘们儿还有法整。硬生生把她拉到树林里给糟蹋了。他们一伙人十几个,尽是些十八九岁的壮汉,我那兄弟媳妇儿受不住,事后也没回家,就在树林里找根藤子吊……吊死了。”
老人说到最后,已泣不成声。
吕知县听完老人的哭诉,气得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周围的人听了也无不掉泪。
过了许久,吕知县才抹了抹眼睛,声音颤抖地说:“本县一定会替你们做主,替你们讨回公道。你们都到衙门里去,本县找人替你们写好状子,你们就回家等候消息。这伙人不好好收拾收拾,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
到了深夜,吕知县写好奏疏。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上天啊,助本县上奏成功吧!”
五更时分,远处的一声鸡鸣打破了平南县城夜空的寂静。接着四面八方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漫长的夜晚终于要结束了,整个平南又将迎来新的曙光。吕知县整整一个夜晚都没合眼,拟写奏疏就花了两个时辰,写好后又反复推敲,想让这篇文字能够打动康熙皇帝,使他下一道圣旨,或派一位钦差大臣来处理彭得贵军营发生的事情。然后又思考怎样将奏章直接交到康熙皇帝手中。按照惯例,外地官员的奏折,先由朝廷官员代交通政司,再转都察院,最后再呈到皇帝手中。也有交太监转皇上的,走这条路子一是太麻烦,二是要花不少银子。关系不到位,再大的案子也很难上达天听的。
几百年来,平南县遭受的创伤太为深重了。兵祸、灾害、********、官员贪腐、以及豪强的掠夺,使这里人口死亡、外迁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战争刚刚结束,民变刚刚平息,匪患稍微有所控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认真治理,平南的老百姓刚刚看到了一线希望,却叫彭得贵的一支人马又给搞得乌烟瘴气。有彭得贵带领人马驻扎在这里,平南的情况又可能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彭得贵职位高,手握兵权,背后有罗大拿撑腰,朝中亦有靠山,尽管他作恶多端,十恶不赦,要扳倒他也决非易事。然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让彭得贵伏法,平南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吕知县为这事儿思考了整整一夜,还是一筹莫展。直到鸡都快叫了,才朦朦胧胧睡去。
忽然,一阵说话的声音把吕知县吵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才知道天已经大亮了。
他正要翻身下床,王夫人跑进来说:“快起来,彭千总派人来了,说是要见你。”
“他派人来干什么?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吕知县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叫他们到大堂那边去。就说我在那边。”
王夫人给女仆如此这般地说了,女仆立刻到门口对彭得贵派来的那些人说:“我们家老爷已经去衙门了,你们还是到那边去见他吧!”
为首的小军官说:“我们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转告,只能在府邸相见。”说完,示意四个士兵抬上箱子就要进门。
女仆也不理睬他们。“砰”地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
小军官拿不定主意,犹豫了半天,只得带着士兵抬着箱子往县衙大堂那边去。到了衙门大堂,小军官看见吕知县从签押房里走出来,立刻上前向吕知县深深一揖,然后才将一封书信双手呈上。
吕知县问:“你们这是来干什么?”
小军官说:“我们是受彭总爷委派,给太爷送信,送东西。”
“他平白无故给我写信,送东西干啥?”
“我们也不知道,彭总爷只吩咐我们把信和东西给您送过来,别的什么也没说。信中肯定说得很清楚,太爷您还是自己看吧。”
吕知县把他们让到屋内,便打开书信看起来,信的内容大致是讲,彭得贵希望吕知县能够学习古时候的廉颇、蔺相如,和他来个“将相和”,从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信中还说了许多恭维吕知县的话。为了表示和好的诚意,特地送上三千两纹银。最后以一首打油诗结尾。诗的内容是:“千里做官只为钱,仁兄何必如此廉。倘若它日挂印去,妻儿老小咋个办?”
吕知县看完信,冷笑一声,在心中说:“自己毫无悔改之意,还想拉本县下水,打错了算盘!”但面上却装作略有所悟,还特意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来盯着小军官,说:“你们还是把银子抬回去吧。本县衙门虽然拮据,也不用彭总爷来周济。自古以来只有地方官府给军队筹饷的,哪有军队节约军饷周济地方官府的道理。你们彭总爷是搞错了吧!”
小军官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是这样的。太爷,彭总爷这银子是送给您个人的,不是送给官府衙门的,难道他在信上没有说清楚吗?您赶快收下吧,小的好回去交差。您赶快收下吧!”
吕知县笑了笑,说:“信上咋没说清楚。只是这银子一旦收下,就说不清楚了。既然你怕回去不好交差,本县就回他一封信,告知他这银子不能收的原因,你们不是就好交差了吗?”
“不,不用写信,您只要把银子收下就行了。如果太爷一定要写信,也请先把银子收下吧。太爷不收银子,彭总爷会责怪小的不会办事。回去一定会挨一顿臭骂。”
小军官显得很急躁,他万万没想到送礼也这么麻烦。送这么大的礼,人家竟然还不想要,心想:“是不是还嫌少?也真是的!”
吕知县看着小军官那着急的样子,说:“好好,你不用着急,本县收下这银子就是了。不过,你得把这封信亲手交给彭总爷。”
小军官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吕知县展开笺纸,提起笔来一挥而就。片刻后,将信封好,交给小军官。几个娃娃兵兴高采烈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