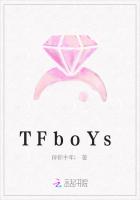谢然的马车通过南坊桥时,他看见几个东张西望的家伙,怎么看都像是望风踩点的贼人,叫冯马停下车去询问,几个家伙躲避着逃开了。
此时府里已经整顿好了,看不出大风过后的狼狈,谢然吩咐了府里的扈从和护院,让他们警惕。同时给还在衙门里忙碌的父亲报了信,毕竟南坊这边住的都是有地位的人家,风灾之后,趁火打劫的贼人不得不防。
午夜里一声惨叫惊醒沉睡的人们,兵刃交加的的声响从谢府方向传了出来,阵激烈的打斗声就像被点着的火药桶一下子让全城都乱了起来。火光四起,一时间掩盖了还未熄灭的灯火的光芒。不过一阵整齐的喊杀声在南城慢慢地向前推进,直到和西城的一队人马汇合,终于压制了乱哄哄的局面。
上百个蒙着面的贼人被围困在西城的内墙下,牛四和焦大带领着学徒园的少年们堵住了南边的通道,府兵和衙役们围着北边的巷口,各家各府的家丁拿着棍棒徐徐向前,将这伙来路不明的贼人挤压进了死胡同口。得到副都督的手令,两百在廉州港停靠的水兵手持强弩已经压阵上来,而城内的大火也被扑灭了,合浦县把被击伤杀死贼人收拢起来,还有落单的贼人全都被干翻了捆绑押进了大牢。
此时紧张的对峙没有缓和下来,贼人显然没想到城里早有准备,制造混乱浑水摸鱼已经落空,被逼上绝路的众贼不愿束手就擒。一个明显是头的彪形大汉怒吼一声就冲出来想要拼死一搏,但是南齐军方大匠制作的强弩却没给他们近身的机会,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名弓手早被万箭穿心。密集的箭阵像割草机一样收割着巷子里的生命,鲜血汇成了溪流将护城河都染红了。
水兵校尉拉开头目的黑布,死后仍然狰狞万分的脸上那三道刀疤让校尉惊呼了起来,此人正是海上恶名昭彰的海盗头子古老三。自廉州开港免税之后,南下西去的航路更加繁忙,海盗也多了起来,最有名的就是下龙湾咕噜岛上的古家兄弟。去年交州水师南巡将咕噜岛连根拔起,古老大和古老二被吊死在广州港口,古老三的船被击沉在海上,大家都以为他葬身鱼腹,没想到竟然还活着,潜到了廉州城来。
原来那日被交州水师击沉了座船之后,古老三竟然蛰伏在水师的船底下,一直随船到了广州,目睹了两个哥哥被吊死却无能为力,发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咕噜岛的军师通过几个以前有勾连的商人联系上了散落在外的下属,古老三却怕人多被察觉,而且广州城是交州水师的大本营,城里又有几千都督府府兵,见广州事不可为就转向防备松懈的副都督所廉州,正好遇上台风,如此天赐良机,于是就有了今晚的放火袭城。
一晚的血战,海盗的尸体被收集在城隍庙下火化了,围观的百姓没有被夜里的慌乱吓到,一个个指指点点着被绑在木桩上的贼人。二十来个活着的喽咯已经没有审问的价值,准备用来血祭死去的十九名百姓。南齐人在北唐人眼里是文弱,但从未缺少血性,对付这些臭名昭著的海盗用再激烈的手段也不会有哪个卫道士出来呱噪有伤天和。
此时听着各处的传回的报告,坐镇州府的谢维陷入了沉思,这次海盗袭城里里外外都透着古怪。按理来说,就算廉州城防备再松懈也不是这百来人就想攻破的,廉州城好歹也是几十万人的大城,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贼人淹死。海盗们的武器虽然杂乱,仔细一看就能辨别得出来是统一打造的,都是军方匠作的手笔,那些长弓都被伪装过,水军校尉已经认出来是北府弓手的制式装备。还有城内各处几乎是同时起火,绝对是有人给海盗们做了内应,而那几个打前哨的家伙也是奇怪,探哨踩点到南坊来说的过去,为什么一定要如此招摇地在知州府前暴露行踪呢?
“莫不是贼人想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跟在父亲身后的谢然想到了这个可能,不过他总觉得还有什么重要东西疏忽了。
“这几日也无甚贵重货物装船起运,也没有哪位大人物到廉州城来啊?”谢维也想到了这种可能,不过袁师爷的回答让他不知道海盗这么做的目标。
“二郎,你带上人手速去码头查看有无异常。”为了以防万一谢维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先遣黄杰去看看。
黎明将至大家都被睡意袭扰的时候,“报!!!”一个县衙的班头急匆匆跑了进来,“禀报大人,东城有海盗流窜,县令大人已将贼人围困在毛家大院,请都督大人指示。”
“持我令牌命武校尉率水军前去清剿,不得走脱一个贼人。”班头领命还没去了一会儿,州里的张捕头又跑了进来了。
“报!!!大人,孟判官在北街被袭,身受重伤,匪徒被兄弟们围堵在昌明坊内,请大人定夺。”听到张捕头的禀报,谢维瞬间反应想调兵去剿灭,却发现城里无兵可调了,只能调遣港口守备。海盗们这时才在四处袭扰,越来越让人奇怪了。
“袁师爷,你怎么看?”
“大人,此事必有蹊跷。”
“噗!”听到这么经典的对话,谢然不小心把刚刚喝进去的茶都喷了出来。
“然儿,有何不妥?”
“咳咳,茶太烫了,父亲大人,莫不是贼人袭城都是幌子,想掩饰什么,或者想调离了港口守卫力量,想把什么东西偷运出去?”谢然赶紧回答道,把刚刚的失态给糊弄过去。
“报!!!”这时随黄杰前去的府兵赶回来报信,“禀报大人,韩家商队的船只突然闯港,推官大人拦截不及已经,船队已经出港向北逃去了。”
“大人,船上必有此次贼人袭城的目的所在,请大人速速报以大都督府。”袁师爷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结果,谢维却没有推卸责任。
“袁师爷,速去清点州府伤亡损失,让合浦县报上斩获贼人的数目,天亮前拟出奏章报予朝廷。”
“是,大人。可是逃走了贼人之事……”
“此事休要再说,本督自会陈情上报,该要承担的自然要承担,别为了一时隐瞒他日给朝中政敌抓了把柄,攻诘二弟。”
袁师爷对朝中的事不精通也不好说什么,作揖告辞办事去了。
“父亲大人可是担心此事动摇二叔在朝中的地位?”
“然儿,朝中政局诡异,你二叔拜了副相,人望又高,为父也是封疆一方的大员,睦州大谢家在朝中更是根基深厚,已经引起了皇家不满。为父已经老了,该退还是要退的。”的确,作为南齐高门大族,谢氏这几年隐隐超过了马陈两家,一时间在朝堂势力大涨。如今这事谁也说不出会有什么结果,突如其来的海盗袭击,已经是百年未有的事了,此事必然会引发新一轮朝庭争论。
看见学徒园的牛四一脸焦急沮丧进来,谢然终于想起来学徒园的技术似乎也是值得有些人冒险的东西。等他赶到园子里,整个园子都成了废墟,作坊的工具大部分被毁了,酿酒的许虎和新学了肥皂技术的焦二被掳了去,学徒园里的少年伤了大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没死人。一地的海盗尸体,满是硝烟的作坊,一群默默站立的少年。
“大伙别难过自责,能留下这么多海盗你们已经尽力了,许虎和焦二我会设法营救,只要人活着,我们就可以重建作坊。”
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太平的外衣包裹着太多的残酷。要生存就会你死我活,谢然终究打破了自己安逸地窝在岭南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