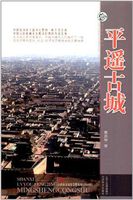长了尾巴和獠牙也未见得就多么可怕——譬如豺狼虎豹,若是被饿鬼杜虚见着了,也许他还会欣喜地发狂,一个个抓来剥了皮,生起火慢慢地烤。
但要是豺狼虎豹长了一双人的眼睛,那可就有些吓人了。
要是它长的不是爪子,而是五指修长的一双手;
要是再穿上一身人的衣服,直起身来学人一样走;
你明明知道它不是人;你怎么看它都是人;你不知道它瘙痒的时候是不是就露出一块儿斑斓的毛皮,或者一截儿尾巴。
任谁看见了,都不免要倒吸一口凉气。
“张知府说话,我怎么有些听不明白呢?”刘姑娘笑着端起茶杯来,轻轻地抿着。
“刘姑娘,你当然明白;你比我还要明白,明白的多了。”张知府笑了几声,“两个月前你跟我打赌,说智广和尚活不过六月十五,结果智广和尚先被高手偷袭,好容易保住性命、多熬了一个月,又被人在胸口上捅了一刀,果真就没活过六月十五。”他上身略向前倾了些,“刘姑娘还敢说自己听不明白?”
“张大人莫非怀疑,智广之死是我们太平商会下得手?”刘姑娘竟然仍带着笑,“那我岂不是自投罗网了?正好我们三人今日自己送上门来,知府大人拿下细细地审便是。”
“哈哈哈哈!”张知府大笑起来。
“智广怎么死的,镇安府没心情管,也管不了那么宽。”张福在一旁冷冷道,“只是大悲寺的圣旨确实是个要紧物件,太平商会终究不过是个商会,人多手杂,容易横生枝节,还是交给我们保管妥当些。”
刘姑娘连看都没看张福一眼。
“张大人,你我有约在先,若是智广和尚真的没活过六月十五,镇安府每年该贴补太平商会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不知道如今张大人是想反悔呢,还是愿赌服输呢?”
“我张某人说话向来一言九鼎,当然是愿赌服输!”张治平面不改色,“只是这一百二十万两银子恐怕太多了,想来大概是刘姑娘算错了账。”
“从大悲寺经过的私盐贩子不可计数,单单东海十二县的几户大头,每年偷漏的盐税少说也有八百万两;就算五五分成,镇安府也能分四百万两。按着前时的赌约,镇安府以后年年多得四百万两白银,我们太平商会就该从中抽三成,正是一百二十万两。”
“刘姑娘这账可就有些糊涂了。”张治平道,“我是占下了大悲寺不假;十二县的私盐头目也确实都来拜过了码头,这既无须瞒你,也瞒不过你。只是我占下大悲寺,大悲寺里的和尚不得镇安府养起来?寺周围住的刺头,不得镇安府找人看起来?更不要提私盐头目们听说大悲寺归了镇安府,暗地里又都去开辟别的道路,如此一来,说什么日后年年坐地分银四百万两,其实根本收不足数,反倒要我镇安府里凭空贴进不少去。更何况……”
张知府说到这里顿了顿,一股肃杀之气凭空而起。
“更何况,圣旨如今还不知落在谁人手里。朝廷本来就想尽了法子要削掉大悲寺的封地,若是派了天兵来问罪,大悲寺到时拿不出圣旨,什么四百两八百两,可就全做了镜花水月!”
刘姑娘噗嗤一声笑了。张治平也跟着笑了。厅上的肃杀之气顿时消解于无形。
“张大人是真豪杰,我一向信得过;既是张大人说收不足数,我便信了。圣旨自然是在我们太平商会手上,我也想快些把这块儿烫手的山芋丢出去,只是……”她眼睛里闪着光,“只是我也怕张大人日后又克扣咱们的银子,我们太平商会上上下下多少张嘴等着吃饭,饿上个把月便饿死了,我却也不敢冒这个险。”
“只是不知照着府上合计,镇安府在大悲寺一年究竟能有多少进项?”黄骞道。
“二百万两封顶。”张福道。
“如此说来,我们太平商会能得六十万两?”
“六十万两,不能再多。”张知府摸着下巴,似笑非笑。
“足矣,足矣!六十万两实在算不得小数目。”刘姑娘笑道。
“确实不是个小数目。”张治平仍然摸着下巴。
“一个月后,圣旨便送到府上。”刘姑娘道。
“圣旨一到,即刻便从府库里拨付六十万两白银给黄掌柜。”张福道。
刘姑娘站起身来,对着张治平一拱手,笑道:“张大人果然爽快!今日相谈甚欢,就此别过,告辞!”
黄骞和小五也赶紧都起身拱手。
张治平拱手回礼,道:“不送。”
张福送着三人出门去了。张治平仍然坐在椅子上。
等张福转回来,瞧见张治平还坐在椅子上,托着下巴愣神儿。
张福一向不爱说话,就站在旁边候着。
风吹得门外树枝摇曳,张治平忽然笑起来。
“张福,你看此事如何?”
“太平商会志不在小。”
“一年几百万两银子,就这么凭空送了我?我也是惊诧地很呐。”
“下多大饵,钓多大鱼。”
“你看这饵,是吃得,还是吃不得?”
张福不吭声。
“我倒要斗胆吃一吃。”张治平起身走到门口。眼前都是重重叠叠的高墙,只能越过墙头看见周围几座大山的山尖。。
“三江集上的眼线说,这几日四面八方的丐帮弟子都往三江集上聚,七月十五要大会群雄。”
“镇安府与丐帮,谁强?”
“丐帮山头林立,手足不睦,一击便溃。”
“与太平商会呢?”
张福沉吟了一会儿。
“太平商会根系庞杂,恐有高人;若能固守镇安府,倒也不怕他们暗算。”
“我听孙万全说,沈万又出山了。”
“七月十五,沈万似乎也要去三江集走一趟。”
“这个老狐狸……”张治平咕哝道。
张福的脸上一直没有表情。
“沈万向来见好就收,不是拼命斗狠的角色,掀不起大浪。”
头顶有鹰飞过。
一个月而已。张治平想。
穿过无数高墙,刘姑娘、黄骞和姜小五三人一路走回城中,早就有白马客栈的人接着。三人就这么默默地走回去。
白马客栈顶楼的雅间里早就备下一桌酒宴。
三个人都坐下吃起来。刘姑娘不说话,黄骞不说,姜小五虽然想说话,也强忍着不说。
忽然听见“喀”地一声,原来是刘姑娘手上用力大了些,一根筷子应声而折。
“镇安府月内必亡!”刘姑娘的嘴角轻轻向上扬起。
黄骞双手捧杯,神色凝重。
“大小姐今番东去,千难万险;黄骞每每念及此处,恨不能分身相随!”
他又对姜小五道:“姜老弟,大小姐的安危,就全仰仗你了!”
姜小五端起酒杯。刘姑娘也端起酒杯。三人相视,一饮而尽。
姜小五看见眼泪在黄骞的眼眶里打转。
刘姑娘拍拍手,叫进来一个杂役,换了双筷子。
“吃,吃了上路。”刘姑娘扬扬筷子,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