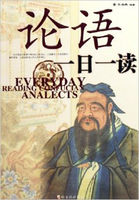根据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的解释,中西比较诗学的“影响研究”“是对已经完成的文化变迁的研究”,而所谓“平行研究”则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变迁的研究”,前者可谓中西诗学的历时静态“考古”,后者则着眼于中西诗学的共时动态“涵化”,而诗学涵化的生命力不在单向的移植,却取决于双向的熔铸和“综摄”(syncretism)。由于中西诗学因传统特异而呈异态展示,而传统的辐射性(effective history)又可以将其效力诉诸于中西诗学各自的“视野”(horizons)与“立场”(situation),因此双向的熔铸当移步换景,双方互为主体与客体,在深掘历史从而叩问传统的同时自由地挪用同质或异质文化资源,以求“视野的融汇”(fusion of horizons)和中西诗学的“综摄”。本文契合于中国诗学传统,旨在重建中国诗学本位话语,同时拟将挪用该传统中具有原创性质的基元命题“以少总多”说为同质文化资源,并以之印证西方诗学及其批评实践,为中西诗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提供一个可能的例证。
1“以少总多”说的基本内涵
中国文论“以少总多”说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始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积淀着中国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性智慧,却已走过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和诸多其它命题如“虚实相生”、“言象意道”等一样,“以少总多”说也具有原创性,它植根于中国具象思维的沃土,因诗性智慧的滋养而得以发展,随历史的递嬗终至进入中国文论基元系统规定着中国文论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文论诸范畴(如比兴、含蓄、繁简等)的精神内涵,为塑造中国文学的文化品格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少总多”说植根于远古,大成于《易经》,由刘勰正式提出,张扬之举泽被后世,奉为圭臬者代不乏人。该命题成熟很早,积淀下来已潜至诗性智慧的深层。它有丰满的理论肌质和深刻的思维深度,不啻是中国艺术创作规律的本质规定,无疑具有本体性质,同时又以具象为其特点,毋宁说就是“道”(本质、规律)与“器”(情貌、物象)的有机统一,只不过这个基元命题不以概念凸现,却以意象呈示,因此“以少总多”其本质就是“以象总象”或“以共象总殊象”,同时又以尚象、崇简、去累(庄子语)呈三维展示,每一个共象都是一个母题,其中包涵着中国诗学的具象式致思历程。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说:“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1】这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对诗人的艺术构思与艺术表达之间关系的论述,学术界也多将这一段文字视为刘勰文学创作论的精华。但也应该看到,所谓“以少总多”不啻是对语言表达能够穷理穷形之奥秘的揭示。这是一种艺术追求,也是语言表达面对众象纷呈所做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神思》篇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
【2】以言尽意之难,于此可见一斑。在刘勰看来,“物无隐貌”其前提是“枢机方通”,而枢机却受辞令管束,辞达枢机通畅则可使“物无隐貌”或曰“情貌无遗”,但是由于“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近乎无奈的窘境迫使历代文人自觉追求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尽的情貌,这就踏上了“以少总多”的知行旅程。正如欧阳建《言尽意论》所言:“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3】据此,言可尽,尽的是物貌情志,但关键是言要相接,名可辨物,相接则情志畅,辨物则名品殊;名殊的目的是要“辨其实”,即现代语义学所谓“切分现实”(segmentation of reality)【4】,使“言”走向“实”,使语言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而这条纽带就是“义理”,其本质就是现实世界经过名之切分转化而来的语义实体,是情志能够把握的现实个体,由此,“名”殊则“实”分、义别、理异,被切分的现实因之而异态纷呈,形成“多”的世界。当然“称名”务须“取类”,“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5】,但由于有限的语言表达与无穷的物象之间业已存在的深刻矛盾,“称名也小,取类也大”【6】,以小名欲取大类,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少总多”。
2“以少总多”说与中国文论
应该说,有限的语言表达与无穷的物象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是一个亘古弥新的困惑与苦恼,为了有所超越,《易经》成熟之前先有一段十分漫长的探索,充满着知行合一的艰辛。新石器时期“神农耕而作陶”因有陶器纹饰,经演化遂有几何文,以精纹状物;夏代“九鼎之备百物”,原始图腾初具象征雏形,常以纹饰摹道;殷周“错画成文”,卦象初立,“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而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7】;西周“五色成文”,“五色比象,昭其物也”【8】,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物一无文”,将“错画成文”的认识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与春秋时的“物相杂为文”一脉相承。这些探索与努力以具象为特点,是卦象得以确立的基础,而这种思维模式又为“以少总多”说在《易经》里的成熟开辟了道路,渗透于其中的又正是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诗性智慧。
《易经》始于殷周,成于战国或秦汉,自此以降,代有人出,历代文论家都对“以少总多”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无论理论评说还是批评实践都因循这种传统,当然也都是该命题的多维呈示抑或表象凸现,本身并没有质的改变。究其因由,这大概是因为《易经》弥纶天地,包容一切,具有极强的涵盖力,同时各个卦象“各指其所之”【9】,能够“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10】,具有很强的宇宙模式的建构力,论归纳做到了“曲成万物而不遗”,论演绎做到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这样一种宇宙代数学已经是中国式诗性智慧的本质规定,积淀下来已经潜存到了各门艺术创作的深层,物化为“洪范九畴”的基元命题,所以难有超越之举。不过详加考察也会看到异态纷呈,虽然历代文论家也许对这个命题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共同的表现就是总在“辞义”或“言旨”上面兜圈子,在下意识中受着这种艺术规律的支配,却并没有像刘勰那样见高识远,在中国文论奔涌不息的理论意绪中慧眼独具,只须“原道”“征圣”“宗经”,就拈出了“以少总多”这个理论命题,可见哲学胸襟和理论思维可以使人具有何等深刻的洞察力。
归纳起来,后世文论少有理论建树,却长于批评实践。涵泳于艺术的长河,文论家们多以只言片语总结创作规律,以点睛之笔在实践着“以少总多”的理论追求和艺术情怀。体系建构已大可不必,要紧的是艺术创作规律的本质规定。“以少总多”才能无所包而无所不包,因之艺术才有驰骋的天地,而这正是艺术得以生存的本质前提。
纵观历代文论及其批评实践,可以看出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国式的诗性智慧通过具象思维把“以少总多”说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使其服务于批评实践,而较少作纯抽象的玄思。据此而衍生出第二个特点,即是“以少总多”说作为艺术创作规律的本质规定在批评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呈二维展开:一是理论维度,以尚象、崇简、去累为理论枢纽,一以贯之,历代文论概莫能外;一是批评手法,凡比兴、隐喻、象征、隐秀、白描、用典等皆是这种规律的物化形态,历代文论家浸淫于其中,致思运思付诸于笔端,诗话词话蕴藉高标,均是“以少总多”的具象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