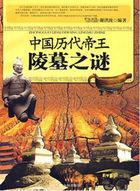【第23章】
巨蟒凌空
能让徐四郎再当一回新郎的宝物究竟如何,倒也不足外人道哉。
只说香胰坊的东家,新近晋升为承务郎的张庶,此时却是安奈不住心中的兴奋,唤来马车往正北的大宁坊行去。张家正宅虽不在此,但张庶却在坊中有一所偏宅,不过有心之人只看到张庶的马车进了宅院后就没再出来,却无人发现张庶进去之后不久,一道黑影便从院墙中飞身而出,一路飞檐走壁,直奔长乐坊而去。
半个时辰后,一身夜行打扮的张庶便立在了黄盛的书房之内。
“师尊,今日一共贩出药胰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二块,统共涉及人户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二户,这是刚制成的热点分布图。”
书房内,张庶一脸肃然的从背上取下了一根圆筒,从里面取出了一张长达两丈,宽一丈有余的巨幅地图,就在书房的地上摊开,只见图上绘制的就是长安城的详细地形图,将长安城市大小一百零八的坊市以及坊内的房舍全都描绘在内,并且以朱砂小点将长安东南、西南和正南四十余个坊市做了标记,这些标记有大有小,其中分店所在处画上的标记是一个小方块,其他地方则以大中小三种圆点分列,编注上标明大标记代表的是五十人以上的大户人家,中等标记为二十人以上人家,小标记则为十人及以下人家。
看着图上的热点分布,几乎城南家境中等的人家和城北的大户都已经覆盖,反倒是西南、东南好些个坊市里只有大户,没有小户。这让黄盛看了眉头大皱,原本定价只要二十文就是针对贫家小户,怕这些人舍不得出钱购买,却不想即便只要二十文,穷人也还是掏不起,算起来小半斗米也够几口之家吃上好些天了。
举灯看图的黄盛略略思索后,沉声问道:“广灵,前几日派去各坊药房善堂探听消息的人手可有回报?”
“尚无!”张庶也看出了黄盛脸上的凝重,知道这位师尊在想些什么,便劝慰道:“师尊,时疫实乃天数,非人力可逆……”
“呵呵!广灵倒是看破了天意?”黄盛开口一笑,他的两颗下门牙半截已出,说话倒是不漏风了:“妄救一人便是逆天,妄救千百人也还是逆天,这天不可逆呼?”
“弟子受教!”张庶被说得面上一红,急忙作揖下拜。他刚才的意思是说这瘟疫真要爆发也是天意注定,天意是不可逆转的。倒是黄盛点醒了他,真要是天意不可逆转,那他救一人和救千百人也是一样逆了天,倒不如敞开了心怀多救几个。
黄盛也没管他心中所想,将灯火放回后让张庶收好地图,便道:“叫子俊带上几个人,每夜一个坊市,每个坊市选五十家贫户,以游侠儿的身份去发药胰。”
张庶听了,却有些不解道:“这……师尊,今日才是分店开业的第一日,何须如此急切?”
黄盛却是笑道:“真要是贫家穷户,你便是开上一百日他也舍不得买,倒是为师疏忽,不成想这二十文钱值得小半斗米,对贫家而言可是些许日子的口粮。”
“师尊!”张庶听了黄盛这番肺腑之言,不由眼圈一热,再次诚心拜倒在地。这些日子他做惯了白玉香胰日进斗金的买卖,也时常受邀去皇宫里跟李漼这个败家皇帝花天酒地,虽然黄盛将药胰只卖二十文帮贫济困的事情他也支持,却也真没把二十文钱放在心上,眼下却听黄盛竟然自责将价钱定得太高,叫他如何不感动、如何不惭愧?
“广灵快快起来,天寒地凉,无事切莫赖在地上。”黄盛瞧着张庶做派,心中暗自得色,方才的话是他刻意所说,不愁不将张庶感动得一塌糊涂。要说黄盛顾念穷人倒也是真心,毕竟白玉香胰虽是宝货,却也做不了万年的长久生意,所以黄盛将药胰和去污皂低价出售,不外就是为了博取一个帮贫济困的好名声。
胰子这东西,用得再慢一个三口之家每月至少也得用上一块,大户人家一旦养成了净手洁面的习惯,销量更是惊人,对于肥皂香皂这样的日用消耗品,做的还得是薄利多销的长线路子,以量取胜方才是持久之道。
“对了,这长安城中的医者,可有什么行会?”黄盛随口问道,适才听张庶介绍今日开卖的情况,提到了许多分店的头名顾客,多是当地药店医馆的坐堂大夫。
张庶听了一楞,摇头道:“广灵不得而知,或许明日派人打探一番?”
“有便最好,可联系一下将各坊医者请来一聚,让他们评判一下药效!”药胰想要推广,自然少不了老专家,记得后世但凡午夜之后,电视里全是老专家卖假药的广告,制假者既然舍得花钱打广告,可见效果还是大大地有。
又交代了张庶一些经营策略和应对方法后,便要张庶回去。
送走了张庶,黄盛却又返回书桌前,摆弄起了一堆削好的篾片竹骨。看着这堆东西黄盛却是不由苦笑起来,眼前便又浮现出了一个小人儿的身影,倒不是别人,正是李保的魔星妹妹李妹娘。
虽然到现在都还不知李保究竟是哪家郡王的公子,但他家中势大是真,这李妹娘自打那日被黄盛画了八字胡后,便跟他杠上了,现在每日都跟着李保来书院上学,而蒙师董廷竟也没拿她当外人,每日《周礼》的课业一件不落的也给小姑娘布置,而这小魔星竟也能跟得上。
只不过,这会子她也不拿手指来戳人了,而是拿的秃笔。之前倒是蘸了墨,让董廷呵斥了一次之后便用秃头来戳,搞得黄盛苦不堪言,只得想法还击。反正现在黄盛已经搞清楚,在课堂上只要不弄得她哭闹,随便怎么来董廷都会视而不见。甚至闹起火的黄盛还咬牙让寿伯给他弄了根真的猴皮筋来,只要小姑娘敢戳他,他就转身用猴皮筋弹之。
这猴皮筋,倒也真是居家旅行,身边常备的上善之物。
这两日南风天,午后习艺时黄盛这等孩子不用练什么拳脚功夫、御射之术,李保便拿来了几只风筝玩耍。小姑娘淘气,总是嘲笑黄盛买不起风筝,头两天黄盛倒是不屑理她,可当他打听到李保的这几只样式老土,花纹难看的风筝竟然每只都在一贯多钱的价位,到叫他真个惊讶了。
唐朝的风筝并不都是纸做的,李保拿出的风筝都是用上好的丝绢作为面儿,并且也得知这风筝分为带响的和不带响。响便是响声,大型风筝可以托起能够发出响声的竹哨,而不能挂竹哨的小风筝则不能叫风筝,只能叫鸢,又分纸鸢、皮鸢和绢鸢。李保拿来的这种翼展足有一丈多长的巨型蝴蝶风筝要价一贯来钱倒也真不贵,光是上面铺着的两层上等丝绢就能值上好几百文了。
昨天风和日丽,李保又拿风筝来放,鬼使神差的拿了一个给黄盛玩,而黄盛也鬼使神差的接过来放,却不想风筝刚放上天,李妹娘这小魔星上来夺,一不小心绞断了线,当即满地打滚的要黄盛赔。这北风呼啸,不一会就将风筝刮得没了影子,便是想拣也拣不回来了。
什么是讹人?这就是讹人!
有道是圣人曰: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碰上李妹娘这个灾星,黄盛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便答应赔她一个。回来之后心里一合计,花一贯钱去买一个,还不如自己做一个,虽然黄盛没去过风筝工厂打过工,却也玩过一段时间,对风筝只知甚详。眼下他准备了数百根的竹骨和篾片,就是要做一个此时还未出现的长蛇风筝来。
黄盛要做的长蛇非常简单,头部牵引直接是最简单的可折叠三角形大风筝,中间的骨节则用十字小风筝,只要在大风筝上画个蛇头就好。
不一会,黄盛修葺好篾片,露儿也把用来粘合的浆糊熬好,主仆两人一个扎骨架,一个裁纸粘糊,不过一个时辰就制出了四十个小风筝,随后黄盛又研了墨彩,将大蛇头和骨节身上的花纹画好,这才休息。
第二日去往书院前,黄盛特地让寿伯取了一个小箱子将风筝都装了起来,一早上无话,小魔星今日似乎也忘记了和黄盛的约定一般,只顾埋头功课的样子。到了午间,黄盛便要李保叫来了两个壮硕的伴当,便从箱子里取出了风筝来。
看着黄盛先拿出的是一个画了硕大墨色蛇头的三角风筝,李保倒是有些诧异,而李妹娘却是嘟着个嘴大呼不好看,不如她丢的蝴蝶风筝。黄盛也不理她,将三角风筝装好后,取了粗线放飞上天,然后便让两个伴当拿着线头,开始在线上加挂骨节。
此时长安,北来暖风正盛,大风筝受力升劲极大,只见黄盛一个个将骨节挂上之后,很快一条巨蛇便蜿蜒浮空,只不过四十节便显出了磅礴气派。李保和李妹娘看得目瞪口呆不说,整个长安书院的人都被惊动了,就连董廷董老夫子抬头看着天上宛若蛟龙一般随风摆动的长蛇风筝,也快要被惊得脑中充血。
“这……这……”久未谋面的吴侍讲也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奔了出来,指着天上的长蛇风筝说不出话来,还是一个跟在他身后,下巴光滑无须,样貌有些阴柔的中年人扬声道:“快快!快将这什物收下来,你这小郎想作死么?”
听这中年人的嗓音,既不粗也不细,黄盛倒也没能分辨,不过李保的两个伴当却是醒过神来,急忙收线将风筝收了下来。回头再看时,只见吴侍讲已经和中年人吵做一团,两人语速太快已经听不清说些什么,直到中年人将头一扭伸手指着黄盛喝道:“速来人,将这小郎绑了。”
“尔敢!”吴侍讲面红耳赤的跳将出来,三两步就拦在黄盛身前,昂声道:“此乃长安书院,谁敢绑人?”
中年人却是痛心疾首的扬声道:“吴师、吴大侍讲,今日若不绑了这小郎入宫请罪,只怕这一院学子俱都危矣!”
黄盛一听这话头立时便大了,再看那长蛇风筝,不禁悔之晚矣!
####
蛇乃何物?
龙种是也!
你一个小屁孩要是在深山老林里别说放风筝,就是穿黄袍玩皇帝游戏也是没人会管,可要是你在长安城里放这种风筝,不管几岁都是欺君僭越的罪,弄不好就得满门抄斩祸延全家,甚至还有可能株连九族。
虽然唐朝的忌讳比起爱搞**的满清要少上许多,但在长安城中,在百余年前李隆基宠爱杨贵妃搞得大唐险些灭国的兴庆宫旧址中放飞这寓意了蛇蟒蛟龙的风筝,岂不是自寻死路?
黄盛几乎是在那名长相阴柔的中年人喊出了要绑他入宫请罪的话后,便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窍。记得前不久还听说有个入了翰林院的进士状元因为在奏章中没有将皇帝名讳中的漼字别写而被判了个三千里流放岭南,现如今自己放的这个风筝真要无限度的上纲上线,只怕套上一个想要谋反的罪名也不为过啊!
怎么办?
装傻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可真要是审问起来,问起风筝是何人所制,自己如何对答?说是自己想出来的?谁信啊?
也就在黄盛闷头急思对策、吴侍讲与那中年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情况却又有了变化,一直在旁观望的李保一手拉着李妹娘奔了过来,直让两个伴当收好风筝,一手又扯了黄盛便往书院大门奔去。
黄盛糊里糊涂被拉着奔出好远之后,才发现吴侍讲等人还在原地争执并未追上,可细看之后却发现不光是吴侍讲等人,就是其他围观的人也好似对他和李保、李妹娘视而不见的样子,直到出了书院大门上了李保的马车后,才听见李保向车夫道了一声:“快!快回宫!”
跟着马车的车帘一动,两个伴当将装风筝的箱子放了上来,李保也忙向两人到:“你二人也跟在后面,随我回宫!”
车身一动,马车便疾驰起来,见黄盛呆呆的模样,李保竟还知道出言相慰道:“黄郎莫慌,万事有九郎担待。”
黄盛看李保满头大汗表情急切的样子,倒也真为他的处事气度所折服,就从他刚才交代的“入宫”两字,黄盛就知道自己之前对他身份的猜测走了眼。要知道即便是郡王之子,也是没有资格想入宫就入宫的,而他第一时间就能想到拉着黄盛带着风筝入宫,便说明他极有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李漼的儿子。
李漼现在三十几岁,有个十余岁的儿子倒也平常,不过黄盛对李保带他入宫的用意反倒有些忐忑,便只能出言相问道:“九郎,可是三郎做的纸鸢不好么?”
“好!”李妹娘可不懂得什么叫僭越,却是拿手来摸黄盛的脑袋道:“赖哭郎做的纸鸢可好了,妹娘也是第一次见哩。”
李保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也是苦笑道:“黄郎,这纸鸢可是你制的?”
“是啊!”黄盛可不敢诬成他人,便道:“三郎昨日回家,便央寿伯去卖个纸鸢做赔,寿伯去问了却要一贯钱。便回来给三郎用竹扎了一个,三郎怕妹娘嫌弃不好,便学着样儿让露儿帮着又做了好些个,就想着若是串起来放,肯定有趣。”
“哦!”李保倒是知道黄盛的管家叫寿伯,使唤丫头叫做露儿,倒也不以为意,想了想后又问:“大纸鸢上的蛇头和小纸鸢上的花纹,可是黄郎画的?”
“嗯!”黄盛点点头,这事他可不能再托成别人。
见黄盛应承下来,李保也是满脸凝重的沉思起来,倒是李妹娘没心没肺见李保不言语后便起身去翻箱子里的风筝,唧唧歪歪的闹着黄盛也教她制作。
眼下这事,黄盛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见李保主动将事情揽下,便也只能静观其变。
不过小半刻时辰,马车便从通衢大道直奔皇城,不过却是没入正宫太极宫,而是从小侧门入了东宫。进宫时黄盛仔细留意了一下,只见宫禁守卫根本就没拦车,而驾车的车夫只是掏出一块看似腰牌的东西亮了一下,便驱车直入。
马车在宫里转了几个弯后,便在一座看上去格局不算很大的殿宇前停了下来,李保则再次一手拉了黄盛,一手拉了妹娘下车,便往殿宇一侧行去,在殿宇回廊中疾走时,黄盛看得真切,沿途所遇见的太监宫女见了李保都自行礼侧让,还有宫女更是低呼小公主回来了,没想到这李妹娘竟还是公主。
直奔了怕有数百步的样子,绕过两道回廊和一座方殿,这才来到了格局看似与黄盛家无甚区别的环形院落,李保拉着黄盛、妹娘直接走进南房,掀开门上的布帘便唤道:“阿母,九郎回来了。”
进了房门,黄盛这才看清屋中陈设与自己家中别无不同,一个年岁比四娘小不了多少的少妇安坐在屋北的一张大胡床上,正手握毫笔作画,见了李保、妹娘便展颜露出了一个和蔼笑容,又扭头看看窗外,不由奇道:“九郎今日回来的怎地这般早……这又是?”
李保放了妹娘的手,拉着黄盛上前介绍道:“阿母,这便是九郎与你提起过的黄郎,单名唤作一个盛字,家中行三。黄郎,快来见过阿母。”
“哦!”黄盛急忙伏地行了一个顿首的大礼,却又抬头向李保装傻道:“九郎,适才听说这里是皇宫哎!你家阿母是娘娘么?”
“呵呵!好伶俐的小娃娃!”李保的母亲闻言却是笑了起来,招手让黄盛起来后笑道:“小黄郎倒也知道礼数,不过宫中规矩到多,你便唤我做徐贵人吧。”
黄盛脸上不露声色,跟着唤了一声徐贵人,可心中却是明白,这李保的母亲铁定不是正宫娘娘,也不是受宠的嫔妃,只不过因为生了李保才母凭子贵,所以要是让黄盛喊她娘娘,只怕又会惹出什么是非来。
不过这徐贵人倒是有些平易近人,将身前作画的矮几推开后便拉了黄盛来亲热,还抚过脑袋来看黄盛的左眼,直到看清黄盛无恙后这才放心下来,从矮几上的果盘中摸过几粒干桂圆给黄盛食用。
这期间一直没说话的李保直待徐贵人看完了黄盛,这才上前附在徐贵人耳边说起了悄悄话,说了没几句后徐贵人本是平常和蔼的脸色就骤然变了,低声喝道:“九郎,此话当真?”
“句句属实!”李保脸上却全不见孩童的模样,一脸的严肃。
徐贵人想了想,又拿目光来看正装傻和妹娘争着吃干桂圆的黄盛,见黄盛完全一副小儿做派和妹娘嬉闹,这才放下心来:“速将那纸鸢拿来给阿母瞧瞧。”
李保点头,转身出门。
这期间黄盛心中骇然之余,只能尽量的模仿小孩儿举动,而妹娘倒也配合,见黄盛剥吃干桂圆便伸手来夺,黄盛假装与她嬉闹,却又将剥了壳的桂圆喂她,倒叫小魔星很是开心。
李保去了没多久,便领着两个伴当将装风筝的箱子抬来,徐贵人看了箱中的风筝后,又拿眼来看黄盛,却是突然将她原本在画的花鸟图抽掉,铺上了一张白纸后对黄盛道:“小黄郎,我家九郎说你会画画儿,可否画上一张?”
“好!倒不知要画何物?”黄盛又喂了一颗桂圆给妹娘后,便乖巧来行至矮几前,一脸懵懂的问。
徐贵人面上表情自然,将研好的彩墨摆了过来:“画甚都行,你最拿手的是何物便画何物。”
“我会画大蛇!”黄盛装作得意的样子,刷刷几笔就将风筝上的蛇头在纸上勾勒出来。
徐贵人看了黄盛画出的大蛇也很是惊讶,细细一看便能看出这画像上的蛇头与风筝上的蛇头如出一辙,便奇道:“小黄郎,这大蛇是何人教你画的?”
黄盛道:“娘亲常带三郎去菩提寺,三郎不怕大蛇,寺里的墙上便有这大蛇。”
这话是黄盛故意说得颠倒,自然教徐贵人去了戒心,她又想了一想之后,却拿过笔在风筝上添了好些颜色,只看她也是寥寥几笔便在蛇头上添上了犄角和龙须,却把原来的蛇眼位置用浅色的颜料遮盖,然后又拉过李保附耳如此这般的说道,这才道:“九郎,你父皇此时该在大明宫饮宴,你便照娘的吩咐办了。嗯!小黄郎和妹娘你也带去,你父皇要是开心,别忘了替小黄郎也讨个赏赐。”
“九郎记下了!”李保说完忙让伴当将风筝和桌上的一碟朱砂毛笔拿走,再次拉上黄盛和妹娘出门,坐了马车便往大明宫去。
黄盛虽然没听到他娘俩如何咬耳朵,却也被这徐贵人的心思所折服,她在风筝上如此改动,又把眼睛位置空出,所想的办法不外就是让李保拿风筝去献宝,又让李漼拿朱砂点睛,到也真是一个化险为夷、连消带打的好计策。
看来,李保身上所显出的老练世故,也多是这徐贵人的教导之功。
车行没多久便入了大明宫,果然李漼这糊涂皇帝又在太液池畔饮宴,而李保也如黄盛猜测的那样,拿着风筝前去找李漼献宝。又叫李漼在风筝上用朱砂点睛,当改头换面的龙形风筝借着湿暖的北风所带来的升力摇摇摆摆蜿蜒腾空时,一个穿着二品服色的官员却是跌跌撞撞的狂奔而来,当即有人高呼道:“路相,何故如此惊慌?”
这人也没抬头看天,却是直接拜倒李漼足下,手指长安市里方向,慌慌张张的急道:“天家,臣方才从市中来,听闻传言这长安城中有巨蟒凌空,怕是妖物现身,要为祸人间哇!”
哪知李漼却是哈哈大笑道:“何来巨蟒?这本是苍龙!路卿,你且抬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