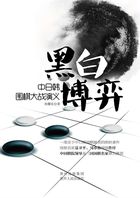王海夷边说边伸手,打算把画和照片取下来,魏小天一看,赶紧上前搭手帮忙。他一边往下取,一边觍着笑说:“老师,这下我是全懂了,你要是不生气呀,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说我怎么一见这颗佛头就起那么大反应?是不是我的艺术敏感性太强了?”
“那是因为你愚昧。”王海夷冷冷地说,“你愚昧,你的情绪才会和佛头共鸣。就像看别人跳大神,凭什么你也感到害怕,因为你也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鬼。
“啊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魏小天自知今天做足了白痴,干脆自我解嘲寻一个台阶下。
“现在我跟你说这佛头,它就和迷信、巫咒、怪力乱神这些玩意儿在一个层面上,不可能出自大家之手。”话题绕了一大圈后,王海夷终于说到佛头正题上了。
“老师,那它出自什么人之手呢?”魏小天问。
“应该是西山画派的东西。”王海夷说。
“西山画派?”魏小天印象中就没有这样一个画派,他脱口问道,“哪个国家啊?”
“咱们市里的西山,知不知道?”
“这我知道。”
“明末清初,西山里边有一帮画匠,人数比较多,画的风格也差不多,就叫出这么个名儿来。不过他们的画整体质量不高,技法也很粗糙,更没出过大师。”
“怎么我从没听说过这个画派。”魏小天说。
“他们的画是用来烧给死人的,算是冥画的一种,所以画了之后就烧了,流传的不多。再说解放以后,这种画也没有市场了,大约早就失传了。”
“死人画?”魏小天又不懂了。
“家里死了人,请个画匠来画几张烧火画儿,祭奠的时候烧了。咱们这地方的老风俗,现在不兴了。”
“哦,”魏小天这下明白了,他突然又想起一节,“不对呀,老师,画派是画画的,佛头可是雕塑。”
“佛头形象构造,肯定出自西山画派之手。”王海夷这样断言,他的理由确也充分,“首先,西山画派的烧火画儿从来只画三样东西,就是天上的佛、世间的人和地狱的鬼。其次,就我了解的情况看,过去的民间画派当中,只有一个西山画派明确提出过‘画佛像鬼,画人像鬼,画鬼还是鬼’的主张。像两只眼睛一哭一笑的手法,这都是西山画派的看家技法。再者说,佛头刚好就在西山下面挖出来,不是西山画派造作的,还能是谁?”
“天哪,居然还有画派主张要画得像鬼的,太不可思议了。”魏小天惊讶不已。
“烧火画儿的特殊处就在于,理论上它是烧给阴间的,烧给死人看,烧给小鬼看的,既然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它的审美当然要按照鬼的想法来设计。”
魏小天看王海夷一张脸定得平平正正说这话,不觉身上打了个寒战,他不愿再纠缠这个问题,悻悻问道:“哎,老师,你说西山画派可能失传了,那我该上哪儿去找西山画派的线索呢?”
王海夷见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就把铺开的照片一张一张拾起来,递回魏小天手里,最后撂下一句话:“去七里桥古玩市场看看吧,没准那条街上有懂行的人。
魏小天在王海夷那儿受了一回教,感觉收获太大,转过来就想在萧郡面前显一手,因此特地把一段访师经历讲得跟个《隆中对》一样。另外,他也是想说动萧郡,好跟他一起去七里桥古玩市场寻访寻访。
萧郡听他讲完了,眼皮抬都没抬,冷冷地问:“你还打算跟佛头这事吗?”
“是啊,一起吧。”魏小天一脸的兴奋。
“哥,不一起了,你去吧,等你把佛头身世搞清了后,写一篇论文发到你们美院学报上。”
“哟,看不起咋地啊,我告诉你,我这事要弄成了,那就开创了新闻调查的一个新门类,它叫艺术调查。”魏小天挥手说道。
“哥,你开创吧,我专业不对口,你知道我大学里学的金融。”萧郡说完,起身就走了。
五
从南二环中段下道,路边有一座四柱三间的冲天石牌坊,穿过牌坊,一条老旧胡同顺着这一片居民区中间七弯八绕延伸出去,这便是七里桥古玩市场。
魏小天才过牌坊楼,站在石阶上打眼一望,见是错错落落的老店旧楼、镶边带色的店招旗幡,只觉得一下回到了清朝一般。
这胡同是一条步行道,道两边有门有户的店面,大多挂了仿古的匾牌,这些店家做的是坐地生意,店里都有正经玩意儿。
各家店门前的道牙上,一家挤一家全是练地摊的文物小贩,有的还铺一块红布,摆了铜钱、破镜、烟斗、镯环之类,有的面前就斗大一方石头,或是半人高一架家具,一看就是做完一回买卖,再见不上二回的主。
魏小天见着路边的店主,先问人家识不识得他照片上的佛头。这条街上的人到底是行家,个个只把照片拿到亮眼处瞧上几眼,给出来的结论竞都合了文研所的鉴定,俱是说这佛头算不上什么古玩,给不起价钱。可是魏小天想跟他们讨教佛头的身世,又发现没几个人能说出子丑寅卯来。
嗣后魏小天改了口,一路径直打听哪里有收藏西山画派作品的。经这么一问,他才发现,即便在文物高手扎堆的七里桥,也极少人听说西山画派。
这样且走且问,眼看一条胡同就快要到尽头,魏小天还没找到一丝半毫的线索,不禁心生几分失望情绪,愁着往下还能往哪个方向去呢。
这时候,前方胡同口一株古树下,竞有个孤零零的路边摊,支着一张大方桌。魏小天正无趣,遂凑到桌摊跟前去。摊主看样子在古稀之年,一副单薄的身子,靠墙坐在一张低椅凳上,只一双眼睛刚刚冒过桌摊。他大约乏得慌,小眼睛眯一阵睁一阵的。
魏小天随手拿起一面铜镜看了看,然后又捏起一块银圆吹一口,放在耳边上听响声。
“大爷,您这是假的吧。”魏小天连吹了几口,问怎么听不见银圆有响声。
老人打了一个激灵,以为生意来了,坐定后,见面前牛高马大的小伙子问他这话,就一句话不说,气呼呼地把头拧向一边,嘬着嘴又继续眯他的瞌睡。
魏小天觉得老人家煞是可爱,自己也不生气,待把银圆放回桌摊,又拿起一个鼻烟壶把玩起来,随口问了一句:“大爷啊,听说过西山画派吗?”
这回老人的瞌睡怕是被魏小天扰到了,他干脆把身子也拧到脸那个方向去,眼睛依旧不往开了睁,嘴里却嘟囔些碎话。
老人自言自语一般,说的是本地土话,语速又快,吐字也不清,魏小天偶尔听得他话里面有“西山,西山”的词冒出来,就停下手里的动作,静心听他到底在说什么。
魏小天才听了个大概,就来了兴头。原来老人家话锋里尽是对魏小天的不屑,他说自己就是西山画派的传人,咋能不知道西山画派呢。
“大爷,您是西山画派的传人?”魏小天简直不敢相信。
“咋了,”老人家到这会儿清醒了,回过身来,仰头望着魏小天问,“你找西山画派干么子?”
魏小天在七里桥找了大半天都无收获,这回就像遇见真神一样,赶紧绕过桌摊,到老人家面前蹲下来,随手递上自己的名片,忙不迭地说:“可算是找着您老了。
老人右手接过名片,左手抖抖索索从桌腿上挂着的一只提包里摸出老花镜来戴上,费劲地把名片瞧了好一阵,才瞧出来魏小天是记者,即刻坐端了身子,重复问他一句:“你找西山画派干么子?”
“大爷,您真是西山画派的传人,不是说西山画派失传了吗?”刚才魏小天等老人看名片的当口,想起王海夷跟他说的话来。
“哪个说失传了,那我算啥子呢?”老人取下眼镜,把眼镜和名片一起塞回提包里。
老人名叫许福生,跟魏小天说,他家就在西山里面。他一边伸手把桌面上的物件翻得叮叮作响,一边给自己打个圆场,说他在七里桥练摊,玩的都是老一辈画匠混饭吃的江湖手段,所以桌摊上这些物件,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古玩,他为啥摆在这里呢,为的又是去蒙那些上七里桥的贪婪小人。
魏小天知他这话是冲着自己记者身份来的,不禁暗自诧异,这把年岁的市井老人,是如何明白记者跟他这门营生之间的关系的。
他看许老所说的诸多情节和王海夷交代的不差,便不再接话茬,赶紧把照片拿出来让他看。
许福生只扫了一眼佛头照片,就一口断定,它是出自西山画派之手。
原来,许福生的父亲、爷爷两辈人,都是西山的画匠。过去,三教九流当中,西山画匠的正业,是替人做白事道场画烧火画儿。许福生在旧社会成天跟着父亲跑白事道场,那时候他只有十多岁,父亲画烧火画儿,他就在旁边帮忙抻纸磨颜料,烧火画儿上的一笔一画都烙进脑子里,现在拿到魏小天的佛头照片,自然一眼能辨出来。
“这东西晦气,你拿着它干啥?”其实许福生算是七里桥的老油子,他最是掂得来记者的行当是专戳他们痛处的,所以自打看了名片后,他冲魏小天说的话,也都本分了。
“老先生,那你现在还画吗?”魏小天仍操心西山画派的事。
“不画啦,早不画啦,没人画啦。现在,现在啥世道,人死了火葬,烧的是纸汽车、纸飞机、纸二奶,连烧的纸钱都是美国票子,谁还烧我们画的那些东西呀。”许福生说到这儿,随口又问一句,“听说现在都烧开纸黄金了,我还没见过呢。”
魏小天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老先生,纸黄金可不是给死人烧的,那是一种理财产品,你可以拿钱买的,买来后能钱生钱。”
许福生不大能明了魏小天的话,仍按着自己的理解应了句:“我有钱了买粮买酒,买那纸黄金干么子。”
许福生在七里桥摆摊,仗的是街上有他一门表亲。表亲家为人宽厚,允许他的桌摊依着院墙摆放,平时收摊后,在后院还留给他一间房,供他存放桌椅板凳和零杂货物,更铺了床铺,方便他住宿。
这天,魏小天和许福生在桌摊前聊得久了,不觉已到下午吃饭时间。许福生赶着要收摊,魏小天却还在兴头上,他就索性帮许老把桌摊收进表亲家的院子,然后邀约一起去胡同外面的饭馆吃饭。
许福生是那种喝一口酒下去,就像鱼从旱坡弹进河里的老头子,全身都活泛开来。这回遇上当记者的请他,又是几十元一瓶的好酒,也就放开喝上了。
才几杯酒下月土,兴头一蹿上来,许福生不自觉地又要在年轻人面前显他混江湖那一套做派。
“小兄弟。”他干过一杯后,这么叫了魏小天一声,直窘得魏小天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连声说:“不敢不敢,许老,您这是折我的寿,您叫我小魏就好啊。”
“小魏兄弟,你和这烧火画儿有什么关系呢。”许福生有些醉意,拗着和魏小天称兄道弟。
“啊,这不是烧火画儿啊,”魏小天才意识到,聊了大半天,许老还当这张照片是一幅画,连忙解释,“这是照片,是佛头的照片。”
“哦?”许福生打个激灵,赶紧把照片要过去仔细看了看,这才看出是一张照片。他倒也老练,随即一拍桌子,拖长了声音说,“不对——呀。”
“啥不对,老先生。”魏小天被许福生阴阳怪气的声音吓了一跳。
“我西山画派都是些画匠,不雕东西的呀。”
听许福生这么说,魏小天便把他从王海夷那儿讨教来的学问重又卖了一遍:“王老师的意思是说,这佛头造像肯定是西山画派的人弄出来的。”
许福生听说美院的教授还知道西山画派,面情上一阵激动,一下自裁了三杯。然后他定了定神,郑重其事地问魏小天:“这么说,你是冲着佛头来的,不是冲着烧火画儿?”
“嗯。
“呵呵,”许福生又自裁一杯,抹了抹嘴,才说,“小兄弟,今天你这酒我可一点儿不白喝,不瞒你说,我有一个大哥,那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偏偏就你这样式的佛头,以前好似听他说过一回两回,不知你愿不愿意随我前往一见呢。
魏小天连忙问,你大哥现在何处?
许福生不言语,拿筷子蘸了蘸酒,伸到魏小天面前的桌上,颤颤巍巍写下几个字。魏小天费劲瞧了半天,方才瞧出来,是“西山古镇”四字。
六
西山古镇是西山里面一座老镇子。去往镇子只有一条通乡公路,这条路沿青龙江蜿蜒北上,一路要过山涧峡谷,更少不了盘山回环,客车一程跑下来,少说也得两个多时辰。
挨到第二天下午,许福生收了摊,魏小天便和他一起去汽车站赶了最晚一班车。一路无话,当天抵达古镇时,天已近黑,古镇的街道、人家全都上了灯。
古镇悬在河畔的石壁山上,靠河一排全是吊脚楼子。现在是夏天,魏小天还在河对面,就看见家家大开着窗户,屋顶吊扇旋得电灯光闪闪烁烁。
河是青龙江的一条小支流,过水不大,魏小天搀着许福生涉水过了河中间的桥石,又沿着石壁上凿出来的梯坎上行,几步就到了古镇街道上。
站在街口往里一看,魏小天才发现,背山一面还有房子,夹在中间的街道只剩不足两米宽。街道上并没有立杆的路灯,隔不远会有一家人在房檐下吊出一盏白炽灯来,光线虽昏暗,蚊虫却在灯光下飞舞得欢,看上去别有一番生机。
许福生和街上人家大多认得,每过一处家门,总有人从里面朝他喊叫。那招呼是冲他打的,各人眼睛却都盯着他身后又高又胖的魏小天看。
许福生堆着一脸的笑,逢招呼必回一句,回来了,回来了,从城里回来,带一位记者上来采访采访呢。
这样走走停停,直到望见一家门外挂一小串若明若暗的彩灯的房子,许福生才指给魏小天说:“看到没有,那一家就是我大哥家了,咦,看来今天有生意呀,彩灯都亮着呢。”
许福生和他大哥是结拜弟兄,大哥名叫郑明星,只比他大几个月份,在古镇上开了这家“明星书场”,专靠说书卖盖碗茶为生。
今天堂屋里果然坐了几桌客人,只因屋内开间窄狭的原因,打门口看进去竟是黑压压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