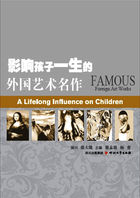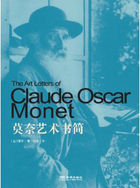斯坦尼以前的学生泽德尼基在美国为他们积极地奔走帮忙,他觉得莫斯科艺术剧院演的是以群戏为特色的剧目,62人的剧团演员竟还嫌不够多,还要在当地找来一些俄罗斯演员,扮演更多的群众角色,以便使台上的群众场面气氛更加真实。到了四月份,他甚至还换下了劳累过度的老师斯坦尼,上场替他扮演《底层》里的角色,而票房并未受到影响②———这样的事在完全以主角一个人的魅力征服观众的梅兰芳剧团里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斯坦尼在美国寻访的城市和演出场次都要多于梅兰芳剧团,可他作为一个演员并没有像梅兰芳访美那样引起社会上那么大的轰动;然而,他的演剧方法却在美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了。斯坦尼剧团才演了十天以后,制作人杰斯特就为会讲英语的泽德尼基安排了一系列的讲座,介绍他的老师斯坦尼发明的新的表演方法,这也是他促销戏票的一个有效手段。在讲座中泽德尼基甚至夸口说,要在斯坦尼指导下为十个百老汇的资深演员上课和排戏。这件事虽然当时没有马上实现,但不久就变得更大了。不但有好几家俄罗斯学派的表演学校在美国诞生,而且逐渐成为美国戏剧表演方法的主流。这要得益于比斯坦尼早去的泽德尼基和一些没有跟随斯坦尼返回莫斯科,而滞留在了美国的团员们。其中RichardBoleslasky和Maria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时,他们选择离开莫斯科艺术剧院,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剧团——美国实验院团。他们的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传播斯坦尼“方法派”主将的美国表演教学大师李·斯特拉斯堡和哈罗德·克勒门。
①Mel Gordon:Stanislavsky in America:an Actor’s Workbook,New York:Routledge,2010,P20.
② 同上,P20。
斯坦尼和他的剧院此行最重要的意义是,他们的方法引起了美国演员学习的兴趣。斯坦尼还在美国巡演时就接受了波士顿一个大出版社的邀约,开始写他的艺术自传《我的艺术生活》,详细解释他的表演体系的创造过程和具体特点。之后他带着剧院回国了,但有些演员留在了美国,再加上后来又有一些去美国定居的俄罗斯演员,成了向美国人传播斯坦尼方法的重要力量。这些俄国表演老师们远不如斯坦尼有名,他们去美国的时候都是想当演员的,但因为很难找到表演的工作,于是就开班讲课变成了老师,教出了一批美国的表演老师,再通过他们教出了一批后来非常有名的美国“方法派”演员,包括马龙·白兰度、玛丽莲·梦露等人。①
①Mel Gordon:Stanislavsky in America:an Actor’s Workbook.New York:Routledge,2010.
(三)两者的比较及其启示
斯剧团和梅剧团都访问了美国,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斯剧团是在美国经济相对最好的时候去的,而梅兰芳访美时大萧条已经开始,可以说运气很不好,但他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成为历史上在美国获得最大成功的非英语戏剧演员,这一点甚至超过了斯坦尼。但如果要问斯坦尼和梅兰芳各自在美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那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美国》一书的作者梅尔·戈登在序言中写道:“俄国的剧团和美国的经纪人当初都怎么也没有料到,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巡演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文化移植的源泉。不出一代人,它就催生出了一个新奇的俄美混血种———百老汇舞台上的现代表演以及它的挑战者———好莱坞电影———的新的表演风格。”①时至今日,八十年多过去了,回过头来反观一下美国这两种戏剧样式的现状,反差更加巨大无比。斯坦尼的表演体系不但留了下来,被美国人发展再利用,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的美国演剧体系,还拓展到了全世界,甚至常常被误认为是“美国表演风格”。而中国戏曲在美国却依然少有人知,就是听说过也只有极其表面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太深,戏曲的形式太过完备人家学不会偷不走吗?为什么在那里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叫好,然后只要“人一走,茶就凉,不思量”了呢?
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时期的戏曲和美国戏剧的差别实在太大。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戏剧刚从夸张的情节剧发展过来,正在摸索现实主义戏剧的路子。当时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导演兼制作人贝拉斯科就是美国早期现实主义戏剧的先行者,他的编导作品包括话剧《蝴蝶夫人》———普契尼同名歌剧的前身,还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后来作为话剧就淡出了舞台,几乎已经被所有的人忘却。美国最杰出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出身于戏剧世家,他的父亲老奥尼尔几乎一辈子都在商业剧团跑码头,主演从法国小说改编而来的最典型的情节剧《基度山恩仇记》,而奥尼尔自己就参与开创了严肃的现实主义的美国戏剧。奥尼尔在写探索戏剧的同时,开始写出了早期带有现实主义味道的作品《天边外》,但还没写出他最出色的现实主义巨著(《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等)。那时候还没有“外百老汇”剧院的概念,也没有现在遍布全国的非营利性地区剧院,严肃的戏剧家很不容易找到展示的舞台。斯坦尼访美的时候,美国的现实主义剧作正在逐渐完善中,表导演方面流行的还是斯坦尼在俄罗斯早就批评过的所谓“表现派”,演员们还没有找到由内到外展现人物真实内心的方法。“表现派”用来演《基度山恩仇记》那样大起大落的情节剧相当合适,但用来演《底层》这样接近自然主义的群像戏就显得粗疏和过火。斯坦尼要求的是每个人都注重细节真实的集体表演,所以美国戏剧家们一看到斯坦尼的表演方法如获至宝———斯坦尼是在他们想走还没有走成的新路上的引路者。此外,当时美国的电影业更是在向现实主义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从卓别林那样的夸张的无声电影过渡到注重细节的有声电影的低调表演,斯坦尼的表演风格特别适合好莱坞的需要。
①Me lGordon:Stanislavsky in America:an Actor’s Workbook.New York:Routledge,2010.
然而美国人看梅兰芳,应该说是惊为“天人”,完全是看一种异国情调的表演,虽然极其崇敬,但只能敬而远之。虽然梅兰芳在每次演出前也安排人用英语做了关于京剧的介绍,帮助观众了解剧情和京剧的风格特点;但毕竟没有像泽德尼基和其他斯门弟子一样,既做系列讲座,又做操作性的表演工作坊,来“传播”自己的表演方法。而且,即便梅兰芳和他的顾问们在当时也想到了这些传播手段,又有多少美国戏剧人会来学?就是来了,我们的戏曲艺术家又能教会多少人?回答不大会是乐观的。
究其原因,除了主流戏剧观不同以外,恐怕还必须承认,我们缺乏善于变通的跨文化戏曲革新家。应该说梅兰芳已经是戏曲界非常锐意进取的革新家,但他一生搞的是“移步不换形”的革新,毕竟只是为了在中国文化内部的京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最多偶尔向外国人展示一下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并没有想到要去影响世界,更不敢想要去影响被当时一部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奉为楷模的西方戏剧。而且,梅兰芳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毕竟不通外文,无法和美国戏剧家进行更为直接的表演层面的交流。他的高参张伯苓、齐如山等大学者学贯中西,对中美戏剧都有很深的造诣,对梅剧团访美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他们又毕竟不通表演,难以“现身说法”。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像斯坦尼的学生泽德尼基那样,能用美国同行喜闻乐见的方式亲身传授老师技艺的跨文化戏曲表演老师,所以也就不可能把京剧的方法在美国留下来。
事实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就在梅兰芳访美的第二年,赛珍珠描写中国农民的小说《大地》出版,立刻在美国畅销———这位作家生在中国,而且前后住了几十年;第三年也就是1932年《大地》得到普利策奖;1937年又被拍成了好莱坞电影,获得奥斯卡奖;1938年,赛珍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有这些最高级的奖项都是第一次授给了一个中国题材的故事,而且那是一个极其真实的故事———尽管演中国农民的主要演员都是化了妆的白人。梅兰芳回国以后的三四十年代,纽约百老汇舞台上还演出过好几出中国戏剧,都很受欢迎,应该说和梅兰芳访美造成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却没有为中国戏曲的进一步传播做出多少贡献,因为那几个戏都只是在舞台上讲了中国内容的故事,却并没有真正呈现出戏曲表演的形式,说到底都只是文人的作品,缺乏真正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的参与。
前文说到早在1912年百老汇就首演过一个美国剧作家写的“中国戏”《黄马褂》,该剧多次重演,包括梅兰芳访美之前的1928年和之后的1934、1941年。《纽约时报》对1928年的演出是这样评论的:“这个运用了中国舞台样式的戏有着自己的西方意图……就像十六年前大幕拉开时所表现的风味和欢乐一样。”①评论家已经看出该剧并不是很正宗。到了1934年,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梅兰芳的正宗戏曲表演,他们对《黄马褂》的评论就更加尖锐了,《波士顿晚报》的剧评称之为“早期在法国被称为‘中国系列’的那样一种东西,它或许看上去很‘假’,而这恰恰也是它所能带来的快乐。②”就在这以后不久,又一个相对正宗的中国戏来到了百老汇———那是一个内容上正宗,但还是没有戏曲演员的中国戏,它的剧本就是戏曲观众耳熟能详的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由精通英国文学、戏剧的翻译家熊式一在英国改写而成,于1934年在伦敦的一个小剧场演出,并于1936年一月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这个由美国人导美国人演的讲英语的中国戏连演了105场,还进行了全国乃至四个国家的巡回演出,可以说商业成就超过了梅兰芳,但评论却远远比不上梅兰芳所得到的。权威剧评家布鲁克斯·阿肯森是这样写的:“几年前《黄袍记》(即《黄马褂》———引者注)引导我们看到何为天真纯朴的中国演剧;也是几年前,梅兰芳博士使我们对纯粹的中国艺术惊鸿一瞥……除了领衔的演员,《王宝钏》的演出很寻常。”③
宰相的公主王宝钏爱上短工汉子薛平贵,嫁给他以后却很快就沦为了弱势一方,这样的故事本来是生活中不会发生的,但对看惯了舞台上的白日梦的中国观众来说,却是早已见怪不怪。考虑到对写实要求更高的西方观众的口味,熊式一特地把薛平贵原来那个短工汉子的身份改成了宰相家里的园丁,小姐王宝钏看上家里的园丁,这就有点像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著名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情节了,对英美人来说应该容易接受得多。但没想到,评论家还是觉得这个戏很不真实:“他(熊式一)对中国戏剧的平静的叙述几乎使每一个西方权威确信他在撒谎,《王宝钏》成了可爱的冒牌货。”阿肯森最后的结论是:“满怀着应有的谦卑,我们赞赏‘中国’戏剧,对眼前的奇迹目瞪口呆,脑子里一片空白。但起码在短时期里,我们无法理解它。”①还有一位评论家帕西·哈姆写道:“人们从(《王宝钏》)中的收益一如二十年前的《黄袍记》,中国的舞台更像个儿童乐园,而不是成熟深刻的艺术。”②为什么评价如此之低呢?关键在这个“中国的舞台”其实并不正宗,就像前面引文中的“中国”戏剧要打引号一样。剧情内涵是中国戏曲的,外表的服装和舞台装置,包括检场人的设置等等也是中国戏曲的,而连接此二者的最主要的中间一环———表演———却不是中国戏曲的,内容和形式在打架,难怪夜夜看戏饶有经验的纽约剧评家看出了一个字———假!这就说明,在中国戏曲走出国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表演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梅兰芳回国以后,在百老汇上演的“中国戏”中,表演成了一个瓶颈。中国的传奇剧情让美国的话剧演员去演,别扭生硬是免不了的;但不难想象,王宝钏的故事如果让梅兰芳来演,美国观众一定会觉得可信。不过问题是,梅兰芳访美演出的全是突出演技的折子戏,最长也就二三十分钟,他的真正讲述完整故事的全本大戏还没有在美国舞台上受过观众和剧评家的检验。所以,怎么才能把中国戏曲精美高超的表演和丰满深刻的剧情结合起来,一直还是中外文化交流中未曾完满解决的问题。
① 转引自詹姆斯·哈贝克:《〈黄袍记〉和〈王宝钏〉遭遇美国》,《戏剧艺术》1999年04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