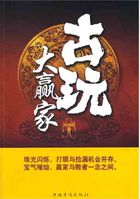刊发于《前卫文学》2013年第二期
一
小杜师傅好像是被鬼子的大炮给轰到沧州的。他有手艺,一把剪刀上下翻飞。保长见他从天津卫来,手里拎的是包着洋铁边儿的考究的牛皮箱,就尝了个鲜。一圈干枯的黄毛拾掇得像牛舔过。保长便允小杜师傅住下。原来一爿驴肉火烧铺子,早被搬了个空给他安顿。
小杜师傅的一日生活又忙碌又单纯,他伺候男男女女的头发,像伺候情人一样。他把大洋和纸币收起来,把各色好奇的目光都倒出去。
偶尔听到炮声,是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对日本人的驻屯军开火。一声响是自己人的,两声响是鬼子的。
他想,还离得远。他的拇指蹭了蹭锋利的剃刀。
小杜师傅原有家小理发馆儿,就在天津城厢东南闸口。他爱淘腾,闲时从起士林的西餐店里顺来人家丢掉的明星杂志,照着摩登女郎的发型依样画葫芦,还挺时髦,太太小姐们都趋之若鹜,生意好得不得了。
偏生那日理发店里就剩下一个嚣张的日本浪人。
浪人在他的店里对打下手的琴表妹动手动脚。盘扣掉了一地。
他在温水盆里舒活了两只手,趁着给那浪人刮脸,手腕一沉,剃刀往下伸了一寸。浪人肥腻的脖子上就添了道血口子。
血就毛毛虫一样淌在他的剃刀上。
那天是民国二十六年,公历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城外的炮就没断过。驻扎津郊的三十八师和天津保安队向日军的海光寺兵营、东局子机场、天津东站猛烈开火,干掉了车站的所有鬼子兵。日本人也红了眼,出动重型轰炸机,怪叫着扔下炸弹,到处是魂飞魄散的爆炸和硝烟。
以往小杜师傅觉得自己一个小老百姓,马马虎虎活一下就不错,大刀片砍人是丘八的分内事。他都没想到他下起刀子来真顺当。即使浪人的血汩汩的腻了满手,也只当是上等的剃须膏。
片刻之后他回过神来了。手也开始不听使唤。
他用最后的力气把表妹从后门拽走。
琴表妹一直以为自己是许过杜表哥的,可是表哥匆匆把她安顿在亲戚家里,自己只带一个装满了剃刀剪子的皮箱,混进撤防的队伍里,逃出城了。
临了临了,她想听的话一句没听到。
想起来也就是眼前的事。
沧州地方小,人也少,间或有老少爷们疏疏拉拉地来剃头,只是三五角钱的小活儿。小杜师傅想,饿不死就行。又惦起路上捡过一张什么报纸,一时空闲了,翻出来看,上面号外斗大的“张逆自忠”四个字。
他认出张自忠的小像。张在天津当市长时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又是办学校又是救济孤寡的。前几年在喜峰口、罗文峪,他的大片刀部队把鬼子砍得哇哇叫,打出了中国军队的精气神。怎么转眼就成了汉奸了。
隔壁有邻居过来,站在两扇门外面,说,“小杜师傅吧?生意不错啊。”
小杜师傅忙往里让,赔笑,“真是失礼了,邻里邻居的,也没过去拜访。”
隔壁先生一身长衫,笑着回道,“我也搬过来的没多久。”
隔壁先生有一头乌发,梳着大背头。小杜师傅想,这发式都是搁在场面上的油滑人的脑袋上的,这一位的背头,忒显老了些。
隔壁先生自报家门,姓梁,留过洋,在天津德国人开的医院里当过主刀大夫。
怎么屈尊来的沧州呢?
见梁先生不想深说,小杜师傅也就不问。
梁先生的一日生活更单纯,总是关起门来自家读读书,饮饮茶,戏匣子里听听尚小云老板的《摩登伽女》《梁红玉》。
小杜师傅这边给好容易来的一位女顾客梳头发,想着,隔壁先生怎么好西皮二黄呢,不是该坐在起士林西餐厅里用亮闪闪的刀叉扒拉牛排的嘛。
偶尔也听到那边收音机调频,一忽是新闻播报,说张自忠任北平绥靖主任,宋哲元二十九军撤离,一忽放着东洋的歌,女人的唱腔像哭死孩子。最终还是停在戏文上:
“叹江东百万黎庶怎胜饥冻,政局动荡,国难重重,恨我难酬壮志,又怕江山断送……”
小杜师傅把逃难前天津最时新的黑胶碟放进自己的唱机,铺子里便有歌星白光那钢丝般的女中音在飘,“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跟隔壁有一搭没一搭应和着。
小杜师傅也去隔壁回访,梁先生单纯的生活就有些变调。梁先生邀请他喝铁观音。茶海摆上,白细清透的骨瓷盖碗,茶盖刮去泡沫,手腕灵活地冲过第一道茶,再慢慢品。
小杜师傅心里嘀咕,兵荒马乱的,还能这么四平八稳。
不过小杜师傅觉得梁先生并不讨厌他的打扰。因为梁先生爱去理发店发呆。
小杜师傅就说,“来的都是客,我也给您理个发吧?”
梁先生施施然落座,说,“我这头发还不长,那就帮我修个面吧,谢谢。”
小杜师傅用柔软的毛刷蘸着剃须膏,勾勒着梁先生的下巴颏儿。地阁衬,天庭满,贵人面相。
梁先生赞,“小杜师傅的手真美,心也细。”
也不是头回有客人赞他的手。
小杜师傅还是喜欢极了,“是我手艺美吧。”
二
悠闲了没有几天,城外炮声与往日不同,街上的溃兵多了起来。夜深了,小杜师傅正收拾刀剪,隔壁来拍门。
一向四平八稳的梁先生把门砸开了,“小杜师傅,请你帮个忙!”
小杜师傅把理发箱子一阖就跟出去了。他才明白原来听到闹嚷嚷的声音,都是隔壁门口一堆大头兵们发出来的。
梁先生喝茶的那张檀木桌已经变成了手术台。上面躺着一个伤兵,周围几个弟兄。大概是他的一位长官,死死地握着伤兵的手。
小杜师傅挤过去一看,差点儿呕出来。那伤兵胸脯子上一道长长的骇人的刀伤,血汩汩地冒着,肉也翻着……小杜师傅下意识捂了眼睛,这不是开膛剖肚了吗?
梁先生捏了他的手臂,“小杜师傅,我要赶紧做手术缝合,麻烦你给我打下手!”
小杜师傅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只得赶紧点头。他对自己说,我也是割过小鬼子喉管的……
几个一脸血污浑身泥土的兵们都围着檀木桌叫,“老李,老李……你坚持住,连长都给你找到大夫了!”
梁先生戴好了胶皮手套,对那位连长说,“长官,这位小兄弟伤势太重,我只能尽力。”
连长仍然死死握着伤兵的手,只是抬起血红的眼睛,像头老虎在悲伤的低声咆哮,“大夫,大夫我相信您!您救了他,以后他的命是您的,我老铁的命也是您的!”
梁先生摇了摇头,说,“我要开始了,时间紧迫。……我居然还带了些麻药!”
小杜师傅不敢看那个铁连长,他只能紧张地盯着梁先生大口罩上露出的一双眼,随时递去止血钳、镊子、手术刀、针和肠线……
兵们伸长手臂高举着从几户人家借来的油灯,屋子里仍然昏暗。胳膊酸了,右手再换左手。小杜师傅觉得夜好漫长,似乎永远都不会天亮。偷空瞄了一眼伤兵,不到二十岁吧,胡子还没长出来。他还跟着师傅学手艺的当儿,这伤兵和他的兄弟们就跟着那铁连长在喜峰口同鬼子拼过大刀吧……哪里是老李,明明只是个小李。
麻药不够,李伤兵忍着伤口的疼痛和利器对他身体的整饬,浑身像浸泡在水里,没有血色的嘴唇被牙齿咬得惨白。
铁连长从窗前折回来,把胳膊递过去。老李犹豫了一下,便不迟疑,一口咬了下去,跟着一行眼泪滚落腮边。
梁先生额上的汗和伤兵一样多,小杜师傅赶紧掏出自己的手帕给梁先生蘸一蘸脑门子。梁先生没有说话。看到梁先生放缓的眼神,他想,老李肯定有救了。
天大亮,老李的胸脯子终于缝好了。梁先生给他打了破伤风的针,对铁连长说,“我这里只有这个,必须送到大医院去……”他又意识到自己在痴人说梦话,便重重叹了一声。
铁连长又双手死死握着梁先生的手,声音有千钧,“多谢!兄弟我无以为报,唯有多杀鬼子!”
小杜师傅以为,铁连长和他手下的兵会在隔壁将养一段日子,他们却同镇上其他零散的兵一道,被不知哪里来的卡车拉走了,像被劫走的。小杜师傅还捐出了自己的铺板给那个伤兵老李作担架。
老李半睁着眼,被兄弟们抬着,朝小杜师傅抬了抬手腕。
小杜师傅便去看看梁先生,他知道忙了一夜的梁先生一定疲惫极了。
梁先生却在收拾行李。梁先生说,“刚接到通报,我被征召了,他们要我当医官,我得……到三十八师的医务部……报到去。”
小杜师傅问,“这么急?”
梁先生说,“倭寇作乱,我一介匹夫,也该竭尽所能,救治更多的同胞吧。”
小杜师傅说,“那……您还没试过我的手艺呢。”
梁先生顿了顿,“来日方长,一定有机会的。”
小杜师傅有些抹不开面儿,最后支吾,“我相中您那头发了,总得让我摸上一摸吧。”
梁先生就仍然四平八稳的,坐在檀木桌旁的明式靠背椅上,冲他微微一笑。
小杜师傅便终于摸到了梁先生的大背头。他把自己的手指轻轻插进那浓密的头发里,摩挲了一下。
“得嘞,先欠着了,一定要试一试我的手艺。”
最后,梁先生跟他告别,两个人握着右手。梁先生的手沉稳有力,手指修长,果然是操手术刀的手。
“您保重!”小杜师傅说。
“您也保重!”梁先生回着。
三
梁先生这一走,就走得干干净净。小杜师傅开始还帮着打扫一下隔壁。后来客人越来越少,连自己的铺子都清闲下来了。
要不就关门吧,歇一歇手,寻摸点儿别的事做。天津是断不敢回的。也不知琴表妹怎么样了。他无力再保护她,安顿在亲戚家该是最妥帖的办法了。
他收拾收拾细软,也就一个手提箱,全部家当都装得下。
柴门简陋,也是一户。小杜师傅轻轻合上门,准备去跟保长辞行。突然保长带着几个兵士倒找上门来。
“这就是本地理发的小杜师傅。”保长赔着笑,“天津来的,手艺端的好。要不老总先试试?”
兵甲说:“不试了不试了。你是杜师傅?”
小杜师傅鞠躬哈腰,口里称是。
“着啊,你不是那天,那个给大夫打下手的小师傅?”
小杜师傅也记起来了,“巧了,这不没几天的事嘛。”
兵乙说,“既然都不是生人,咱们也不客套了。是这,弟兄们有日子没有理发了,这胡子拉扎的。一会儿把人马都给你拉来,你给拾掇拾掇?”
那敢情好。“包各位老总满意。”小杜师傅说。
“别老总老总的,俺们不兴这个。”兵丙说。
兵们呼呼啦啦又走了。
保长帮小杜师傅烧开水,磨剃刀,重新摆好剃头的各色器物。
“往哪里走啊?哪里不都一样,到处放炮,都是不长眼睛的。”保长自言自语。
小杜师傅也没想好回一句什么,就听门外喊号声和脚步声。有个长官在训话,说什么按班排序列,叫号理发,余者原地休息。
一个一个的大头兵进屋。他们几乎没有几个利索的人,不是胳膊绑着夹板,就是拖着腿。还有包着脑袋的,知道自己也没的头可剃,就蹲在一角,摸出烟卷来咂摸。
小杜师傅来者不拒,动作娴熟地刮着脑瓢,颇感牛刀小用。
在天津,他在日租界接的大都是时髦客人,除了有蛮横的日本人不给钱,日常进项还算可观。沧州自然比不得天津。他又是头一回给兵士们剃头,心里掂量着好歹。若是他们不给钱,剃霸王头,也只得由他们吧。谁让他自个儿一时技痒难耐。
兵们一个个摩挲着青瓜脑袋,称心如意。
原来西北军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自来就是背大刀,剃光头,从师长到火头兵,上下一体,好认得很。
“师长也剃光头?”
“那是自然。你看我们张师长,别说剃光头,就是吃的,穿的,从来都跟我们一个样。”兵甲说起长官来,口气像说自己的老爹老哥一样亲昵。
“关键张扒皮会打仗,我们都服他呢。”兵乙接茬。
“张扒皮,是天津的张自忠张市长吗?”小杜师傅问着,手下仍不闲着,仔细地刮着鬓角。
“正是呢。”
“可是,我听见说,说他去主政北平,当什么绥靖主任,听日本人的?”小杜师傅期期艾艾地问。
“胡谝!”兵丙怒了,“听鬼子的话,我们师长就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是汉奸们造谣,坏我们师长呢。”
“老总恕罪,老总恕罪。”小杜师傅忙不迭赔礼。他想起路上捡的那张报纸,说是张自忠把原来二十九军在冀察政委会的委员都开了缺,却聘了一干汉奸上任。究竟怎么个情形,他一介草民,想不清里面的玄机。
“都吵吵什么!”一直在屋外的长官最后才进来,正是那天带来伤兵的铁连长。
铁连长大马金刀坐下。
小杜师傅打点起十二分精神,一把刮刀使得纯熟。他想问,你们那个老李还是小李的,怎么样了?看铁连长疲惫的神色,始终没敢问出口。
铁连长倒先搭讪,“你这天津师傅,怎么到的沧州?”
“不瞒各位老总,我也……弄死过一个日本浪人。怕了,跑出来的。”
“有尿性!是条汉子。”兵甲喝了一声。
铁连长点点头,站起来,布军装口袋里掏出几块钱来,摁在桌上。“杜师傅,这是我的饷银,也没有富余的了,就算弟兄们这几个的,若是短了些,还请多担待。”
小杜师傅赶紧把钱推回去,“这怎么好使得?老总们前边打鬼子,我给老总们剃个头,应该的。”
铁连长不由分说,把纸币和碎银毫子装在小杜师傅一边的皮箱里。“我们穷,但纪律还是要讲的。若是要张师长知道了,还不扒了我的皮?”说着血淋淋的扒皮,竟是笑着。
小杜师傅也就不敢推辞了。
兵甲起兴,“小杜师傅,你跟我们有缘哪,不如跟着我们吧,当个随军剃头匠。”
小杜师傅只是笑笑。“我一个逃难的,哪里能随了军呢?”
可他竟真格的拎了皮箱,跟着这个不足百人的营开拔了。
他也真格的当着保长的面,掩好两扇门。“说不定就还回来。”
保长嘬着旱烟枪,扬了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