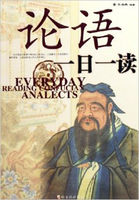2.《读者》的创办
1980年的秋天,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曹克己找到编辑胡亚权,要他办一份杂志,胡亚权一口答应。那时,与全国上下“锣鼓喧天”的办刊热潮不同,深处内地的甘肃出版业还是悄然无声。刚刚调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曹克己希望运作一份属于出版社自己的杂志,这个老报人只专注于方向的领导———他要胡亚权办杂志,要人,给!要条件,给!至于办什么杂志,曹总编并不明确给予干预意见。胡亚权将郑元绪选为合作伙伴———两个年轻人对于办什么杂志苦思冥想数日未果,是报架上琳琅满目的杂志给了他们启发:杂志越来越多,怎么看得完,要是有一份精华摘要性质的杂志就好了!
这不是中国的第一份文摘类杂志,而胡、郑二人的基本想法,是避免与其他文摘类杂志雷同。按照设想,他们的这本文摘类杂志,是包括时事、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各个方面的综合类杂志。很快,关于创办文摘类杂志的报告得到了批准,但是他们又被杂志的命名难住。不久,几本寄自香港朋友的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办一本中国人的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被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的气质风貌深深打动的胡亚权发出感慨,他觉得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的办刊理念完美地贴合了他对于即将诞生的这本杂志的构想,又能体现“编辑为读者摘文,读者为编辑荐文”这一主旨,所以经过出版社商议,决定杂志亦定名为《读者文摘》。20世纪80年代初的许多办刊人为其创办的杂志确定名称与办刊思想时,很多都直接借鉴别国刊物,习以为常。且“版权”一词对那时的中国人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随着这一中国最具力量杂志的诞生,日后那场旷日持久的中美杂志刊名官司,就此埋下伏笔。1981年,《读者文摘》创刊,定价3角,印数3万,首期仅卖出15000份。
20多年后,她成为中国目前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传阅率最高的一本杂志。2004年,《读者》杂志发行量首次突破1000万份;2008年,《读者》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第184位,品牌价值达40.83亿元,列国内传媒行业第17位、杂志类第1位;入选第三届亚洲品牌500强,位列第221位;荣获2008年“中国娇子新锐榜”推委会特别大奖———30年十大中国骄子,《读者》的颁奖辞是:它是13亿中国人的心灵鸡汤,饱含真善美维生素和励志蛋白质;它是和谐社会里的最和谐音符,让读者看到世间相互的美好,品味平常生活的滋味,珍惜手头拥有的一切,激发勤奋工作的斗志。它是有益的知识,也是生活的哲学。它是情感的慰藉,也是力量的源泉。
3.新的英雄出自新的时代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和《读者》,其创办之初,均有时代浪潮作为强力助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善用每分每秒”的理念蔚为风潮。听收音机、看电影和周日开车带着全家人出游,取代用在阅读和上教堂的大量时间,成为美国人消磨闲暇时间的崭新模式———越来越少人愿意将大量的时间用在阅读长篇大论上,人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涉猎大量信息,于是更短的文章,甚至新闻摘要流行开来。文摘类杂志是精华撷取,省却了读者阅读大量杂志去粗取精的时间,符合那时美国人的生活节奏要求。同时,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知识实用性强,思想贴近大众,宣扬自我提升的理念,推销不同的价值观以迎合各种阶层,很快就成为相当一部分保守大众的“世俗圣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1980年起,出版业、报刊业经过十年“文革”的沉寂,开始全面复苏,出版社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有人甚至说:“当时好像印什么书都可以卖出去,而且供不应求。”一些“文革”期间被迫停刊的杂志,如《人民文学》、《诗刊》、《大众电影》、《新观察》、《收获》等也纷纷“解禁”,一开印发行量就很大,有的杂志一期竟可以发行500万份。据说,当时最火的《大众电影》,发行量一度接近千万,创下了中国杂志发行的世纪纪录。一夕之间,办杂志成为出版界谋求发展生机的新路。当时的报纸只有两百多种,而杂志也仅有四五百种,几乎是“办一本、火一本”。创刊于这个时期的《读者文摘》,正是为历经多年滞闷封闭、患上“读书饥渴症”、满世界找书读的国人提供了一份营养齐全、口味丰富的大餐。
变革时代颇具转型新意的社会精神,最容易催生产业英雄。社会精神包含着对新事物的需求。而需求,就意味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找准这种需求的,莫不是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20世纪前期、中叶的电子工业进程,造就了索尼、松下;20世纪末、21世纪初信息技术时代的兴起,又造就了美国在线、雅虎。所以,诞生于20世纪初美国快餐文化背景中的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和创刊于20世纪末中国“精神盛宴”文化背景中的《读者》,都是英雄选择时代、时代造就英雄的结果。即使如胡亚权在事后多年所称,最初采用“《读者文摘》”作为刊名,并非要借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的国际声誉拓展市场。然而,在办刊理念上,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绝对是《读者》血统纯正的同门宗师,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出于某种尊严考虑的辩驳的必要。
松下公司素来有“模仿公司”的雅号,其产品多数是模仿其他公司所造,却能“比别人做得更精、更好”。通过“模仿”建立庞大家业的松下,并未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止步于跟跑的地位,而是向着依附自身高新技术研发拓展市场的技术型企业逐步转型———对《读者》而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年的师徒共同站在21世纪初叶的平台之上,既然已经能够以相仿的地位姿态面对全球期刊市场的挑战,那么,这个崭新的时代中,谁能充当领跑者,或未易量。抓住时代精神,把握市场需求,不仅是创业之初的要求,而是时时刻刻的要求。
二、我生君未老
《读者》———这朵中国期刊业的奇葩拥有惊人的发行量和国内市场影响力。当然,发行量和读者口碑的确能够说明一份杂志的成就和潜力,但这并不代表它能面对新兴媒体向传统媒体发起挑战、开放市场向落后体制提出要求,也并不能够遮掩它身上无法回避的缺陷———如果不加以修正改进,这些缺陷将在它前途的美好图景中添上乌云。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和《读者》,作为师徒,在理念上相似,风格上相亲,内容上相近,形式上相仿———都为贴近大众兴趣、涉猎广博知识、着眼人性光辉、挖掘精神价值的综合性文摘类杂志,更同是两个杂志出版业的“神话”,具有相当的可比照性。即使“徒弟”早已今非昔比,有资格、能耐与“师傅”比肩,然而资历老道、力量雄厚、经验丰富的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对后起之秀《读者》来说,仍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值得学习效仿的楷模。从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那里学来的方法、观瞻的教训,更有助于确定中国期刊有效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和“战术”。
1.发行量说明了什么?
2006年,与1000万册的月发行量相形见绌的是,刚刚成立的读者集团,年收入仅为3.7亿元人民币。而读者文摘集团,则是20多亿美元,位居2006年全球出版业排行榜第8。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2000多万册的月发行量为其出版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利润,而《读者》杂志的发行量为其取得的利润率却排在发行量远不如它的国内《知音》、《时尚》、《家庭》等杂志之后。1000万和2000万的发行量同样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一本刊物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已经没有质的差别,可其背后,两个出版集团的经济效益却相去甚远。发行量到底说明了什么?对全球出版业排名靠前的许多集团而言,传统出版是其所有业务中重要但是规模很小的一个板块,同样,享誉世界的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杂志本身对读者文摘集团来说,是其历史和灵魂所在,始终标志着集团的核心影响力。该杂志巨大的发行量,是业务拓展、规模扩张以实现效益增长的最好契机,却不构成其收入来源的主干。而对《读者》而言,发行量也许仅仅就是一个能令中国杂志可以雄视世界期刊发行量排行榜的数字,一个令杂志堪称“影响一代人生活”的理由、一个值得骄傲的资本、一个有关尊严或曰地位的神话。
《读者》杂志一直甘做那碗热腾腾的心灵鸡汤、那个淡定而从容的道德守望者,一切关乎爱和温情,无关商机,无关利益。那么,当《读者》杂志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仅排在全球第44位、且是唯一进入前50强的中国出版集团的残酷现实时,那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许应当透过1000万这个数字,直达效益增长的核心问题。
2.还要向“师傅”学什么?
对于长时间属于“社办企业”、发行上仅依赖邮局、集团化处于崭新和稚嫩起点的《读者》杂志而言,新媒体的迅速勃兴、境外期刊的大幅侵入、自由办刊人的市场分割和新一代读者群体的阅读要求,仍是它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有读者甚至撰文称《读者》已至“末路”。这种说法虽然偏激,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自受众对杂志的批评和要求。软肋在哪里?如何补足它?这已经成为《读者》杂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其与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做一番比较就不难看出以下几点:
(1)体制的局限是深刻的
甘肃,《读者》杂志的“故乡”,是中国西部一片经济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土地。从最初的创办到2006年,《读者》杂志一直都是甘肃人民出版社之下的一份社办杂志。
甚至在国内名牌期刊如《知音》、《家庭》等纷纷走上集团化道路的时候,《读者》也出于种种原因固执地坚持着它的产权所有、经营体制和发行方式,这严重制约了《读者》品牌的开发利用。《读者》品牌在兰州本地进行深度开发,进军文化产业,困难重重———人才、资金、氛围、外部环境在兰州都是不具备的。开采品牌能量的关键仍然是走集团化道路。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则与之不同———独立法人,充分的财产权与独立核算权———即使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在2003年遭遇最大危机,灵活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在关键时刻助其筹集资金,转变思路,化险为夷。早在20世纪末,读者文摘集团(The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就转变依靠一本杂志的单一经营模式,收购雷曼杂志出版集团,充分发挥其品牌效应,大量抢占着出版市场。另出版有27本杂志,兼营书籍、音像制品的制作和发行业务,并通过实时电视、电缆、上门服务和互联网等许多渠道销售其产品。公司的网站和各杂志网站,更是提供让读者下载阅读电子版本的服务。
尽管凭借经典的办刊理念和坚实的读者市场,《读者》———这份戴着“体制镣铐”的中国最“大牌”的杂志仍然创下一个又一个新的发行纪录,也积极实践了“集团化”改革。但是,随着国际出版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较量已经渐渐从几本期刊之间蔓延到其所隶属的庞大出版集团。随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出现和壮大,集团化起步较晚就意味着经验不足、市场进入困难等问题。所以,经营体制方面积极锐意的改革和业务拓展方面勇敢的尝试都是必需的,否则,发行量“巨大”而收入“微小”的矛盾,必定会给仅靠一本杂志作为出版“大厦”基石的读者集团的明天蒙上阴影。
(2)品牌的能量是待采的
从经济学和营销学角度来看,品牌效应可以引发连带外部效应,表现为消费者的忠实度高,消费群体数量可持续增长,品牌旗下产品横向扩张力强劲,从而也反向刺激产品配套设施的完善和新产品的开发。
早在2000年,仍在大学任教的民盟甘肃省委的车安宁先生就已经对《读者》杂志的品牌开发提出意见提案,吁请各界重视《读者》的品牌效应,将其做大做强,发展相关文化产业。提案批转相关部门,答复是:“提案很好,时机还不太成熟。”《读者》杂志的经营模式一直很单一,收入只单纯依赖广告和发行。拥有如此巨大的品牌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杂志,多年来除了新办少许刊物,对版本稍有增加外,在资本市场少有动作。截至2007年1月18日,中国期刊发行量最大,读者影响最深远的《读者》杂志才建立起自己的网站。在信息时代,这听起来不免令人匪夷所思。而《读者》杂志在广告、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收入,与杂志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品牌经济价值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