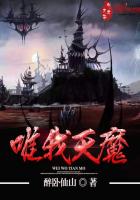第二节小说作家与书商
在阐述作家与书商的关系之前,需要先说明一下作家和作序者的关系。小说作家和作序者的关系,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序者是书商请的;有的是作者本人请的;有的则既不是书商所请,也不是作者所请,而是自己主动给小说作序,这往往是选家或者就是书商自己,他们可能和作者素不相识,只是选中了小说作品,故而作序刊行。无论如何,小说的序言是与小说的出版紧密联系着的。
明清之际小说作品序跋的写作者,不但对小说作品加以肯定,还往往对作者加以褒奖,这在以前是很少见到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序跋类似于小说的“识语”, 多宣扬作者或作品的风格和特点,有为小说做广告、促销路的成分。譬如临海逸叟在《鼓掌绝尘·叙》中所说:
余主人龚君,延选经文诗画,嗣后房稿行世,因海内共赏选叙,索《鼓掌绝尘》小引一篇。余素沉酣经史,咀嚼贤直,风流荡宕,靡不爱焉。于花前月下之趣,摈而不录久矣。归鞭尚速,马蹄厥疾,无暇览焉。主人取将竣之帙于手中,一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兹吴君纂其篇,开帙则满幅香浮,掩卷则馀香钩引,入手不能释者什九,遂名之《鼓掌绝尘》云。大正五年《含秀居丛书》本《鼓掌绝尘》,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据文中之意,临海逸叟说自己因急于从出游之地返回家乡,本无时间细读《鼓掌绝尘》一书,但一读之后,即深受感染,因之作序。他说此书“一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开帙则满幅香浮,掩卷则馀香钩引,入手不能释者什九”,对没有读过此书的人来说,看过临海逸叟的序言之后,应当会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小说中“序”的作用之一,正是在此。
临海逸叟在这里还提到了序者、作者和选家的关系。作序者临海逸叟可能是“龚君”家的门客、坐馆塾师或幕僚,所以才称龚君为“余主人”。 龚君可能是受书商委托的选家,或其本人就是书商也未可知,所以才有“延选经文诗画,嗣后房稿行世”之说。《鼓掌绝尘》应当是他所“延选”的“经文诗画”中属于“文”类的一部作品。这篇序中提到的三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吴君编纂了《鼓掌绝尘》,被龚君选中准备出版,龚君又请临海逸叟作序。
其次,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主体意识加强,多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经历和感情。由于小说中留有太多作者自己的自我形象,为不至于埋没作者的心迹和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作序者往往很自然地提到作者及其创作情况。小说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常常是“文如其人”,即小说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外化,譬如《豆棚闲话》中,处处可见艾衲居士“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嬉笑怒骂、放荡谑浪的神采;又如《无声戏》和《十二楼》中,时时可见李渔追求尖新奇巧的独特匠心。故而序者在阐释作品内容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说起作者。
序者在谈到作者时,往往表现出敬重的情感。比如睡乡居士(杜浚)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赞扬凌濛初为人为文之“奇”: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馀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
他在这里谈到凌濛初为人和为文的风格,归结为一个字:“奇”;然后说到“二拍”的创作缘起,正是作者为人为文之“奇”的“绪馀”。
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也极力褒扬周楫的才华,并感叹其贫困遭际:
予览胜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震霆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快矣乎!余何幸而得此。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周子间气所锺,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观者幸于牝牡骊黄之外索之。
在这里,湖海士称周楫为“旷世异才”、“间气所锺,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这种称誉,未免有过分之虞。但他说“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从《西湖二集》的内容和文笔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说作家与书商的交往,是作家重要的人际交往之一。做书籍生意的书坊主,必然经常与以书为伴侣的读书人打交道,更何况是写书的人。书坊主周围必然聚集一批小说作家,不管是为共同谋求经济利益,还是因为气味相投。
一般来说,书商与作者创作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书商拟定了创作题材,请作家来写,《警世阴阳梦》等紧跟时事、迅速出版的几部时事小说,可能就出于此种情况。另外,绿天馆主人(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也提到书商的敦请和成书的关系: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据考证,绿天馆主人和茂苑野史氏都是冯梦龙的别号,此处假托为两个不同的人,有托言的成分。但《古今小说》是“因贾人之请”,而从“家藏古今小说”中“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这种情况当是纪实。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刊刻,也是出于书商尚友堂主人的怂恿。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明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成书经过:
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篇,得四十种……嗟乎!文讵有定价乎?贾人一试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可见,“二拍”在成书过程中,书商的参与居重要地位。“初刻”因书商所请而印行,书商得到利益之后,又催促作者创作“二刻”。
书商与作者创作的另一种关系,是作家创作完小说之后,被书商知道了,或者作者自己拿去给书商或选家看,使作品得以面世。从前文引述中可以得知,《初刻拍案惊奇》、《玉闺红》、《西湖二集》等书,都属于这种情况。
一般而言,书商和小说作家的关系,只是一种供求双方的经济关系。但也有特殊情况。明清之际的书商不全是唯利是图之辈,也有性情比较高雅、与读书人很谈得来的书商,成为诸多士人的好友。书坊做的是读书人的生意,其营业性质决定了书坊不但是商业场所,还是文化和社交场所。士人到书坊来买书、看书、租书,甚至借书坊为聚会场所,必然要与各种各样的书商打交道,有时就能成为同声相求的知交。比如南京三山街的蔡益所书坊,布置清雅素淡,没有一点市侩气息,当时生员都爱来此逗留。蔡益所为人豪爽仗义,同情东林党、复社诸人,结交的多是南京文坛名流和国子监中的太学生,并且不卖任何诋毁东林复社或吹捧魏阉党人的作品。东林遗孤和复社主将如黄宗羲、侯朝宗、陈定生、吴应箕等人,常来蔡益所书坊聚会,商量社务,研讨时局,有时就住在书坊的客房中。至于陆云龙、李渔等书坊主,因其自身就是选家和作家,他们与作家的交往,当是互为友朋的成分居多。
陆云龙、李渔、凌濛初等,都是当时有一定影响、有一些特点的书坊主。《十六名家小品》冯次牧的序后,有陆云龙的一则类乎“征文启事”的东西,说“祈不爱其珠玉,予敢僭辱齿牙,敬把梨枣于同人,幸邮筒而逮我”,末了数行云:“惠瑶草见在杭州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
陆云龙还是选家和评点家。他编辑的选本不下十余种,流传至今尚有《明文归》三十四卷,《明文奇艳》二十卷,《皇明八大家》十六卷,《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三卷,《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合集》十六卷,《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二十一卷,《翠娱阁评选文韵》四卷,《翠娱阁评选文奇》四卷,《翠娱阁评选词菁》二卷诸种。经他编著、评点或作序的小说有五种:编撰《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四十回,《清夜钟》十六回,为《辽海丹忠录》、《幻影》和《禅真后史》等作序。
李渔也作过书坊主。顺治十七年(1660),他从杭州迁居南京,在南京创办书铺“翼圣堂”,成为一名书商。
凌濛初则出生于书商世家。凌家是湖州著名刻书之家,刊行过朱墨套板的精印书籍,凌濛初的父兄子侄辈大多是书坊主。但崇祯元年(1628)刊刻的《拍案惊奇》和崇祯五年(1632)《二刻拍案惊奇》,似乎都不是他在自己家中的书坊中刊印的。《拍案惊奇》是尚友堂刊刻的,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篇,得四十种。”凌濛初除编著“二拍”之外,还用套印法刊刻了《孟浩然诗集》、《王摩诘诗集》等书。
第三节一个典型案例——关于书坊主、出资者、故事原型与小说主题
上文我们谈到交游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创作的影响时,谈到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顺治年间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与《十二楼·奉先楼》的关系。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关于书坊主、出资者、写作者、故事原型与小说主题之间关系的典型案例。在对李渔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版本嬗变原因的探究中,我们发现张缙彦与《无声戏》创作、出版以及被禁的关系颇为耐人寻味。
李渔《无声戏》的被禁,在明清之际的小说出版界是有一定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例典型事件。当朝官员出资,资助书坊主出版小说作品;书坊主出版的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作品;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为出资官员歌功颂德;小说作品内容触及了当朝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于是官员被弹劾,小说作品被禁,书坊主受冲击,被迫将小说作品改头换面、增删调整,重新出版赚钱;以至于造成复杂的版本流变情况,为后来关于这些小说作品的版本研究、主题意旨研究制造了很多迷雾。
从《无声戏》到《连城璧》、《十二楼》复杂的版本嬗变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与出资者、故事原型与小说主题之间的密切关系。
20世纪以来,李渔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的版本嬗变,一直为学界所注目,海内外已有十多篇文章专门予以梳理辨析,其他还有多篇论文、论著附带论及。从《无声戏》到《连城璧》、《十二楼》的嬗变过程,大致已经梳理清楚,但由于可供继续研究的资料极少,仍然留有众多疑点,未能解决。笔者在阅读中发现一些前人尚未提及的资料,又有一点自己的看法,未知确否,公之于众,求教方家。
一、张缙彦与《无声戏》的“编刊”
清初顺治年间,满清王朝入主中原未久,南明反抗势力犹存,人心不稳,天下大局仍然漂泊未定,清朝官员之间的满汉之争、南北党争异常激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也在劫难逃地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李渔早期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的刊行问世,就曾引起过很大的政治风波,成为清初南北党之争中刘正宗、张缙彦一案的一条重要罪证。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弹劾前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其中一条罪证是:
缙彦仕明为尚书……及闯贼至京,开门纳款。犹曰事在前朝,已邀上恩赦宥。乃自归诚后,仍不知洗心涤虑。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臣未闻有身为大臣拥戴逆贼、盗鬻宗社之英雄。且当日抗贼殉难者有人,阖门俱死者有人,岂以未有隔壁人救活逊彼英雄?虽病狂丧心,亦不敢出此等语。缙彦乃笔之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慕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