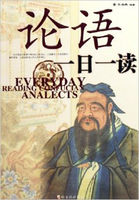在清末变通旗制期间,大部分驻防都设立了一些八旗工厂或习艺所。
由于经费所限,各地八旗工厂的成效普遍不大,加上工艺不成熟,产品质量较差,很难打开销路,导致工厂在运作的过程中步履维艰,更谈不上扩充规模。但是应该承认,这些工厂的创办确实产生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后,掌握一技之长的旗人得以比较顺利地就业谋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清末八旗工厂的创办。
4.兴办学堂,发展教育
根据其内容和性质,清末为筹划旗人生计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教育,如开办农业讲习所、工艺传习所等,在旗人中普及一些浅显的职业知识;另一类就是普通教育。前一类,前文已有所涉及,这里着重介绍普通教育的情况。
1903年3月20日,袁世凯在奏疏中提到:
臣前面奉谕旨,以八旗兵丁生计日蹙,饬在挑选旗兵内考拔学生,分遣各学堂肄业以广造就……惟查此次所挑旗兵,其间资性朴勇者固多,而聪颖识字者甚少,以之入营训练,则精壮有余,以之就学肄业,则启迪匪易。拟恳饬下八旗、外火器营及圆明园健锐等营,另选天资聪秀,文理粗通者,候由京旗练兵翼长内阁学士臣铁良赴京,分别考验。再由臣复加考试,以便分遣入武备、医学、农工、机器、电报、铁路各学堂,切实讲求,以期成就。其四五品以下世职各员,并八旗举、贡、生、监,有志向学者,亦准其一律送考,以仰副朝廷嘉惠满蒙,作育人才至意。
可见,此前清政府已经有了通过兴学来扶助八旗生计的考虑。稍后,山东巡抚周馥奏:“旗丁生计日蹙,请挑选八旗聪颖子弟,入武备、医学、农工、机器、电报、铁路各学堂,以期成就,”获得允准,进一步证实了清政府上述想法。通过在京旗和山东驻防的小规模试行,清政府于正式宣布为八旗“另筹生计”前后,将这一做法向全国各地驻防推广。1907年4月,为了吸引生计困难的八旗子弟入学,清政府特别作出规定,凡八旗子弟由初等小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准其尽先挑补马甲以下钱粮;由高等小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准其尽先挑补马甲以上各钱粮;次年,进一步补充说明:“嗣后各旗挑补钱粮应查照上年部文,无论官立、公立、私立小学堂学生均一律尽先挑补,以昭公溥,其有现已毕业,经督学局考验合格,给予毕业文凭,加盖关防者,应准坐补钱粮”。
在清政府的一再倡导下,各地驻防增设学额,劝导八旗子弟入学,取得了一定成绩。迄1907年底,动手较早的绥远已设立陆军、中学、高等、初级、蒙养、半日、清、蒙各学堂18处,接收学生800余人;奉天除将原有小学堂五处按照新章加以整顿,设立高等、初等各数班,招收学生360名进行培养外,还专门创设满、蒙文讲习所,以便促进奉天和蒙旗各部落的沟通,应付沙俄的觊觎和侵略;即使在“僻处一隅”的宁夏,也节缩马粮,设满汉义学2处,接收学生120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惠兴女学(它起初由一位旗人妇女创办,后来被官方接手),据奏报,到1910年为止,已有初级师范、高等小学、初等小学等各类学生从那里毕业,而且对美术、手工、女红、绣品尤为擅长,在当年南洋开办的劝业会上,该校送往参展的美术、手工、女红、绣品达147种之多,并获得金牌和优奖。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晚清兴办八旗教育的确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辛亥鼎革尤其是停发旗饷后得以顺利就业的满族人,除了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一措施的受益者。不过限于财力,兼之囿于风俗,清政府通过兴学来解决八旗生计的做法同样并不现实。在各地兴办学堂的过程中,驻防长官因款项无着,大都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因为就学并不能在经济效益上立竿见影,所以旗人愿意送子弟入学者,本就寥寥,入学之后,退学者又屡见不鲜,甚至在京师各学堂,如钦天监天文算学馆等也是如此。无奈之下,有的驻防长官不得不恩威并施,如广州将军增祺向清政府反映,由于旗人子弟“非因风气初开,不免为习俗所囿,即因家计所累,暂图糊口之方”,大多不愿入学,他不得不“严饬各该协佐领等官,先将七、八岁以上之幼童以及二十岁以下之成人,无论为马步甲,为闲散,为壮丁,逐一清查,各有若干名,除已在各官立私立学堂肄业及充当新军、挑赴工厂学习工艺,暨因家道贫寒,必资营业生活者不计外,其余均为详细开导,督令一律入学。如有无故不就学者,即将其父兄处以责罚”,真可称得上用心良苦了。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筹八旗生计落实最好的地方是东三省,而东三省之所以能够走在各驻防的前面,主要缘于其“家有地亩”的自然优势和“世为农工”的生产劳动传统。单就各地最为头疼的款项问题而论,东三省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据金梁估算,三省八旗官兵及内务府所属向有随缺伍田、庄园、山场等地,统计约及150万亩,足可供旗丁解甲归农之用;而且正额之外,被隐占盗典,久未清理的“浮多”之地,尚不止数倍,“如能一律清查丈放,按地收价,至少之数一千万金以上”。其实早在1902年,清政府就下令将从未输纳过钱粮的吉林“通省旗户自占之地,出卖之地及站丁、官庄之地,悉行报明,派员查丈,一律升科”。1905年,在赵尔巽奏请下,东北所有官庄地,一律被纳入丈放收价范围。至1909年,经政府丈放的官庄地已达1356700余亩(内带地投充原额地30460亩),收地价银1821000余两,从而为计口授田,兴办工商各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在筹八旗生计成绩最大的奉天,一旦将各项计划运作起来,经济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压力。1909年,锡良向清政府汇报了清查旗署款项筹办八旗生计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办各项实业的款项也大都是东挪西凑,眼下尚可无虞,但难期长久维持。
奉天尚且如此,其他各驻防筹办八旗生计的前景就更可想而知了。
(三)改变“旗”、“民”分治,旗人治旗的社会控制格局,促进“旗”、“民”社会的一体化
在清代“旗”、“民”分治的社会格局下,旗人向来由自成一体的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臂指相使”,节节控制,有关旗人事务地方官一般无权过问。这一社会控制体系对于巩固满族统治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其中在清末倍遭非议的一点,就是它造成了满、汉双方感情隔膜,龃龉丛生,如张元济所言,“事关旗制,汉则曰不便措辞,事属汉务,旗则曰可勿过问”,“亦有貌为和衷者,实则依回迁就,敷衍了事,而形格势禁,终有此疆彼界之嫌”,尤其在驻防省份,“旗汉互争,该管官各有袒护,于是积不相能,乖气致戾”。在通常情况下,所谓“各有袒护”,主要是旗官对八旗兵丁的纵容和庇护。根据规定,旗、民之间发生纠葛和冲突,应该由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共同审理。但一旦旗丁涉案甚至是毙伤民命后,佐领、协领等多徇情枉法,不仅不予积极配合,甚且在被饬交出涉案旗兵后,仍百般拖延,代为欺隐,因此导致审理常常不能顺利进行,或不了了之,或单方受罚,结果是旗、民之间积衅难消,争端不断,旗兵有恃无恐,愈发骄横,成为地方官一块心病。
1892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就曾碰到这样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是年年初,荆州东门外距城五里的草市后街泰山庙演戏酬神,旗丁小福等想要上台看戏,被管台的庞加顺拦阻,遂导致旗、民混相殴打,其后,旗丁屡屡寻衅,先后造成民人2人死亡,多人受伤。人命关天,地方官曾企图会同理事同知审理此案,但困难重重:搜集证据时,民人伤轻者,恐被讼累,不敢报官,纷纷隐瞒伤情,旗兵则轻伤报重伤,无伤报有伤,为公正审案造成阻碍;此间,草市人进城经商办事,途经旗兵驻扎的东门外,又多次无故被殴;而且,旗兵所在协领始终拒不交出逞凶案犯。在这种情况下,江陵县令龙兆麟只能将此事禀报荆州知府舒惠电,舒惠电又转禀张之洞,寻求解决。张之洞查考道光年间荆州旗、民因观划龙舟而交讧最后提省审办的成案,一面差委裕庚会同荆州府暨理事同知提集旗、民滋事要犯人证,秉公审理,一面移咨将军祥亨要求配合,并郑重声明,“如该协领等延不交出正凶,该印委各员难以会审。臣等即查照道光年间成案,饬提此案应讯人犯要证至省,督同臬司研讯确情,分别定拟奏明请旨办理”。在朝廷的重视下,案子最终虽得以妥善解决,但其中所暴露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张之洞为处理案件,可谓煞费苦心,不过他所提到的特别措施也只能是偶一为之,要根本消除上述恶果,只能求助于旗、民分离体系的变革。
20世纪初,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旗兵不法滋事,逍遥法外”成为《申报》等报刊抨击的对象;与此同时,随着旗、民居住和交产等一系列壁垒被打破,旗人被允许离开旗营,择地自便谋生,旗、民分治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旗”、“民”合治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