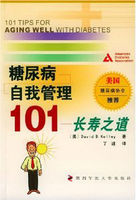不只是表现在民众反洋人洋教的舆论上,其实所有题材的传闻都可能基于这种心理因素。下面不妨再举关于民间对官员政情评价的两则传闻事例来略窥一斑。人所熟知,丁宝桢以在山东巡抚任上捕杀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而名扬朝野,他光绪二年(1876年)升为四川总督,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卒于此任。川人中有关于他的“四天四地”谣:“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迎公之来,欢天喜地;观公之政,昏天黑地;送公之去,谢天谢地。”还有清季名臣张之洞,据说就任两广总督后不久,也在粤人中落得类似的传谣,只是与上引谣词个别字眼上略有不同而已:“闻公之名,惊天动地;望公之来,欢天喜地;见公之事,乌天黑地;愿公之去,谢天谢地!”这种谣歌虽然没有具体的叙事情节,但无疑也应视为传闻的一种形式,属评价性传闻之列。
从所引录的这两则谣歌来看,不论是对丁宝桢还是张之洞来说,都反映了辖区民众对他们始则寄予厚望,由衷欢迎,继则观其政务,大失所望,由喜转厌,愿其速去的这么一种心理演变过程。这从对张之洞谣辑录者的说明性文字中可得以更具体的印证:“张文襄由晋抚擢督两广,命下,粤中舆情大欢,几有我后来苏之望。乃下车首开赌禁,办事者务铺张。以建筑广雅书院言之,且糜帑至数十万。督粤未一年,工作繁兴,赋敛无艺,至是,粤人始大失所望。”我们且不论这种评价是否符合实际,以此来说明有关传闻生发的感情宣泄与愿望表达的心理基因,不能不谓典型。
三、文化偏执心理
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传闻,特别是牵涉到外域人和事物者当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列强恃其坚船利炮强行摧开中国国门,“天朝”的锁国壁垒坍于一旦,使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长期处在闭塞的环境之中,即使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在最初与“夷敌”交锋接触的时候,也不免带上陌生和迷惑的目光。像最先受命赴粤主持禁烟和御夷的林则徐,也曾对当时比较普遍传扬的一种说法,即“夷人”须赖中国的茶叶、大黄,一日无之则病,数日无之则死,表示出信实,把断绝向其这方面的供货视为可以制敌的要术。他甚至还曾明确将英军“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的传闻之事信实地形诸奏章。至于在一般士大夫和民众当中,关于“夷人”的千奇百怪的传闻更大有市场。甚至西洋人貌相上与华人的差异,也成为有关传闻的重要素材。那时初见西洋人的样子,人们每每大惊小怪。据先为传教士又在华任外交官员的美国人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记述,1874年即清同治十三年的秋季,他偕两位本国同伴在中国内地游历,当“途经一个大约十万人口的城市时”,“人们几乎倾巢而出”围观他们,他们中一个身材短小而留着垂至胸间的浓密长胡子者,竟被围观者指为女性,认作是何氏的夫人,说是在他们国家女人和男人一样长胡须,持此论者还被别人认作是有“渊博知识”的人。当时诸多国人除了对强行闯来的夷人的痛恨之外,也是带着文化上的优越感来由表及里地观照他们的,若辈与华人不同的貌相,实际上是被看做了其处“蛮荒之地”、属“化外之群”的外在标志。或谓其“类魑魅之形,具猿猴之象;出身苦海,甘游鱼鳖之群;窜迹荒山,豢养豺狼之性”;进而蔑视它如“蜉蝣不知朝暮,蝼蛄不知春秋,夏虫不可语冰,井蛙焉能测海”,大有“华夷不可同居,人鬼岂容并域”之概——这是颇具典型性的。至于对其“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三纲五常全不要,一点圣贤不知道”之类的直接指斥,以及由此所生发的传闻,更是诸多反洋人洋教宣传品中所惯有的。
在这中间,还有特别醒目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洋人嗜淫的特别强调。在反洋教题材的传闻中这是一个非常盛行的话题。即使对侵略战争中洋兵罪行的揭露,当时许多人的特别关注点或亦在此。譬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当时京民初见洋人,耳闻目睹侵略者的横暴行径愤恨而又惊恐之下,有人这样状描他们心目中对“夷鬼”的印象:“诸夷性皆贪而极淫,所到之地,首掳银钱衣物,次及牲畜,或宰食,或牵卖,虽鸡犬靡有孑遗。惟不多杀人,掳去亦多释回。独见妇女,则未有不淫,无论青娥老妪,西子无盐,避之不早,死之不速,无不被污被掳者。”并且还举及这样两个具体事例:一是洋兵进入北京之前,郊外张家湾一带“妇女闻警自尽者二千数百人”,有个回回老阿訇,自称能诵咒使洋人退却,于是,未寻死的妇女们多藏身其礼拜寺中,但“及英夷大至,诵咒无灵”,所藏妇女被“尽行掳去”。再是京城广渠门外双树村,金姓庄头有两个妙龄娉婷之女,被洋兵掳去,金庄头奋力追攻,“手刃二女”,回来后亦举火自焚。记述者既赞叹于金庄头父女的“节义凛然”,又对比遭掳淫的妇女前例而大发感慨地说:“天朝礼仪之风化,贞洁自守之闺女,乃辱于禽兽不如之强暴,能无把酒问天、拔剑斫地耶?”
侵略者奸淫方面的恶举肯定有之,无疑是其侵略罪行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但上面所引述的情事推敲起来当传闻之属,不仅评论上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叙事情节上也不可能尽然符实,肯定加入了定性描述的渲染成分。这从记述者接着对英国伦理习俗的介绍中,刻意采择并强调关于其“夫妇无别,对众可以狎抱,甚至宣淫”,“苟合私奔无禁”之类的说法,并置所谓“雁群有序,驼性知羞,英之淫风至此,谓为禽兽不如,予非刻薄之论”的评语,亦可有助印证。足见若辈对当时制造祸乱者的敏感的认知点之所在,显出有过分渲染此点而相对地冲淡了侵略者其他多方面恶举的倾向,这当然不能有助于对侵略者从本质上予以深刻认识,仅就表象而言也不无片面之嫌。而像对洋人的这种印象在当时的国人中决非个别,特别是这类话题的传闻,在民间社会中形成相当普遍的一种舆论(这从持续不衰的反洋教传闻中可得到进一步印证)。文化偏执心理因素显然在这中间起着直接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纲常名教的伦理观念,对妇女“贞节”是一种压迫性、奴役性的畸形注重,而此种意识,晚清时期不论是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是平民百姓来说,都是沦肌浃髓的,能够脱出此彀而树立新观念者应该说是凤毛麟角。对大多国人来说,仍然本能地在这方面具有卫道的特别敏感性,这种心理的促使,应该是有关舆论夸张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此外,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下述因素的确值得注意:当时出自士大夫笔下对洋人洋教所谓“乱伦”的描绘,除了反映作者“比一般老百姓更执著于纲常礼教而憎恶西方的人权平等、男女平等的观念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看成是封建士大夫自己最隐秘的那一部分内心活动的折射”,“封建正统文化造就了士大夫复杂的双重人格”,“口头上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想人格,而内心却无法排解潜意识中的人欲冲动和好奇”,他们绘声绘色地渲染教会“乱伦”,“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反映了宣传者自身那种被纲常名教压抑和封闭在心灵深处的本能欲望,也是封建伦理掩盖着的男性对女性野蛮支配欲的折光”。这的确是很有道理的。
文化偏执心理对社会传闻生发的影响尚不止于这些,它更体现在有关中西文化事物接触冲撞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每个典型场次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时,总是有着醒目的反映。要么把标志西方“长技”的器物指斥为不屑一顾的“奇技淫巧”,将其“政教”归结为不值不谈的“蛮邦之俗”;要么把西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寻根到华夏吾土,执拗于不是文化引进策略上的而是由衷而发的“西物中源”、“西学中源”说。而无论哪种表现的文化偏执,都衍生出诸多奇奇怪怪的传闻话题。比较起来,像“西物中源”、“西学中源”说似乎有着较深的学理基础,其实,即使在民间这种意识也可本能地生发。那篇产生于鸦片战争期间的粤民“谕英夷檄”中,就有这样的宣示:“汝虽(有)大呢羽毛,非我湖丝焉能织就?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不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汝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汝除此三物更有何能?我天朝平素仁慈,不忍制造此等毒物,伤害汝等。如果狠心制造,何难不诛尽汝等畜类”?激烈的民族义愤情绪当中,岂不也夹杂着浓重的文化偏执心理因素?这反映在对有关信息认知上的迷误自然可能助长有关传闻的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