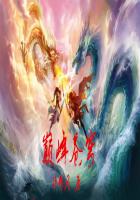四、作息定时习惯的形成
与星期休息制度相关的,还有做事定时与作息区分的习惯与观念。即平日劳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区分及做事定时观念。以往人们的农业生产及家庭手工业生产,都是个人或家庭成员的私人化活动,依自然昼夜及农时季节等进行活动,不需要精确的时间来区分劳作和休闲,一切时间完全由个人按实际情况而自行安排。人们也缺乏活动定时的习惯和观念,时间区分界线模糊,以相当于两小时的“时辰”作为基本时间划分单位,在实际生活中则用人们最熟悉并易于掌握的“一顿饭工夫”、“一袋烟工夫”、“一炷香工夫”等。如果需要多人约定时间集会等,也以诸如“饭后”、“午后”、“掌灯时”等模糊的时间概念。人们的时间概念模糊,作息活动时间也分界不清,作息起居,基本上是依自己情况自行掌握的自然状态。城市生活也基本如此,商家的营业也往往在昼夜自然节奏之内,依商家的勤惰和需要而营业,开门营业或闭门打烊一般并不定时。人们的活动也往往在昼夜自然调节之下,比较随意而缓慢。因而人们没有精确的劳作与休闲时间的区分观念,没有精确定时地安排活动的习惯,也不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
开口通商以后,最早是通商城市的人们看到西人作息定时的习惯,与我国作息不分的习惯不同。西人做事定时,注重效率,集中精力于一事,讲求效率的勤谨习惯,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定时与注重效率的重要。然而,直至19世纪末,虽然在通商城市里西人洋行、事业实行定时作息制度的影响下,那些在西人事业中做事的人,已经习惯了作息定时的生活,人们也已经开始认识到作息定时习惯的好处。在通商城市的一些与外贸相关的商业行业,由于受到西人洋行定时习惯的影响,时间观念也有所增强。但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商业、事业,还仍然沿袭着作息不定、自由自主的传统习惯。至于通商城市以外的广大城乡,人们的生活作息更是沿袭传统习惯而少有变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各地大城市工商业及新式事业开始普遍发展,人们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增多,节奏加快,商务接洽、车船开行、商品运送交接、工厂做工、社会事务等群体协作性活动增多,都需要更精确固定的时间。人们社会交往和互动增多,活动的时间安排更趋精密与短促,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公共性增强,需要众人以共同的时间节奏来协调。同时,照明工具进步使昼夜活动界线淡化,人们的活动不再严格受着昼夜及农时的限制,可以比较自由地安排时间,而不同的活动如劳作、社交与休闲等需要一定的时间区隔和安排。城市生活的这些变化,使以往劳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不加区分,以及人们各自活动时间不定的活动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及公共生活的需要。人们的劳作时间与休闲时间需要加以区别,并使众人的活动时间和节奏尽量一致,以便于统一步调,进行公共活动。特别是一些群体性的活动需要人们一起集合进行,更需要精确的时间限定。如学校上课,每个班级有数十人需要有确定的集合时间;商业生活节奏加快,需要更精确的商品交接与交易时间;社交活动增多,也需要更精确的时间约定以会合多人;戏园演戏,需要有确定的演出时间以便于众多观众按时到达等等。总之,城市生活公共性的增强,人们活动内容的增多和可支配时间的延长等因素,都促使人们需要更精确地安排时间。钟表的普及,使人们有了可以精确掌握时间的工具。这些都促使城市人们的活动趋向定时化,作息时间趋向区隔化、同步化。
正是适应这种城市生活的需要,清末以后,首先是新式学校开始实行课程定时制度,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须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后来在学习西方、移风易俗风气的影响及教育界的示范下,一些文人团体聚会,也规定集散时间,以示革新风俗,节省时间。时人有记云:“晚近士大夫,颇知仿效西法,其团体之治事也,有定时,以某时始,以某时终。”如1906年《大公报》刊载某一阅报处和说报所事务的社会团体制定的会议规则,其中便有专条关于会议定时的规定。规定会议于下午一时开始,参加者需准时出席:“来会者订于一钟点到齐,如届时不到,恕不多候。”还对定时散会作了限定:“来会者须俟四钟一齐散,倘随便来去,恐一切应研究之事难竟,其诸如有要事,请预先声明。”做事定时的新风俗首先开始在知识阶层中流行开来。
此外社会上一些企业、事业也开始仿行工作定时制度。如天津就有华人工商企业仿效西人企业而工作定时,有记云:“光绪中叶,……天津某财团之治事,效法西人,有定时,职员晨集暮散,迟到早退者曰旷,竟日之治事为七小时,是为法定时刻,在此时内,不得治己事。”但中国企业、事业效法西俗进行工作定时管理,在这时候还不多见,人们以传统习惯衡之,认为这种工作定时的管理制度对人束缚太过刻板,这种管理方式被人们讥笑为是“成人自侪于儿童”,把工作定时及区分工作与私事时间的管理制度,认为是把成人当儿童一样管着。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工作定时的管理制度还抱有相当的成见,人们的习惯和观念还难以很快转变过来。虽然清末以后,一些官署、学校、事业等相继实行定时工作制度,但人们一时还难以适应,工作时间往往仍然沿行着作息不分、公私事不分的习惯。
千百年来的农业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于缓慢从容的做事节奏,习惯于作息不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习惯于劳作时也偷闲休息的悠然从容,习惯于办公事时也兼顾私事的实惠乐趣,这种充满情趣、顺乎天然的生活习惯,使人们感觉舒适愉悦,而不习惯西人把做事和休息时间、办公与私事时间截然分开的生硬刻板的作息方式,甚至认为西人作息定时方式,将大块时间划定为个人休息及处理私事,因而是浪费时间、耽误正事,不如中国人以更多的时间来做事,不致耗费时日。但是,随着人们对西人情况的了解,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人在中西习惯比较下,对于中国传统作息习惯开始反省。如当时有识者指出:“西人办事,功课之密、规则之勤,胜我国几百十倍。而我国人乃误认,反以为逸于我。辄曰:‘若西人治事,但须每日上午几点钟至几钟,下午几点钟至几钟,而礼拜日悉停工。是其赴工之外,余皆归自用,较之我国逸多矣。’殊不知彼所谓几点钟至几点钟,此实在到工之时刻,而到工时又极辛苦。……且各国凡办公之地,为事皆极烦冗,诸人运笔如飞尚恐不及,非若吾国挽近,虽定入署时刻而实无事可作,咸相聚谈笑或辫发剃头,甚至任售什物者入,诸司员恣意看古董字画或珠宝也。”
清末民初以后,由学界、政界开始,后来所有公共设施、工商企业等也都逐渐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虽然作息时间不分、公私事务不分是中国人千百年沿袭的传统习惯,与中国人知命乐生的人生观相表里,并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但是,作息时间区分,公私事务区分,是近代工商业生活所需要的时间管理模式,人们也开始逐渐适应和习惯。
随着工作定时制度的普遍实行,人们也开始产生对于个人休息时间的权利意识。民国以后,政府机关、学校、公共事业等,仿效西方国家的一般通行制度,基本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而以往一直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工人,也开始仿效西方国家的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有更多休息和自己支配的时间。如民间对于民国制定的“五一劳动节”的理解,就是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人们对此也给予理解。如福建古田地方志中就对“五一劳动节”作注释道:“工人要求解放,每日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睡眠,均劳逸也。”随着社会的变动,工作定时制度的推行,人们已经把个人拥有休息时间作为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而捍卫,即使是下层劳动者也开始起而争取了。定时工作,保证休息时间,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休息权成为合法与正当的个人权利,至此,中国人的作息习惯和作息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结语】
由以上对晚清至民初时期城市“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形成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认识:第一,开口通商后,首先从通商城市开始,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由休闲娱乐业兴旺而出现市民日常化、大众化的“公共休闲”兴起,并以夜生活兴旺、星期休息制度及作息定时习惯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相应的市民参与公共活动的“公共时间”。直至清末民初时期,伴随着全国大中城市工商业、新市政的发展,这种市民大众化的“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也扩展到了全国大中城市,成为引导市民休闲生活的主导趋向。
第二,这一时期城市市民“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的形成,是以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市民人口增多、市民生活商业化发展,及交通、照明等技术的进步为基础的,亦即以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为前提,以这种发展引起人们生活方式、休闲方式的变化为契机,是市民生活城市化、社会化、公共化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第三,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市民“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的形成,成为城市市民生活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有了大众化的“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才为民间社团、学会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为较大范围及经常性的公众之间信息、语言、思想、文化、情趣等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因而使得这一时期民间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涌起了一股股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重重波浪,形成了公共社会活动的高潮,创造了这一时期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面。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独立自由地参与公共活动,思想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激发着观念的激烈碰撞和新思潮的勃兴,形成日益趋同的思想变革节奏和价值取向,成为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正是近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
[作者简介: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