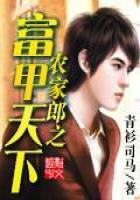电影艺术理论的探索和论争也是这一时期的热点。以白景晟发表于1979年的《丢掉戏剧的拐杖》为开端的关于电影的“戏剧性”的论争,和稍后的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论战,尽管都只是停留在传统的电影观念层面而且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论争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戏剧式”电影等旧观念的动摇,表明了曾一度成为政治附庸甚至工具的中国电影正在走向艺术的自觉,开始了对电影自身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的思考和探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在关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表述中,张起了一面影响了整个新时期电影发展的艺术旗帜——巴赞的“纪实美学”。
如前所述,对于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者们来说,现实主义的探索和发展是他们接受一切新理论、新手段的前提和标准。所以他们对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纪实理论的接受和使用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功利性的“误读”:他们所倡导的,与其说是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不如说是他们从巴赞理论中发现的写实技巧——长镜头和场面调度。他们关注的不是照相式的“物质现实的复原”,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把握和再现。但这种误读实际上又是一种历史的策略,一种“深刻的片面”。正是在如何达到银幕具象的真实性这一点上,他们找到了巴赞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之间的契合点。所以才会发生“误读”,所以他们才会将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纪实美学更多地看做是一种纪实的技巧论。
对纪实美学的接受和使用,形成了一种如郑洞天所说的“中国式的纪实美学”。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纪实为技巧和外观,以现实主义为其内核的艺术观。银幕具象的虚假和缺乏生活实感从来都是中国电影腾飞之心弥盛却又一直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中国式的纪实美学”从现实主义的“写真实”原则出发,将纪实性从作为内核的美学原则转向作为外在的视觉风格。注重影像的生活实感,要求影片通过“真正生活化的场景和音响,通过光、声、表演和蒙太奇语言再现出使观众完全相信的实际生活”。
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形成了一股“纪实电影”的热潮。《邻居》(1981年,郑洞天、徐谷明导演)、《沙鸥》(1981年,张暖忻导演)、《都市里的村庄》(1982年,滕文骥导演)、《见习律师》(1982年,韩小磊编导)、《逆光》(1982年,丁荫楠导演)、《大桥下面》(1983年,白沉导演)、《乡音》(1983年,胡炳榴导演)、《人到中年》(1982年,王启民、孙羽导演)、《青春祭》(1985年,张暖忻导演)、《鸳鸯楼》(1987年,郑洞天导演)等都是这一热潮的产物。这些影片中,既有《邻居》这样以准确、细腻地展示现实生活图画为其特征的作品,也有像《沙鸥》、《青春祭》这样将纪实和写意融为一体的影片。但创作者们都刻意追求电影反映生活时的真实性和影片的“生活气息”。他们通过大量的实景和外景拍摄;通过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和生活化的表演;通过长镜头、运动摄影、自然光效、同期录音和场面调度等手段,使银幕影像充满了呼之欲出的生活实感。让观众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拥挤不堪的筒子楼、杂乱的四合院、低矮的棚户区,看到了自己起居、劳作和生活的种种情形。这些初看似乎并不完美而且显得杂芜、不干净的画面恰恰有效地保证了影片再现生活时的完整和真实。
但“纪实电影”并非以纪实为全部目的,停留在对生活原始状态的记录上。对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的反映才是其最终目标。《邻居》通过当时极为敏感的住房问题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都市里的村庄》在自然丰富的生活情境的展示中,塑造了丁小亚这个性格复杂、有典型性的年青女劳模形象;《鸳鸯楼》则在六户普通人家一个下午和晚上的生活的“尽可能真切的记录”中,反映了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际关系和心理结构的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封闭与开放,欲念与现实等种种矛盾的重新组合与交织”。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反思电影”和“娱乐片”的兴起,“纪实电影”声势渐弱,但纪实美学的影响却依然持续。纪实性风格和那种将各种表面上并无紧密戏剧关联的生活事件组织为一个有机整体,多层次、多角度、开放式地再现生活的“散点式”电影结构方法都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电影创作。及至新世纪,在《小武》(1998年,贾樟柯导演)、《站台》(2000年,贾樟柯导演)、《任逍遥》(2002年,贾樟柯导演),《安阳婴儿》(2001年,王超导演)、《江城夏日》(2006年,王超导演)、《盲井》(2003年,李扬导演)等影片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影响和它的发展。
继纪实美学引进之后,对电影影像本体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关注热点。研究者和创作者们对电影造型、电影声音、声画结合以及电影语言特性等各方面的深入探讨,已不仅局限于实践性的技巧研究,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本体层次上的电影特性研究。理论的发展为创作实践的突破做了准备。
和“纪实电影”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和客观再现不同,“文化反思”电影所强调的,是艺术家主体意识的强烈渗透,是对生活的独特审视和深层的哲理思考。这也要求它寻求新的电影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技巧上的变化。
从《一个和八个》开始,《黄土地》、《海滩》、《猎场札橵》、《黑炮事件》等一批影片以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对电影形式的极端追求,对传统叙事方法的断然拒绝以及不规则、不完整的构图和压抑的影调、雕塑般的造型等表象后面对影像本体的大胆变革强烈地震撼了中国影坛。这些影片中的影像既是高度纪实的,同时又是高度表现性的。它们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其自身也已经成为电影思维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影片的创作者电影思维的彻底性,才使他们获得了艺术上的完整性”。《黄土地》中浑厚涌流的黄河,塞满了画框的黄土地,农民身上大红大黑的色彩以及凝滞不动的镜头和构图,都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重负和艰难的命运。而《黑炮事件》里全白的会议室,占满了整面墙壁的大钟,则惊人地显示着官僚主义的僵化、空洞和封建意识积淀的可怕。
这些影片对影像造型表现的开拓,显示了一种运用电影影像的多种可能性来把握和表现生活的艺术思维方式。它对传统的“影戏”观念的突破标志着一种新的“影像”观念的出现,表明新时期现实主义电影对其自身艺术规律的探索已经深入到本体层面,而这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艺术自觉的重要收获。
三、开放中的迷失:“现实”与“现时”
在1976年后中国现实主义电影频繁而激烈的蜕变背后,仍然是政治、商业、艺术诸因素的博弈。而大众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改变就是这种博弈的具体表征。这其中,大众文化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
某种意义上,社会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包括了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主流政治文化,由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创造和掌控的精英文化,以及在前工业社会体现为民间文化,后来则体现为都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大众文化这三种文化并存的形态。
通常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精英文化常常与主流政治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左右社会发展趋势并“俯瞰”、“定位”或“改写”着大众文化。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都市和商业文化转变。这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改变了传统的民间文化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始终处于边缘地带的状况。它甚至控制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政治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
在中国,“大众”的所指似乎一直都处在不断的变换流动之中。在“五四”之前,它所指向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粗鄙愚昧的下层民众;在“五四”精英们的眼中,它是需要启蒙和唤醒的蒙昧国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是“庶民”、“平民”和“劳工”;再往后,它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而到了今天,它是相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市民百姓。
“大众”的语义变化实际上也体现在中国文艺的大众化诉求不断改变的内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