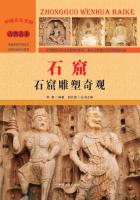考察1976年以后的所谓新时期电影,就不能不首先谈到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新时期的历史背景,是刚刚过去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它的现实背景,则是迄今仍在继续的,中国人民从“文革”废墟中复苏并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十年“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痛苦和伤害,它还带来了人们伤痛之后回首抚摸伤痕时的疑惑和探求,带来了全民族的对“文革”及至更远一些的历史的深刻反思。而改革开放后纷至沓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期的躁动不安,以及观念蜕变的痛苦过程等则构成了新时期另一面的总体文化氛围。新时期电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动一样,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也对这一时期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它的蜕变和走向。回头看去,我们甚至会惊讶于这种蜕变的频繁而激烈:几乎每过几年,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电影就会经历一次突围式的面貌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题材上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到“日常生活”,到“主旋律”的迅速变换,更体现在“现实主义精神”的从回归到深化,到开放式发展中的迷失。
一、从“伤痕”到“寻根”:回归中的偏离
从“文革”噩梦中走出来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在重新获得创作权利的狂喜之后,很快就痛苦地发现他们正身处于一种传统缺失的尴尬境地。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已经被彻底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僵化、教条的,极端政治功利性的“伪现实主义”。这种状况使得在1977至1978年的所谓“徘徊时期”里拍摄的《十月风云》(1977年,张一导演)、《大河奔流》(1978年,谢铁骊、陈怀皑导演)等揭批“四人帮”的影片在思想框架和艺术精神上仍然因袭着“伪现实主义”的僵化模式,成为对政治的机械反映。对刚刚结束的深重政治灾难的痛苦记忆和“徘徊时期”里电影创作在“伪现实主义”怪圈里的徘徊都使得新时期电影不得不挣脱“伪现实主义”的桎梏,去寻找新的出路。但这种寻找却又绝不可能是一次挣脱其现实政治职能的“突围”。每一个时代都要求自己的声音,新时期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电影仍将无可选择地承担起它的现实政治职能。于是人们回过头去,把目光投向了隔断在历史另一边的现实主义传统。恢复现实主义传统,恢复和坚持艺术中的真实性,成为新时期电影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无论对中国的社会政治还是文化艺术来说,1979年都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年头。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讨论后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的社会政治氛围,改革开放让人们看到的令人憧憬的将来,都使这一年成为一个努力挣脱过去而注目于现实,注目于未来的年代。身处这一年代的人们几乎是同时感受到了走出阴影的喜悦和挣脱过去的艰难。
正是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小花》(1979年,张铮、黄健中导演)、《苦恼人的笑》(1979年,杨延晋、邓一民导演)、《归心似箭》(1979年,李俊导演)、《从奴隶到将军》(1979年,王炎导演)等第一批“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影片。
在当时潮水般涌现的由“伤痕”而“政治反思”的文艺思潮中,影片《苦恼人的笑》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政治反思色彩。但我们发现,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电影创作者们的心理写照。在“文革”中,他们也和影片里的记者傅彬一样,想说出自己的声音而不能。但他们在新时期里终于得到了傅彬所没有的,说真话的权利。影片将对“四人帮”的批判集中在压制人民说真话这一点上,恰好表明了新时期的电影艺术家们在解脱禁锢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说真话,写真实。而直面现实人生,冷静地反思历史,观照现实,便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创作的影片里面,“革命历史题材”占了绝大部分。这至少表明了创作者们仍尚未真正彻底走出历史阴影。他们的镜头更多地对准了更为久远的革命战争年代而不是现实生活或是刚刚成为背景的文革。但在这些影片中已经显出了他们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冷静的现实批判精神。
这一时期,电影创作者们已经高高地擎起了他们的人道主义旗帜。在经历了一场反人性的历史浩劫之后,人道主义理想成为艺术家们“视野中一片朦胧而温暖的亮色”。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情、人性美更成为他们观照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准绳。在《小花》、《归心似箭》等影片中,创作者们并不像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那样将描写战争事件放在首位。他们“并不顾忌事件本身的完整性”而“依照人物感情发展的需要”来结构影片,以“突出影片的人情色彩”。在这些影片中,战争事件已经成为背景,而战争中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的个性则成为表现的重点。影片《归心似箭》“把爱情当做重点,在爱情上作文章”,在描写抗联战士魏得胜归队的过程中,浓墨重彩地集中表现了他在面对“生死关”、“金钱关”、“爱情关”时所显示出来的人情、人性的美。尤其是影片中爱情场景的细腻描绘,更表明了创作者闯“禁区”的胆识。《小花》是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的,但影片对换了原作中战争和感情的位置,将一部描写具体战斗过程的小说变成了一部动人的艺术抒情片。这一年的反思题材影片像《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1979年,腾文骥、吴天明导演)等也突破了“徘徊时期”电影图解政策,作政治结论的局限,以悲剧的色调刻画了在“文革”浩劫中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压抑和心理磨难。
如同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氛围中的杂色纷呈一样,这些影片也不可避免带有转折时期的烙印。在《小花》和《归心似箭》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出罩在英雄人物头顶的光环,而《苦恼人的笑》和《生活的颤音》对历史反思的最后支点也仍然是表层的政治批判。
进入1980年代后,正如钟惦棐所说,新时期电影开始“从浮泛转向深邃,从狭窄走向宽舒”。随着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也变得更加深入。如果说新时期电影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在最初只是简单地回复了1930至1940年代和解放初期电影的政治性、社会性价值取向,到1979年才逐渐转移到“人学”,开始注重人情、人性、注重人道主义精神的话,到1980年代,这种追求就更加明显和深入了。1980至1981年间创作的《巴山夜雨》(1980年,吴永刚、吴贻弓导演)、《天云山传奇》(1980年,谢晋导演)、《西安事变》(1981年,成荫导演)、《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年,张其、李亚林导演)等影片标志着新时期电影现实主义的真正确立。这些影片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对人情、人性美的呼唤和对历史,对现实的表层政治批判上,而是以更冷峻的笔调,更强烈的现实批判锋芒来解剖历史,还历史以真面目。《西安事变》以其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人化”地塑造了蒋介石的形象而令人耳目一新,《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影片则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影片,它们的批判锋芒直指某一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这些影片都以人伦关系为框架,通过对美的毁灭、人性磨难、人情的被压制等悲剧事件的表现,深刻地批判了现实社会中的反人性因素。
作为第一部将反思的视野从“文革”延伸至更远一些的反右时期的电影作品,《天云山传奇》并非一部“研究反右政策”的影片。导演谢晋并不着意于故事的政治性,着意于探讨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而是通过具体的艺术性——人物的曲折命运来体现一切。影片将“反右”斗争推到后景,注目于宋薇、罗群、冯晴岚和周瑜贞等人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遭遇和人们身上的美好情操。但透过这样的叙事表层,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影片的现实批判锋芒。创作者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非人现实所造成的悲剧的展示,正是对那一时期社会现实的猛烈批判。
新时期的电影创作者们,无论是谢晋这样的老导演,还是后起的中年或青年艺术家,他们都不仅仅是真诚地,而更是自觉地高扬人道主义旗帜,运用理性的批判武器去解剖历史,解剖社会,直面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批判者。谢晋说过:“我的作品是在力图刻画民族的悲剧性格中,给人以反思警世的作用。……面对人性的蒙羞,我不准备也不愿意掉转头去视而不见,更不对昨天的邪恶、丑陋采取宽容态度……”这也正是新时期反思题材影片的共同特征。
当人们将目光从过去转向现在,从历史的反思转向对前进中的现实生活的表现时,情况便复杂多了。这时,他们所面对的将不再仅仅是历史造成的悲剧,而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决定了电影创作者们必须将“再现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为创作的主要任务之一。真实反映新时期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变化是新时期现实题材影片的目标。
在表现现实生活时,艺术家们尽力摒弃“工农兵电影”和“文革”“伪现实主义电影”的粉饰生活,只写光明不写黑暗的弊端,批判一切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反动因素。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掩盖矛盾、粉饰现实并不能给人民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主张现实主义艺术要揭露矛盾、引起人们思考,帮助人们看到主宰生活的积极力量,看到生活发展的方向。
拍摄于1981年的《邻居》(郑洞天、徐谷明导演)敏锐地抓取了现实生活中十分敏感的住房问题,真实地展现了某大学房屋分配中的种种矛盾。影片的轰动一时表明了人民对这样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的渴求和欢迎。《邻居》出现后,随之而来的许多影片迅速地触及了各种现实问题。影片《人到中年》(1982年,王启民、孙羽导演)从较深的层次上提出了新时期中国无法回避的知识分子问题。影片的女主角陆文婷是一位兢兢业业、医术高超的眼科大夫。为了事业,她付出了一切——几乎包括生命。然而她的个人生活却是一场悲剧,她没有起码的经济收入和住房条件,热爱丈夫和儿子却又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们做点什么,甚至在事业上她也并非一帆风顺,评职称受阻挠,辛辛苦苦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陆文婷的悲剧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更多的造成她的悲剧的因素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影片对现实的悲剧的展示,显示了更为犀利的现实批判锋芒。
在“改革题材”的优秀影片中,新时期现实主义电影的现实批判精神也不断地走向深入和冷峻。影片《不该发生的故事》(1983年,张辉导演)讲述了农村改革中几个共产党员“没人要”的故事。《花园街5号》(1984年,姜树森、赵实导演)则记述了某城市中党的领导人更替时所发生的故事。这两部影片都直接触及了在改革开放中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矛盾。而影片《秋天里的春天》(1985年,白沉导演)另辟蹊径,描写了一个曾经由组织安排嫁给某市委书记的女人(周良蕙)在丈夫死于“文革”后,试图再嫁给在困难中与她相濡以沫的邮递员罗立平时又横遭“组织”干涉的遭遇,大胆地批判了党的肌体中的某些封建因素。
果戈理说过:“有这样的时候,你如果不把现实的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显示出来,你另外就无法使社会,甚至使整个世代的人去瞻望美好的事物;有这样的时候,如果不同时像白昼一样明白地给一切人指出道路,甚至根本就不应该讲到崇高的和美好的事物”。新时期电影创作中大批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甚至是揭露“阴暗面”,写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作品的出现,不仅表明了电影艺术家们主体意识的充分觉醒,也标志着新时期电影现实主义创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进入了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它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剧烈变化,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改变,从传统走向现代必然是一场艰难的蜕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旧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新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巨大差距,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使身处转型期的人们感到了巨大的失落和困惑。为了确立新的价值观,适应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人们纷纷回过头去,希望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个稳固的支点。这一时期,文学界率先发起一阵势不可挡的“寻根”热潮,开始了文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