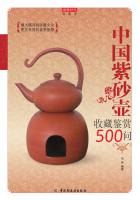二、光
电影中的影像通过光影变化形成,电影艺术实际上也是光影艺术。爱因汉姆认为:
物体的表象就被看成是物体本身固有的亮度值或色彩值与外部光源加于该物体的亮度值和色彩值互相混合之后,形成的混合物。
物体的表象是光线照射的结果,是不同光线照射物体使之获得亮度值和色彩值的综合。这是物体在现实时空中获得的表象。电影媒介的作用是纪录物体的表象,摄影师在操作摄影机时会运用一定的手段以获得理想的光影效果,所以,胶片上获得的物体和人像光影效果实际上是其自然效果和人的视野的综合,从而获得一种视像。摄影者在视像中溶入了主观的感觉、艺术语言和理念,从而导致视像携带电影作者的主观密码而成为一种艺术语言媒介。电影的物质媒介固化了客体的表象,同时也固化了主体的感觉。
爱因汉姆认为光线最大的意义在于把物体(其实也包括人)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而阴影不是光明的缺席,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物体给人视觉效果在于物体本身的形状和光线的照射,照射的作用使得物体具有更大的偶然性和变化。虽然他论述的是绘画规律,但是其揭示的美学原理在电影之中仍然适应,只是电影相对于绘画要复杂得多。电影作为光影艺术,电影照明的众多方式形成了丰富的电影语言,从而为电影作者按照内心的想象塑造电影形象。电影照明形成的形象成为一种主观性影像,这使得现实时空中的形象经过主观精神改造,成为一种精神形象。而且,布光、光线设计、光线方向、光线效果、薄膜照明、模拟照明、修饰性照明、形象性光线、戏剧性光线、光斑、剪影等成为电影形象的修辞方式,成为视觉语言的媒介。光线的影调和明暗效果是重要的情感语言,能准确描写人物的情绪状态。西方有句著名的熟语:上帝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里可以引申为:电影作者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电影摄影师是利用光线进行艺术创作的工匠。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摄影李屏宾充分地利用了淡黄色光线塑造了老北京的城市形象,烘托了电影怀旧、幽怨的情绪气氛。许小姐少年时代居住在老北平,北平的四合院、街道、邮差、风筝等还原了老北平的建筑和生活形态,而煤油灯这一古老的照明工具为电影提供了淡黄色的影调,这成为影片中重要的情感语言。作家房间内的摆设洋溢着浓浓的古典意味,木质书架、长椅、床透出淡淡的光泽,厚厚的书本排列得像城墙一样,而煤油灯淡黄色的灯光“像一个邀请”样烘托了少女敏感、单纯的心境。片中最后一个镜头是典型的回顾性镜头,煤油灯下的少女的脸洋溢着向往、期望、幸福,在一生的悲剧发生后此时煤油灯下的少女让人无限伤感和心碎。越南著名导演陈英雄的《青木瓜滋味》和《夏天的滋味》光线的运用成为影片重要的修辞方式。《青木瓜滋味》中少女仆人和少爷居住在木质建筑内,园内种植越南青木瓜藤,当切开青木瓜后,白色瓜籽和淡黄色瓜瓤亮着光泽,晶莹剔透。园内的阳光清净明朗,照亮了少年时代的少爷和女孩单纯美好的心境。光线给予电影一种诗歌般的气质和意境。《夏天的滋味》中越南阳光更加明朗,姐妹在光波闪亮的亚热带泉水的洗濯中窃窃私语。长发黑亮浓密,妹妹的头发在甩水的过程中弯曲盘旋,慢镜头中记录的是生命旺盛的青春。阳光下的村口,三三两两的牛群在怡然回刍,巨大的古木静静伫立,夏天的蝉不断嘶鸣,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明亮的阳光和澄洁的月光构建了梦境一样的审美四维空间,洋溢着诗意生活气氛。
三、色彩与形状
人对色彩的经验和对情感的经验有相似之处,色彩是情感的外延。色彩产生情感体验,形式对应理智判断。色彩诉诸感觉,形式诉诸知觉。这与人类的生存经验和生理密切相关,人类生存环境中充满了色彩和形式,各种各样的色彩和形式给人带来种种生存体验,快感、痛感、安宁感、迷失感、困惑感、愉悦感、崇高感、悲壮感、优美感,等等。生存体验和事物的色彩形式建立一种潜意识的关联,看到有关的色彩和形式会自然产生相应的感知觉和体验,相反,有关的感知觉可以自然在大脑中想象出与生活经验相似的色彩和形式,也就是形象。两者之间有直接对应的关系。人在睡眠状态,如果把脚露在被子外,很容易做梦,在冰天雪地里游走。梦境此时也是一种深层次潜意识的想象,与现实中人的生存境况也有种种曲折隐含的关联,所以中国有句俗语: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也是建构形象和形象运动世界的过程,这与电影或形象艺术非常相似。在一定意义上,现实生存世界的生存规律是电影的语法,其深层次地决定了电影中形象的建构和形象的运动。
影像这一名词实际上是黑白电影时代的遗留,当时电影只有黑白两色,银幕上的人物和物体的形象是黑色/灰色,电影形象称之为影像。在彩色电影时代,影像颜色由黑白变为彩色,影像实际上变成了“彩像”,色彩成为电影形象的现实,也成为电影作者的艺术语言。现实时空中色彩和形状在生存境况中与人的感觉、情绪、理智建立种种关联,从而使得色彩和形状与人的精神产生对应关系,形成类似符号的能指与(含蓄)所指的关系。现实生存境况中形成的表达关系在电影不同的语境中会得以表现,现实时空的生存逻辑是电影语言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实生存逻辑是电影视听语言的语法。比如说红色,在现实生活中红色的东西有血液、果汁、服装、蛇冠、旗帜、太阳、红眼病等,在不同的生存境况中人会获得不同的感觉、体验和认知,从而赋予红色不同的含义。血液的红可以意味着活力,也可以意味着恐怖;服装的红鲜艳,令人悦目;蛇冠的红令人害怕意味着惊恐;太阳的红灿烂辉煌令人景仰。而这种种意义被置入红色后成为其在一定的语言文化系统中相对固定的意义内蕴,红色成为形象能指,意义成为所指。在相似语境中同一语言文化系统的人会对红色作出相似的感觉、体验和认知。在具体的生存时空中会形成快感、痛感等感觉。在宏大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可以形成象征意义,红色可以象征革命,也可以象征恐怖主义。电影的视听语言正是利用人类感知的相似性进行审美四维空间的建构,从而使观众获得相似的感觉、体验和认知理解。这也为电影作者和电影观众之间建立传播的桥梁。同时,由于人的生存境况、文化结构和审美趣味的不一致,观众接受时的感觉、体验和理解会发生“偏差”,不同的“偏差”会赋予色彩和形状不同的意义,这符合接受规律。所谓意义与体验是同与不同的具体存在。
在电影中,色彩和形状的语言围绕着人的感觉、知觉、理解、体验等精神存在建构,后者是电影语言的旨归和目的。摄影师在拍摄之前会根据剧本构思和导演意图设计色彩总谱、色彩基调,人、场面的色彩造型、场面转换或镜头转换的色彩转换和色彩结构等从而使得电影具有总体色彩效果,并奠定电影的情绪基调和视觉氛围。色彩、色调和影调可以形成一种情感语言诉诸人的无意识,使观众得到审美体验。色彩的明度、饱和度、冷暖、重量等都是针对人的感觉进行测量和标准设计,意味着色彩的电影参数以人为核心建立,色彩直接与人的感觉建立关联,一定的色彩意味着一定的感觉。并因此在具体的情境之中产生意义。
《红高粱》中张艺谋把红的文化元素发挥到极致,高粱红、太阳红、土地红、棉袄红、女儿红、血红、夕阳红等在影片中形成红的审美体系,《红高粱》的审美四维空间是红色的空间。红形成的色彩体系强烈刺激观众的视觉感官,构成强烈的生命力象征,成为电影的形象核心魅力,震撼了观众的心灵。《蓝》中影片的色彩基调是蓝,电影名字与电影色调一致,电影中出现大量的蓝色物体和蓝色的色调,女主角的衣装、游泳池的池水、天空等与人物的忧郁气质吻合,奠定了电影把人物从绝望中的进行拯救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气氛。《白》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白色,女角的白色婚纱、北欧波兰的白雪、墙壁、蜡烛等,《白》叙述的是身体拯救的故事,男主角的不幸遭际和女主角的欲望与白色有着内在的一致,白色的凄惶与白色的欲望,片尾男主角在白雪中远望着女主角时,女主角打出的手语——“下次我们再来一次”,女主角的欲望在寒冷的北欧苏醒,夫妻关系得以还原。白色意味纯洁,或者欲望,或者平等,或者凄惶,色彩与情节相一致。《红》中出现的巨幅广告背景红色、围巾红等,主色调不像《蓝》和《白》那样明显,但是全片的主题是博爱精神的拯救和苏醒,孤苦的老人在女主角的拯救下重燃爱心,主题和主色彩的情绪意味一致,红色有效地烘托了博爱的拯救主题。
形状在电影中主要是人和物的形状,主要诉诸观众的知觉。形状被识别其实与符号被辨认类似。甚至反过来,符号也是一种形状识别。电影中物体的识别和现实生活中的物体识别极其相似,电影中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记录,现实时空中建立的识别在电影中延续存在。观众看见了形状,识别了形状,由此眼睛被置于电影审美四维空间的现场,成为电影叙事如影随形的旁观者。这是对单个人与物的观看和识别。同时,观众还有对形状组合的观看和识别。电影空间中的人群会形成一定的关系状态,如队形、群形。物体也会形成一定的形状关系,并且,人和物之间也会形成形状关系,从而形成不同的美感。在《奥林匹亚》中运动员的队形、运动员和体育设施等构建了具有独特美感的画面。电影中的形状具有独特的形式美,在审美四维空间中,物体和人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人形和环境中的物体形状产生形式美感。在电影视听语言中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