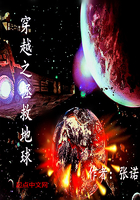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钱的意思很清楚,“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后来鲁迅、周作人兄弟表示不必声明不谈政治,陈独秀则对于声明“不谈政治”和北京同人另起炉灶办杂志非常生气。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又与同人商量,放弃“宣言不谈政治”(但可换用陈独秀的说法,即“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不再另起炉灶办杂志(理由是“我们这一班人绝不够办两个杂志”),提出“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征询同人意见的结果: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之均赞成(陶、王还坚持不得已可停办《新青年》,但不宜分为两个杂志,以免破坏精神团结);李大钊开始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倾向于“从前的第一种办法”(《新青年》和北京同人各办各的),但也不反对《新青年》编辑部移回北京,后来又只同意移回北京;周作人赞成移回北京,但也觉得即便分裂,出现两个杂志也无所谓;鲁迅和周作人的态度基本一致,但不过分看重《新青年》“这一个名目”;钱玄同表示:他“和周氏兄弟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勉强在一起维持,有“统一思想之嫌”,“最丢脸”,“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胡适在这些同人中的周旋,充分说明他当时对启蒙的重视,他在个别词句上虽然有所变通,但在启蒙的大原则上却没有动摇。
胡适由决计不谈政治,到创办《努力周报》论政,的确是当时中国恶劣政治逼迫的。也就是说,坏政治使得胡适不能再回避了,因为他立志“不谈政治”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积重难返,谈政治难以遽然奏效;他暂时“不谈政治”的归宿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恶政治。所以当政治愈加恶化的时候,胡适也就会逐渐向“谈政治”靠拢,而恶政治到了无法忍受之际,胡适肯定是要冲上“谈政治”第一线的。诚如胡适1947年在一次演说中所说的:“我民国六年回国,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谈政治,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政治性的杂志。
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想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促使胡适公开谈政治,除了恶政治的现实外,另一个因素就是胡适站在实验主义立场上,认为中国思想界对付黑暗政治现实的武器太乏力了。胡适说,他本来在《每周评论》被查禁后因为繁忙和身体不好,是不想重新出山来做政论文章的,但“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胡适认为,“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本来恶劣的政治是应该有人来过问的,但是令他不满意的是人们不是把热情和精力放在批评军阀政府上,而是热衷于高谈舶来的主义,甚至把刊物上应有的针对时事的栏目如社论、时评都取消了,代之以不相关的专门副刊。胡适为此不能接受。其实胡适不懂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思潮的兴趣陡增,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感到就政治谈政治于事无补,不如打开思路去探寻有助于解开坏政治“死结”的域外的理论和方法。显然,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是存在偏见的。
二、丁文江的政治情结
促使胡适重整旗鼓办报写政论文章的诸因素中,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的影响大概也很重要。丁文江虽然搞的是自然科学,但对政治一向热衷,并且还有自己的一套主见。他认为黑暗的中国政治根本不是靠“中国的文艺复兴”所能改变的,他与胡适能敞开心扉交换各自对中国政治改造的看法,因而会对胡适产生影响。胡适在丁文江不幸去世后为他作了一篇较为详尽的传记(写成于1956年),在传记中胡适谈到了丁的主张及对自己的影响:
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其中有几句话差不多是专指我说的:“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在朋友的谈话中,他常说的是:“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丁文江是我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我国地质学发展史及地质调查史上具有无人可以替代的重要地位。他1911年从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回国,直到1936年初因煤气中毒逝世,在20多年的时间里,“第一个时期是主持北京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个时期是主持北票煤矿公司,第三个时期是主持中央研究院。”他先后在三个单位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总经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尽管他的专业是自然科学,但他却几乎是与生俱来地对现实政治感兴趣,他不满足于当一名热衷政治的旁观者,而且还要积极地去论说政治、干预政治。丁文江的好友董显光在丁文江逝世后回忆说,1922~1923年间,他和丁文江同在天津工作,并同住一个寓所的前后间,董在华北水利委员会服务,并兼任《密勒氏评论报》驻华副主笔,丁文江主持北票煤矿公司的技术工作,通过工作之余的闲聊,他对丁文江的学识和兴趣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丁文江给董的印象除了“他中文、英文、德文的造诣都极深,而治学的范围又极广,因之,天文地理,无不通晓”外,就是他对政治的兴趣:他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记得那时他正在从事一本关于过去五百年中国宰相的籍贯考据的著作。他所获得的结论是中国宰相出生于南方的占最多数,而其中尤以籍隶江苏省北部的为多。
当时我认为他既是一个地质学者,何必以有用的时间来做这种无关紧要的研究,因此有一天我便劝他不如利用空余时间去找金矿银矿。但他却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看来,丁文江和大多数自然科技工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科技、实业救国论者,而是一个有着干政激情、问政情结的资深科学家。蒋廷黻在丁文江逝世后也曾回忆说,大约是在1925年冬季的一次天津的宴会上,他初识了丁文江。丁文江作为地质专家所讲的煤矿事情,蒋廷黻并不感兴趣,相反,丁文江对政治现实的深入了解倒是给蒋廷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大家谈到内战,由内战谈到当时的军阀和军队。关于这些题目,在君的知识简直是骇人的。军阀个人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的高低、教育的程度、生活的习惯、彼此的关系、部队的数量、素质、配备等,在君几乎是无不知的。就是当时日本的专业军事密探都不能比在君知道的更多或更正确。丁文江热衷干预政治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他曾经同蒋廷黻等人所讲过的:当政的军阀中的许多人是爱国的,至少是想爱国的,有些实在是高度爱国的。许多军人具有绝好的天资,可惜是没有受过近代式的教育。
如果军阀也受过好的教育,他们也会对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从保定回来,带来边守靖、吴景濂、张绍曾等捣鬼的电文十二件,我把他们编成一篇,在《努力》上发表。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也许,按照这个逻辑,丁文江想通过办报来影响军阀,让他们把手中的权力用得更好些。丁的一句口头禅“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对知识分子单纯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不能奏效的担心,他设计的替代办法就是谈政治、干预政治,甚至以此唤起军阀的“爱国心”,从而改善政治。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实的政治越来越坏,丁文江觉得如果国民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必然就会有更坏的政治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努力周报》的创办,很大程度上也是丁文江竭力主张的结果,其情形如胡适作《丁文江的传记》所言:“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最可以表现出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
……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
在君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般朋友们的议论。其后的历史证实了丁文江的担心不全为多余。在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奉系军阀有时表现得更野蛮、贪婪和无耻,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的破坏也更大。丁文江论政的目的也就是要尽可能促成政局朝不那么坏的方向发展,避免他认为最坏的奉系军阀主政局面的出现。
丁文江致信胡适,表达出不甘平庸人生的情怀。1922年11月劝胡适注意休息,甚至认为只有选择出国一次才能获得真正的修养,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他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我以为你非出洋一次不能真正休息,千万不要固执!我决不是怕事的人,也不是代朋友怕事的人。如果你身体强健,你要走,我还要责备你,因为奋斗是我们的责任,冒险是我们的义务。但是以你这种身体,再有了意外的刺激,你一定要完全牺牲了的。这是万不值得的。”《努力周报》上丁文江的文章许多用的是“宗淹”笔名,据胡适说,丁的本意“那当然是表示他崇敬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后来《努力周报》因故暂停出版,继之又决定延期复刊,而丁文江似乎与多数心灰意冷的同人不同,他办报热情不减,似乎还想继续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