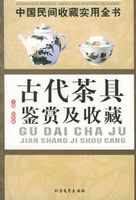其次,隐形的英雄形象。谍战剧中的英雄精神多是通过英雄人物恪守崇高使命而浓缩成的一种民族魂,他们不同于战场上一呼百应、叱咤风云的英雄将领,却常常不被人关注甚至被人误解。正如《暗算》开篇旁白:“他们没有声音,只有行动;他们没有日常,只有非常;他们没有眼泪,只有悲伤;他们没有传记,只有传说。”如果说军事剧中的英雄是张扬化的形象,那么谍战剧中的英雄则是“隐形的英雄”。如《一双绣花鞋》中林南轩是我军卧底于敌方的谍报人员,但一直被叶大龙误解并对其实施抓捕,当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丁部长也壮烈牺牲后,林南轩仍然坚守信仰并坚持战斗;《梅花档案》中的龙飞独自打入特务组织,为此一次次延误和未婚妻南云的婚礼,最终导致二人决裂;《誓言无声》中许子风清楚地知道自己女儿在和特务谈恋爱,但自己所做的除了以封建家长的姿态阻挠以外,为了国家机密却不能言说理由;《潜伏》中余则成深爱着左蓝,但为了长期潜伏,却不得不与左蓝假装陌路,甚至左蓝牺牲了,也不敢暴露悲痛的情感。后来,当余则成爱上他生命中第二个女人翠平后,却又不得不为了潜伏使命,眼睁睁地与心爱的人擦肩而过。在这些情感的漩涡中,他们首先是国家、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其次才是普通人。这种充满悲伤却又不能张扬的巨大内心痛苦恰恰是谍战剧最引人关注的地方,同时,也是最能滋养人心、慰藉人心的灵丹妙药。
二、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的存在意义
21世纪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英雄精神理念的复归,这种复归是整个社会审美理想裂变时期的产物,是处于精神焦虑状态的受众的集体召唤。
英雄主义曾经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运动和斗争中,英雄主义,确切地说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理念和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实际上,“英雄主义情结”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母题,凝练着人们对英雄的渴慕和崇拜,具有普世意义。古希腊神话中捍卫正义、崇尚自由的阿克琉斯、赫拉克勒斯、宙斯等众神形象无不是古今中外人们共同崇尚的英雄人物原型。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崇尚英雄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只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宣传的需要,一度无限扩张了这一社会需求。“文革”时期,民众的“英雄主义情结”再度遭到强化和扭曲,“样板戏”的审美标准禁锢了大众对英雄的审美需求,英雄主义理念也一度被歪曲。但星移斗转、时代更迭,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和内涵却始终没有变,变化的只是时代风潮中人物形象塑造方式和观众的审美趣味。
到了新世纪,从谍战剧的发展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英雄精神才开始真正复归,而这种复归首先是建构在消解空泛“英雄神话”基础之上的。上世纪末,社会审美理想发生巨变,人文关怀、英雄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净土,虽然否定传统带来的快意与新鲜事物带来的刺激大大填补了民众内心的空虚,但这种刺激随着市场化各种矛盾的纠结而迅速消退。“上帝死了”,“英雄没了”,“人也空了”,世俗的芸芸众生,在周而复始的琐碎生活中,又开始踏上了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与信念依托之路。谍战剧中的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恰逢其时地来到了民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是在整个社会文化心理趋于焦虑浮躁的时候,在基于观众感官刺激和消费所生产的无价值、无品位、无内涵的东西甚嚣尘上的时候,让观众重新找到了前行的路标。
三、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的塑造
伴随反特片程式化叙事模式的还有人物形象脸谱化、人物性格扁平化的弊端,致使英雄人物一出场,无须开口,观众就能从他的穿着打扮、举止形态甚至音乐背景知道他是位“英雄”,待到他开口,更是神圣无比,高立云端,让人顶礼膜拜。这种“‘扁形人物’是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观众的审美想象赋予了扁平人物合理的身份和性格,单一的英雄人物形象就易于被观众接受,但引申到现今谍战剧人物形象塑造,即便是普通的“圆形人物”也未必能得到观众的认同,观众个性化的审美趣味需要编导者弥补反特片在人性刻画方面的失当,以开掘出人物独特的个性特征,让人觉得可信,这应该就是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最根本要求。
《潜伏》在人物个性化塑造方面就提供了这样的成功范例。该剧除了余则成和翠平,首次塑造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吴站长”:他善于处理人情世故,会耍政治手腕,对人生和时局看得透彻清明;他能利用下属间的斗争来取得一种平衡,同时还能巧妙地为自己敛财。然而,他给观众的感觉却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的狡诈中含着宽厚,精明中含着糊涂,这么一个立体的“吴站长”自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黎明之前》无疑是2010年最受观众欢迎的谍战剧,其重要原因就是塑造了鲜活而真实的“这一个”。刘新杰因为党的需要,在敌人内部一直“沉睡”了十年。人非草木,当他用十年时光和身边那些本该是敌人的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哪怕这情谊是一种革命需要,谁又能说其中不包含半点真情呢?十年,即使是块石头也被焐热了,何况是人呢?所以,当他被“唤醒”时,有一种说不出的迷失感。与智商和定力都几乎堪称完美的余则成相比,刘新杰就显得嫩多了。第一场戏里,他就因为自己的鲁莽而差点暴露身份。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才使这个人物显得更真实可爱。剧中刘新杰和国民党情报局长谭忠恕的情感处理也具有可信度,他俩从小一起长大,谭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善待刘新杰,同时他们又有同窗之谊,共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正如编剧黄珂所言,“这部戏是写信念和兄弟情的,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虽因立场不同成了敌人,但心底里他们互相钦佩对方”,所以谭忠恕才会最后成全刘新杰,换来自己后半辈子的被软禁。该剧把刘新杰置于这种“兄弟是敌人”的艰难抉择之中,使得人物个性丰富饱满而又耐人寻味。
四、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中的女性抒写
由于承载和因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并成为被看的客体。新世纪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虽有所变化,但男权意识似乎隐藏得更深了。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电视媒介中,男性话语主导着对女性形象的想象和塑造,于是在电视荧幕上呈现出了“消费女性”的现象,女性的柔弱、感情用事和女性的身体成为电视媒介乐于塑造和暴露的素材。谍战剧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决定了其不可能把儿女情长作为情感塑造的主要方面,而如果缺失女性形象又难以平衡剧集的两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谍战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便显得尤为重要。谍战剧中的女性形象通常有三种:
一种是正面形象。比如我方女干部,常常作为配角出现,性别特征并不明显。一些谍战剧中这类人物形象常常处于被轻视和批判的地位,办案过程中这类人物不成熟并且感情用事,往往需要男主角的引导和帮助,如《一双绣花鞋》中女干部彭沛芝对身边人轻视冷淡,处处摆官架、拿官腔,不成气候。《数风流人物》中女干部夏晴作为主人公,虽能独当一面,但在遇到工作问题和生活苦恼时仍需求助于男性领导。尽管编导还力图通过情感戏来丰满夏晴的女性魅力,但成效不大,因为青春妩媚且更具女性气质的特务何梅更能行使被看和补缺功能,何梅和汪卫明(我公安局刑侦人员)之间的情感戏才更加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另一种是负面形象——年轻貌美、富有魅力的女特务形象。女特务形象,曾经是反特片中最具争议和关注的话题,她们往往是“黑色女人”,代表着颠覆社会秩序的反动势力。银幕上的女特务带有鲜明的视觉符号特征,她们总是妖娆漂亮,穿着高高的鞋子,涂着鲜艳的口红,穿着剪裁合体的衣服。谍战剧中的女特务形象也是如此,她们或貌美如花,心如蛇蝎;或明艳多情,善耍手段;或感情丰富,心理脆弱。她们是电视剧《数风流人物》里的何梅,《梅花档案》中的白薇和白蔷,《英雄虎胆》里的阿兰……这些人物形象有时候甚至压倒正面人物形象让观众难以忘怀。试想一个个鲜活、生动,同时又能完成符合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编码,继而满足男性话语下的“女性消费”,又怎能不让人记忆深刻呢?女特务形象在满足了大多数男性观众浅层次的感官欲望之外,作为谍战剧中另类女性也为充满英雄阳刚气息的谍战剧注入了一丝阴柔之美。有趣的是,如花似玉的女特务往往不是敌方最关键的人物,她们的美貌和放荡恰是考验我方侦察员的“法宝”,可谓“禁欲的古典英雄与纵欲的女特务之间建立起强烈的性别冲突与情感张力,考验着侦察英雄的道德观”。如《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复杂的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她身处险恶的土匪部落,其形象本身是用来满足大众视觉欲望的特殊符号,譬如她的特务使命是利用美色引诱曾泰,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形象,不仅多次险些被匪首李汉光强暴,还发现自己的父母被李月桂所害。于是,孤独无助的阿兰心存幻想地将希望寄托在合乎双方价值衡量标准的曾泰身上,当然,立场和使命使曾泰抵制住了“蛇蝎美人”阿兰的诱惑。
谍战剧中还有一类年长的女特务形象,她们或是大权在握的土匪首领,或是隐藏很深的特务头目,往往老奸巨猾、凶恶残忍。这类女性形象其实是作为反面帮衬的角色而存在的,“现代叙事学理论把作品中的人物作为叙事要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体,即‘正面’人物;第二类是反主体,即‘负面’人物;第三类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承担‘帮手’功能”。这类人物作为“负面”人物的帮衬角色,是剧情必不可少的元素,对于推动剧情有着重要的作用。《英雄虎胆》中的李月桂、《羊城暗哨》中的梅姨等皆是此类人物的代表,与年轻女特务相比,这类人物经验丰富而又易被忽视,往往成了悬念的最佳载体。
值得一提的是,谍战剧《潜伏》中“翠平”这一角色,突破了以上所说的三种女性形象特征。翠平是一个性格直爽、相貌平常的女游击队长,坚信“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从一开始她就对余则成所扮演的“潜伏”角色不认同,因为她的单纯几次差点让余则成深陷险境。与之前谍战剧中的女性颇有心计的形象对比,翠平这个完全不懂谍战为何物的局外人显得独树一帜,她看上去大大咧咧,但粗中有细,善良纯朴,她在“潜伏”中成长,自然就成了整个剧作的亮点。这个人物设置是对传统谍战片的一种另类表达。
第三节谍战剧的主题表达与叙事风格
一、多元化的主题表达
经典的文学影视作品常常被赋予多重内涵的解读,一些在影视史上流传久远的作品往往也是含蕴深厚的佳作。整体来看,大部分谍战剧的主题虽不及经典电影含意隽永,但在其发展的短短数年间已经彰显了主题内涵多元化的特征。
(一)主流价值观的内涵表述
基于谍战题材的特殊性,谍战剧自诞生之日起便被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承载者的烙印,因而很多谍战剧也可以称之为“主旋律电视剧”。《誓言无声》中许子风为保守国家机密默默牺牲;《暗算》中钱之江自杀后以身体送出情报;《密令1949》中冯秉堃数年坚持长期卧底敌方,忍受亲人的误解和埋怨;《潜伏》中的主人公余则成成就了革命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舍家为国的崇高信念在每一部谍战剧里都有体现,也作为谍战剧的主题内涵之一贯穿始终。随着时代的变迁,谍战剧还必须采取新的认同模式来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具体表现就是“主旋律色彩”淡化,但“主旋律意识”不能淡化,它将更加潜移默化地引导大众认同主导文化。与以往反特片一味通过歌功颂德、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提出苍白爱国口号等方式来归属自己主流意识形态不同,我们提出“新英雄主义人物”的塑造和革命叙事当下化的认同模式:
第一种认同模式是通过“新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与当下现实链接,人性化、平民化的英雄形象更易于被受众接纳,主流意识形态也通过真实生动的人物塑造潜移默化地行使了其主导和决定的权力。关于新英雄主义的人物形象塑造在上一节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种认同模式是将革命叙事进行当下化和世俗化转换。“大众日常生活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当下化’实际上就是使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下大众最关切的问题进行对接,形成了一种‘相关性’。”对当今受众来说,革命历史题材叙事文本一定程度上已经陌生化了,隐秘战线上的谍战斗争题材更是制造间离效果的典范,但如何在陌生化的基础上让观众体味现在,感知和平年代不会出现的对敌斗争的情境从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就需要文本在题材、风格、叙事等方面做好嫁接,转革命叙事的历史话语为当下阐释。此方面《暗算》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叙事文本。《暗算》的《看风》一章是依托回国女数学家黄依依“破译光密”而演绎出的一段浪漫而悲情的爱情故事,黄依依既是一个被周恩来总理点名回国的天才数学家,又是一个有着非凡勇气的至情至真的女人,她执著于自己选择的爱情,当安在天不能选择她时,她为爱自暴自弃失去了理智,她个性张扬,放任自由,与社会传统和压抑低调的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并一直进行不懈的斗争和反抗,这在上世纪60年代也就注定了其悲剧性结局的不可避免。安在天太了解她的个性:“对于她这样的人,唯有爱着,才能活着。”这一段60年代的悲情故事却让看了太多偶像剧的当代观众欷歔不已,当游戏人生玩弄情感已不是社会个案,当一切都可以拿来戏耍和消费的时候,我们依然钟情于黄依依的执著精神。普世主题之一的爱情故事与大众日常生活对接,“拯救和改造”的母题向大众文化靠拢,于是,《暗算》顺利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