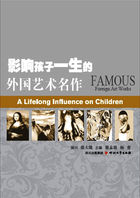其次,农村剧着力刻画了“创新式”村民形象。“创新式”村民形象通常有着坚毅、执著、不服输的品质。譬如《乡村爱情》的主人公谢永强,他大学毕业后一心等待到乡政府工作,然而命运弄人,他被分配到村里的小学做了教师,巨大的落差使得他无法做好本职工作。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在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开荒山、种果园,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当家的女人》的菊香为了摆脱家庭的贫困,先后养兔、养羊、养水貂,力争以养殖致富,虽历经挫折仍然执著坚韧,被誉为新时代的“李双双”。《圣水湖畔》的马莲是个与菊香相似的角色,她性格直率、不畏权威,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多次上访,执著地将高科技谷种引进村里并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刘老根》中的刘老根不甘于享清福,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开始了艰苦的创业,成为农民创业的典范。
再次,农村剧深度挖掘了“中间式”村民形象。创作者注重人物塑造的多样性,着重对这类“中间式”村民形象进行深度开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他们羡慕带领村民致富的“创新式”村民,但又惧怕创业带来的风险和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在不满足于自身处境,声称要脱贫致富时,却又好吃懒做,偷奸耍滑。在剧中,他们的名字大多被村民遗忘,只剩下一个绰号,如二歪、徐三懒、大嘴叉子等等。可以说,他们是当年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人物再现。“中间式”的村民形象的设置不仅增强了剧情的喜剧性,成为推动剧情顺利进展的润滑剂,更重要的是,创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加强了农村剧思想表达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通过对这些人的改造,显示出改革开放后新农村的变化。如《美丽的田野》中塑造的“三军司令”,这一绰号源于他三个儿子的名字——“空军、海军、陆军”。“三军司令”游手好闲,却还振振有词地说:“老天给你一副人的皮囊,你还去干活,真是白瞎了!”他爱凑在女人堆里说闲话,传播小道消息,但他本性善良,良心未泯,在村长的教导和村民的帮助下,他改掉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走上了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与“三军司令”异曲同工的还有《圣水湖畔》和《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的“徐三懒”和“大嘴叉子”,他们都不务正业,爱扎推听闲话,好装腔作势,但他们富有正义感和幽默感,最后都被改造成乐于为乡亲服务的“有用的人”。
农村剧就是这样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抑制恶、邪、丑,弘扬真、善、美,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品质的提高和优化社会习俗的目的。
二、鲜明的文化地域性
地域文化特色是经过世世代代生活积累而成的,是一个地方生活的微观缩影。地域性文化形态在各地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渗透着,几乎不受现代科技成果的影响而改变。同时,不同地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气质,使其建筑、饮食、风俗各个层面散发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可以说,不同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来自历史、气候、地形地势、交通、国家政策法规等多方面的影响。农村剧具有鲜明的文化地域性,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民风民俗中传达地域文化意蕴
农村是我国文化根基的所在,更是民间风俗保存最好的博物馆,所以,这种风俗的地域性在农村剧中有着明显的印记。如《篱笆·女人和狗》中加入了很多节庆民俗:端午节、乞巧节、中秋节等等,增添了全剧的趣味性和地域性。在北方的民间传说中,牛郎和织女会在乞巧节这一天会面,如果人们坐在葡萄树下就会听见他们的哭泣和谈话。因此剧中有着香草、大嫂马莲和巧姑坐在葡萄树下静静地倾听的情节,而听到的却是苏小个子的酸曲,三人的不同反应也从侧面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此外,剧中还加入了一些日常民俗,如拜老树为干娘、绞面线、在馒头上点花等等,丰富了作品的地域内涵性。《插树岭》中多次表现了东北农村的风俗习惯,如过年时家家门前都要点上火堆,希望来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党员二楞妈》表现了西北地区抬花轿、贴剪纸、上坟等各种民风民俗,因此很好地调动了观众的审美兴趣。
(二)借助音乐凸显地域文化印迹
文化地域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则是通过广为流传的民间音乐来承载。东北农村剧多以其特有的“二人转”来展现其地域文化的独特风采,对此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东北民间艺术中的重要地位。“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并吸取河北的莲花落,增加了舞蹈、身段、走场等形式。在东北农村,“二人转”有着肥沃的培育与滋润这种民间艺术的土壤,形成了炕头、场院式的小舞台表演形式。东北的艺术家们将地域文化与电视剧完美地结合起来,打破地域的束缚,增强了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和持久力。《刘老根》中大量地融入了“二人转”艺术,把东北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直率性格和质朴的民风民俗淋漓酣畅地展示了出来。《马大帅》中马大帅为了挣钱接下哭丧的活,在一位亡人的纪念日上表演单出头《王二奶思夫》,长达7分41秒,词语幽默,感情真挚,得到了观众的肯定。《福贵》则用湖南花鼓戏朴实、明快、活泼的曲调贯穿剧情,且不断地为剧中苦难的人开启一扇扇欢乐之门,对比的美学效果提升了电视剧的文化韵味。此外,《党员二楞妈》中反映了黄河流域的戏曲文化,如陕西的信天游“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我来眊妹妹你,半个月眊了你十五回,就因为眊你我跑成了罗圈腿”,这种对爱情直接而大胆的表白十分符合西北农民粗犷豪放的个性。
从辩证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农村剧的地域性弘扬了中国不同地域博大精深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容易引起观众的收视兴趣,但也由此限制了收视人群,方言的差异和地域特色的凸现一定程度上会减少部分观众的认同感,这一矛盾在农村剧今后的发展与突围中亟待解决。
三、源自农村生活的喜剧性
电视作为大众艺术,其功能不仅仅在于宣传教育,还在于带给观众更多的精神抚慰和审美愉悦,人们在紧张的生活之余,期望能从电视中得到放松和欢笑。凡是喜剧元素运用妥帖的电视剧一般都比较容易获得观众的青睐。为此,编导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农村剧中注入喜剧元素,如依靠夸张的表演、诙谐幽默的台词以及喜剧人物的塑造来博取观众的欢心,并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某些弱点进行夸张性、戏剧性或倒错性的表现来制造笑料与卖点。我们认为,农村剧的喜剧性源自“俗”,“俗”是农村文明的本真状态。农村社会向来是作为市民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农民受到土地的局限空间相对闭塞,文化一旦扎根就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这与城市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村文明稳固而顽固,不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蜕变,广大农民往往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各种文化加以改造,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众多的俚语、谣谚、顺口溜、歇后语,农村文化体系也自发形成并保存了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创造了独特的祭祀婚俗习惯和生活习俗。
为此,观众很容易在农村剧中感受到那些源自生活的喜剧性。比如,“农村三部曲”中的巧姑。首先是她长了一张不饶人的嘴,和苏小个子吵架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歇后语,让苏小个子招架不过来。其次是她的奸诈,在家开小灶,煮了饺子偷偷送给自己父母吃;看人下菜,想从“兔子王”那儿分一杯羹,就在他面前花言巧语,好茶好烟地热情招待。而老大媳妇的“直和憨”与巧姑的“刁和滑”正好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一乡之长》中对反面人物胡家兄弟的喜剧式塑造更是别具一格,创作者并没有让他们恶贯满盈,也没有让观众看了恨得咬牙切齿,更多的是让观众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好笑和有趣。他们仗着姐夫是县委书记,不仅在村里拖欠油坊承包款、聚众赌博,还处处想法阻挠新领导郝运来的工作。但他们有头无脑,不会工于心计,稍做坏事就会被人戳穿,行事中鲁莽而又不失天真可爱,是一对让观众乐不可支的“活宝”。
东北农村剧更具有那种源于平实生活的喜剧性。从《刘老根》开始,在观众的印象中,反映东北农村的电视剧就和风趣幽默画上了等号。如剧中“药匣子”的喜剧性来自于人物言行的反差:他貌似比其他村民有文化,于是经常卖弄文采,却又常常犯“张冠李戴”的语病;他貌似具有高超医术,又具有高尚医德,却又常常追名逐利,牟取私利,晚上偷偷去向山庄的顾客兜售自制的治疗不孕不育的药品时,却又无意间透露出自己膝下无子的难堪事实;他对丁香无限关怀,却又对丁香存有非分之想和对刘老根的嫉妒,他既能在看到丁香因刘老根而生气的时候给她送去药膳,又能在刘老根面前对丁香冷语相向。这些拿自己的“矛”戳自己“盾”的戏法,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让观众忍俊不禁。
此外,2007年开播的农村剧《文化站长》塑造了以“管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喜剧人物。创作者从一些细致入微的生活小事入手,一点点地为观众揭开文化生活的大幕,引人发笑的素材背后,又蕴涵着农民真诚纯朴的感情和对文化生活的渴求。正如该剧导演余淳所说,《文化站长》是一部轻喜剧,观众在笑过之后也会思索农民的文化生活怎么样?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生活?
农村剧这些源自生活的喜剧性表达,宣传了一种达观与超然的人生态度,让观众在观剧中自然地化解了现实的不快。在农村剧中创作者往往由关注小人物折射大社会,将特定阶层中的小人物放在貌似琐碎的小事情中去表现小冲突,用略带夸张和变形的人物和事件,将身边经常发生的故事在幽默、嘲笑和讽刺中表现出来,让观众在“含泪的笑”中体味出或浓或淡的生活的无奈和尴尬。
应该说,目前农村剧的创作数量不少,但真正称得上精品的却不多,至今没有出现能够超越上世纪“农村三部曲”那样谱写当代中国农民生存状态和改革前后“心灵史”的力作,且有格调低俗化的趋势。我们说,农村剧的创作确实要通俗易懂,但通俗易懂并不等于放弃审美追求而走向低俗、庸俗甚至媚俗的另一端。另外,农村剧“地域性失衡”现象十分严重,如反映北方农村生活尤其是东北农村生活的电视剧多,而反映南方农村生活的电视剧却凤毛麟角。其实,农村广阔,各方风土人情迥异,农民生活状态也不尽相同,看似平淡、普通、日复一日的农村生活中,却有着无限的文化宝藏,等待我们创作者去开掘、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