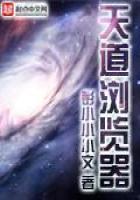当我无限怅惘的漫步在云端时,突然流云塌陷,我径直摔下。容不得我半点思考,直勾勾地往地面栽去。顿时,世界漆黑,撕心裂肺的疼痛蔓延全身。我想,我再也活不了了。
良久,我缓缓睁开双眼,只见屋子里红烛垂泪,铜炉留香,气若幽兰,依旧是我钟爱的沉香气味。只觉得胸口异常的闷,刚想张口唤人,一口黑血便从嘴中吐出。生平第一次吐血,我倒没有吓得不知所措。因为,我依然自信的以为自己还是处于梦境之中。我缓缓地抬起手想要拭去嘴角的鲜血,刚一触摸,便体察到血液的温热。顿时便慌张起来,我已经回到现实里了!更加让我不安的是,我的裙裳上也满是鲜血。怎么又是葵水?距她上次拜访才一旬有余。我是不是要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笼罩我的世界。
我不顾一切地喊道:“尔朱荣,沈辞,尔朱荣,沈辞……”此时我的语气必定是十分虚弱,思维的混乱已然让我顾不了称谓、人选。
话音未落,沈辞便冲了进来,随他身后的是一脸慌张的哥哥。
他们满是紧张,不约而同地喊我的名字,我微微一笑,想说其实自己没事,可却没了力气,再次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当真是梦来如山倒,梦去如抽丝。
接下来的数日,我便是在王府中休养。医官说我是伤神所致,病情古怪。索性自由良方,才并无大碍。医者总是喜欢夸张病人的病情,然后用药到病除的保证,来渲染着自己医术水平的高超,古今都是如此。
事后,沈辞总是会不羁地调侃,说什么古人弹琴,用情深处,便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我这倒好,高山流水遇葵水。听到这,我脸颊绯红,沈辞你这般直白地取笑,考虑过一个沉静内敛女子的感受么。话虽如此,我也无意中听府上侍女说,我昏倒的那几日,沈公子早已收起了往日的洒脱作派,一日日的在园中吹起吹箫,曲声呜咽。说到此处,侍女脸上早已如天边晚霞。
这一日,汝南王元悦来访,非要央请我这位“好兄弟”去第一楼听曲。这个王爷真是荒诞不经,相处日久,竟还以为我是男儿之身。看着他邪魅的眼神,我自然心神难安。拉着哥哥与沈辞一并前往,根本不顾元悦气急败坏的神情。
原来这一日,是备受瞩目的“赏花会”。整个洛阳城规模较大的十所妓馆的花魁,齐聚于此,供花客品鉴。
赤红色的步障绵延两里,无一不在炫耀着此地的繁华。步障之外,人头攒动,尽是想要瞧热闹的人群。
店内僮仆把我们引领到厅堂,依旧是灯火辉煌,极尽奢华之能事。单是,室内的一方大大的水池,便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我和哥哥以及沈辞早早落座,只见元悦铁青着脸还在责备僮仆:“为何姓范的不出来见我?”僮仆吓得面色苍白,硬着头皮说道:“掌柜的在招待贵客。”听完他的答复,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不禁感慨,论服务业从业人员应变能力的重要性。果然,元悦一个巴掌甩在僮仆的脸上:“还******贵客,老子就是贵客。”此时大厅里,尽是丝竹之声,一片喧嚣,自然没人顾及此边的争吵。我和沈辞,第一时间把他俩分揭开,对这个霸道王爷也是颇为无奈。
没多久,待众位纨绔子弟坐定。只听得一声清脆的笛声响,便有一群舞女拥着一个花魁登场,姣服华裳,珠翠流光,虽然绝姿妙态,然而风尘之味颇浓,我已了无兴致。
不知何时,元悦把手搭在了我的手上,我像是碰到了火炉里的炭火,连忙撤回手来。元悦在一旁嬉笑:“鱼兄弟,好生羞涩。你我都是男子,如何这般生分?”只见沈辞侧过身来,径直把手搭在元悦的肩上:“汝南王,同是男子,你怎么一直对我视而不见,如此厚此薄彼?”元悦一脸嫌弃地把他的手挪开,面露鄙夷地说道:“你这粗糙汉子,休要打本王的便宜。本王,向来只爱鱼儿这般清秀小生。”说得毫不顾忌,惊落我一身鸡皮疙瘩,看来汝南王爱好男风,所言不虚。
台上的花魁走马灯似的轮换,我也着实没记住几个面孔。只有膏粱公子的喝彩之声与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于是,我总是可以在人声沸腾的时候看到,有的女子欢喜答谢,有的女子花容失色。
沈辞用手中打着拍子的银箸朝正前方的楼上指了指,只见范玄向提着酒壶在栏杆内卑躬屈膝,看来僮仆所说的贵客就在其中。元悦早已顺着银箸的方向看了过去,嘴里不由得骂道:“范玄向,好你个奸贼,原来这里还有这等的好去处。”说罢,便拉着我的手,要往楼上去。我一把挣脱开,跑到沈辞旁站定。沈辞,笑着望着我:“你跟着我就好。”我点了点头。
店内一个管事模样的中年男子,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把我们引到了楼上包厢之内坐定。果然,此处是一个上佳的位置,厅堂的一切都可以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所以,我发现纸醉金迷的公子堆里,一个宝蓝色的身影。是桑律,当然,还有睡卧在他怀里以及趴在他肩上的蜂蜂蝶蝶。甫一发现的新大陆,在一瞬之间,沉没汪洋。忽然有一种晕眩的感觉,想必是楼太高的缘故吧,我在心里无奈着嘲笑自己。拿起案几上的银杯,把酒一饮而尽。元悦满脸担心:“鱼儿,慢点喝,喝坏了身子如何是好。”沈辞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手中的酒一并饮下,低声说道:“方才的酒就当作是你敬我好了。”我苦笑着,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寒意与暖意。
沈辞做了一个禁声的手势,只听得一声红牙板响,便有铜琵琶声呜咽起来。一袭曳地白色烟笼寒水百花裙缓缓而来,最后压轴出场的花魁艳若桃花,广袖舒展,妖冶迷人。原来,此人正是云喜。只一出场,便有富家公子开始打赏。从沈辞口中我才知道,在我昏迷的这几日,云喜便辞别王府会到第一楼。想必是没有承蒙清河王的恩宠,失意而回。
再一看时,云喜早已移至池边,巧笑顾盼,脸颊泛起一对梨涡。只见她,在急促的琵琶声中旋转着,宛若彩蝶。忽然一个转身,水袖曼舞,佳人已舞到水面之上。裙裾飘飞,窈窕的身段柔软的好似春絮。总是舞姿翩跹,她也能牢牢地在水面之中站稳。我隔着珠帘,看那池面上的人儿,亭亭玉立,恰似凌波仙子。
一曲舞罢,众人已如痴如醉。以至于一向标榜正人君子的沈辞,都有点走神了。
按照惯例,表演之后,在座众人可以对花魁进行竞价。价高者,得花魁。无人问津者,自然回到妓馆,依旧往日营生。
都城向来,不缺一掷千金的主儿。于是,前九位的花魁很快就被各个府上的公子够得。最贵的价格,已到百金。然而,这更像是漫长无聊的前奏,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竞拍的时候,各个妓馆的老鸨都会牵着自家的姑娘到台上。三圈之后,没有加价者,最高价的那个人自然可以抱得美人归。
云喜被一个半老的徐娘牵着,落落大方的在舞池中央站定。只听一个醉醺醺的声音喊道:“洛阳桑家,两百金。”话音一出,满堂哄然。我看着楼下的桑律,志得意满,好不快活。看来,曾经的胆小鬼也试着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成长,心里不由得苦笑。只听旁边有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洛阳何青,三百金。”我试着探过头去看,苦于隔着隔断,无法看到。这时,又听到楼下嘈杂:“都是什么猫猫狗狗,通直郎宋维,三百五十金。”正是前几日被北流暴打的宋维,没想到伤好的这么利索,这么快就可以胡作非为了。话音未落,只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华服少年喊道:“通知郎是几品官来着,好生威风。”见那宋维正要发火,转过头看时,立马变了一副嘴脸,“原来是遵公子,小人失态。”
少年也不理会,旁边的侍卫高声喊道:“高阳王府,五百金。”在座的公子哥们无一不投来艳羡的目光。原来此人正是,高阳王元雍的长子,元遵。而高阳王,正是洛阳城中首屈一指的富豪。看来,此次的花魁竞价,名花有主了。
沈辞逗对面的元悦:“汝南王平日素来风雅,为何不竞价一番。”元悦一脸不屑:“本王,对这些庸脂俗粉向来不屑一顾。”说罢,又转头向我,目光流连。
老鸨已经牵着云喜,走了两圈。
云喜,面色如水,不悲不喜。
就在这时,依旧是旁边的那个熟悉声音响起:“洛阳何青,一千金!”
厅堂内,顿时如炸开了锅,目光纷纷向楼上望去。有说书先生也早已乔装打扮混了进来,在纸上飞快的写着,日后这一段又可以讲的唾沫横飞。
云喜的脸上竟开始,有了一些喜色。自己有了这么高的身价,确实应当欣喜。
老鸨牵着云喜,一圈圈的走着,早已笑的合不拢嘴。众人望向元遵,此刻能出得了更高价格的只有元遵了。然而元遵面如死灰,并无一丝兴致,已然败下阵来。
我问沈辞,可否识得何青。他如往日般胸有成竹,却依旧是笑而不语。
元悦早已暗骂:“明日我就要上朝找太后讨要封赏,堂堂的王爷连侍妾都卖不起。”
几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两个身穿墨色斗篷的人被数人簇拥着朝后门走去。我拉起沈辞,就要跟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