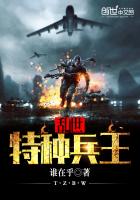那些小孩子们因为他不会做游戏或者不会放风筝,或者是因为他某个词发音错了而取笑他的时候,他仅仅是因为知道杀死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子是不公正的,才使他没把他们抓起来撕成两半。
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气。在丛林里,他知道自己和那些动物比起来是弱的,可是在村子里人们都说他像一头公牛一样壮。
毛格利还一点也不懂得种姓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次一个陶工的驴子滑进了泥坑,毛格利抓住驴子的尾巴把它拉了出来,还帮助陶工把陶罐堆起来,好运到卡里瓦拉市场上去卖。这使人们大为震惊,因为陶工属于低级的种姓,至于驴子,就更加卑贱了。当祭司斥责他的时候,毛格利威胁说要把他也放到驴子背上去。祭司告诉米苏阿的丈夫说,毛格利最好是让他去干活,越快越好;村子里的头人对毛格利说,他第二天就得赶着水牛去放牧。没有谁会比毛格利更高兴了;那天晚上,因为他被指派要为村子服务,就去参加每天晚上都要举行的聚会。人们在一棵大无花果树下,围着一个石砌的平台坐成一圈。
这里是村子的俱乐部,头人、守夜人、剃头匠(他知道村子里所有的闲言碎语).还有拥有一支塔牌老式步枪的村里的猎人老布尔迪,都要在这里碰头、抽烟。猴子们坐在高高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平台底下有个洞,洞里住着一条眼镜蛇,他每天晚上都能喝上一小盘牛奶,因为他是神蛇;老人们围坐在树下聊天,抽着巨大的水烟袋,一直到深夜才散。他们讲神、人和鬼的美妙故事,布尔迪还讲丛林动物的生活,更加美妙动听,那些坐在圈子外边的孩子们听得眼睛都要从脑袋上鼓出来了。大部分故事是关于动物的,因为丛林一直就在他们家门外。鹿和野猪经常来吃他们的庄稼,老虎时不时会在黄昏、就在村子的大门口看得见的地方咬走一个人。
毛格利自然知道他们谈的一些事情,他遮住脸,不让别人看到他在笑。当布尔迪把他的塔牌步枪放在膝上,从一个神奇的故事讲到另一个神奇的故事时,可以看到毛格利的双肩抖个不停。
布尔迪解释道,那个拖走米苏阿儿子的老虎是一只鬼虎,他身上附着一个缺德的老放债人的鬼魂,这个人是前几年死的。
“我知道这可是真的,”他说, “因为普闰·戴斯自从那回暴动被烧了账本、挨了揍之后,走路就一瘸一拐的了,而我说的那只老虎也是一瘸一拐的,因为他留下的蹄印深浅不一样。”
“是真的,是真的;这肯定是真的。”那些灰白胡子的老人一齐点头说道。
“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胡编乱造出来的吗?”毛格利开口说话了, “那只老虎一瘸一拐,是因为他生下来就是瘸腿,这是谁都知道的。说放债人的魂附在一只连豺的胆量都没有的动物身上,简直是胡话。”
布尔迪吃了一惊,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头人瞪圆了眼睛。
“噢!是丛林里的毛小子,是不是?”布尔迪问, “你既然这么聪明,为什么不把他的皮剥下来送到卡里瓦拉去?政府用一百卢比悬赏他的命呢。好好呆着,大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
毛格利站起来就走。 “整个晚上我躺在这里听,”他回过头来大声说道, “除了一两句,布尔迪说的关于丛林的一切没有一个词是真的,可是丛林就在他的家门口呀。我怎么能相信他讲的什么鬼、神、妖怪的故事呢?他还说是他亲眼见过的呢。”
“这个孩子真该去放牛了。”头人说。布尔迪被毛格利的傲慢无礼气得直喘粗气。
大多数印度山村习惯上让几个孩子大清早就把牛和水牛赶出去放牧,晚上再把他们赶回来。那些牛轻易就可以踩死一个白种男人,却任由一些几乎还够不到他们鼻子的小孩子们又打又骂。只要和牛群呆在一起,这些孩子就会非常安全,因为即使是老虎也不敢袭击一大群牛。可是如果他们跑开去摘花,或者捉蜥蜴,有时就会被老虎叼走。黎明时分,毛格利骑在牛群头领大公牛拉玛的背上,穿过村子的街道;蓝灰色的水牛,长着向后弯曲的长角和凶猛吓人的眼睛,一只接一只地从牛棚走出来,跟在他后面。毛格利很清楚地向那些和他一起放牧的孩子表明,他是头儿。他用一根又长又光滑的竹竿打水牛,又告诉一个叫卡米亚的小男孩,叫他们自己放牧牛群,小心不要离开牛群乱跑;毛格利自己赶着水牛继续往前走。
印度的牧场布满了岩石、矮树丛、杂草和小溪流,牛群分散其间,一下子就看不见了。水牛通常喜欢呆在池塘和泥沼里,在温暖的烂泥中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打滚或者晒太阳。毛格利把他们赶到平原边上、维根加河流出丛林的地方;然后他从拉玛的脖子上跳下来,快步跑到竹丛那里,找到了灰兄弟。
“哎,”灰兄弟说, “我在这里等了好多天了。你怎么于起了放牛的活?”
“这是命令,”毛格利说, “我暂时是村子里的放牛人。谢尔可汗有什么消息吗?”
“他已经回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还在这里等了你很久。现在他又走了,因为这里猎物太少。但是他一直想要杀死你。”
“很好,”毛格利说, “只要他不在的时候,你或者四个兄弟中的任何一个就坐在那块岩石上,这样我一出村子就能看见你们。他回来后,你就在平原中间的那棵达克树下等我。我们犯不着自己走进谢尔可汗的嘴里。”
然后,毛格利拣了一块阴凉的地方,躺下来睡着了,在他四周,水牛安静地吃草。在印度放牛,是天下最悠闲自在的一种活儿。牛往前移动着,嚼着草,然后躺下来,然后再往前移动,他们甚至都懒得哞哞地叫两声。他们只是发出呼噜的声音。水牛就更少说什么了,只是一头接一头地走进烂泥塘,慢慢地钻进烂泥,直到只剩下鼻子和瞪圆的青瓷色眼睛还露在水面上,他们躺在那里,就像一根根圆木头。太阳晒得石块在酷热中跳起了舞,放牧的孩子们听见一只鸢(永远不会再多)在头顶几乎望不见的高空呼啸着,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死了,或者一头牛要死了,那只鸢就会俯冲而下,几里之外的另一只鸢看见他往下飞,会跟着飞下来,接着又飞来一只,又飞来一只,就在他们死去之前,会有二十只饥饿的鸢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到这里来。
放牧的孩子们睡去,醒来,又睡去;他们用干草编织小笼子,把蚂蚱放进里面;或者抓两只螳螂,看他们打架;或者把黑色或红色的丛林坚果穿成一串项链;或者观察一只蜥蜴在岩石上晒太阳,一条蛇在水坑边捉青蛙。然后他们唱起了长长、长长的歌,结尾的地方带着本地的奇特的颤音,这样的一天比起大多数人的整整的一生还要漫长,也许他们用泥造一座城堡,还有泥人、泥马、泥水牛,他们在泥人手里插上芦苇,自己扮作国王,泥人、泥马、泥水牛就是他们的军队,或者他们把自己装成是受崇拜的神。傍晚到来了,孩子们呼喊着,水牛笨拙地爬出黏糊糊的烂泥,喷出一声接一声像打枪一样的声音,他们排成行,穿过昏暗的平原,回到灯火闪烁的村庄。
毛格利杀死了老虎
一天又一天,毛格利领着水牛到它们的泥塘里;一天又一天,他看见一里半外平原上灰兄弟的脊背(他由此知道谢尔可汗还没有回来);一天又一天他躺在草地上倾听周嗣的声音,梦想着往日丛林的时光。在那些漫长而寂静的上午,如果谢尔可汗在维根加河畔的丛林里伸出瘸腿迈错一步,毛格利也会听见的。
终于有一天,他在约为信号的地方没有看到灰兄弟,他笑了,带领水牛来到达克树旁的溪流边,树上开满了繁盛的红花。
灰兄弟坐在那里,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
“他隐藏了一个月,想让你放松警惕。昨天晚上他和塔巴克一起翻山越岭,要来加紧追踪你。”灰狼一边喘气一边说。
毛格利皱了皱眉头, “我倒不怕谢尔可汗,只是塔巴克很狡诈。”
“不用怕,”灰兄弟说着,轻轻舔了一下嘴唇, “我在黎明的时候遇见了塔巴克。现在他大概正在对鸢卖弄他的聪明吧,可是,在我咬断他的脊梁骨之前,他就把什么都告诉了我。谢尔可汗打算今天晚上在村口大门边等着你——专门等你,不等别人。他现在正躺在维根加的那条干涸的大河谷里。”
“他今天吃过了,还是空着肚子?”毛格利问。答案对他是生死攸关的。
“他黎明时杀了一只猪,还喝了水。你要知道,谢尔可汗永远不会戒食的,即使是为了报仇。”
“噢!笨蛋,笨蛋!简直就是比小孩子还小孩子!又吃又喝,他还以为我会一直等到他睡够了呢!他躺在哪里?要是我们有十个同伴,就可以在他躺着的地方动手干掉他。这些水牛除非闻到他的味道,否则是不会冲上去的。我们怎么能找到他留下的踪迹,好让水牛嗅出他来?”
“他在维根加河里游了很长一段,踪迹就断了。”灰兄弟说。
“肯定是塔巴克告诉他的,我知道。他自己压根也不会想出这个办法来。”毛格利把手指放进嘴里,寻思着, “维根加的大河谷。它通向离这里不到半里的平原。我可以带着牛群从丛林绕到河谷的头上,然后猛扑下去——但是他会从另一头溜掉。我们必须堵住这一头。灰兄弟,你能帮我把牛群分成两部分吗?”
“我恐怕不行——但是我带了一个聪明的帮手。”灰兄弟快步跑开,钻进一个洞里。接着洞里伸出一只灰色的大脑袋,那是毛格利非常熟悉的;炎热的空气中充满了丛林里最凄凉的叫喊——那是一只捕猎的狼在正午的嗥叫。
“阿克拉!阿克拉!”毛格利拍着手掌说, “我早就该知道你不会忘记我。我们正要做一件大事。请把牛群分成两半,阿克拉。让母牛和小牛在一块儿,公牛和耕地的水牛在一块儿。”
两只狼跳起了四对舞式样的步子,在牛群里跑进跑出,牛喷着鼻息,昂着头,被分成了两堆。一堆里,母水牛站着,把她们的小牛围在当中,瞪着眼睛,以蹄踢地,只要哪一只狼稍微停下不动,她们就会冲上前去把他踩死。在另一堆里,成年公牛和年轻的公牛喷着鼻息,跺着蹄子;只是他们看起来吓人,实际并不特别危险,因为他们没有小牛需要保护。就是有六个男人,也不能这么干净利索地把牛群分开。
“有什么命令?”阿克拉气喘吁吁地说, “他们又要合到一块儿去了。”
毛格利迅速跨上拉玛的背。 “把公牛赶到左边,阿克拉。
灰兄弟,等我们走了以后,你把母牛集中在一起,赶进河谷底部的那一头。”
“赶多远?”灰兄弟问道。他喘着气,对牛群猛咬着。
“直到河岸高到谢尔可汗跳不上去的地方,”毛格利喊道,“让他们守在河谷里,直到我们下来。”公牛在阿克拉的吼声下奔了过去。灰兄弟站在母牛前面,母牛向他冲去,他跑在她们前面一点点,就这样把她们带到了河谷底下的一头。这时阿克拉已经把公牛赶到左边很远的地方了。
“干得好!再冲一次他们就要开始跑了。小心,现在——小心了,阿克拉。咬一次足够了,他们就要冲起来了。哎哟嗬!
这可比赶黑公鹿狂野。你没想到这些家伙会这样跑进丛林吧?”
“我身强力壮的时候也——也猎过这些家伙,”阿克拉在扬起的尘土中喘着气, “我要把他们赶进丛林吗?”
“对,赶进去!快点赶!拉玛已经气疯了。噢,如果我能告诉他我今天需要他干什么,那该多好!”
这一次公牛转向了右边,横冲进高耸着的密林。其他那些在半里外观望的放牛的孩子,拼了命飞快地跑回村子,大声叫喊道:水牛疯了,都跑了。
毛格利的计划其实非常简单。他想做的只是在山上绕一个大圈,到了河谷头上以后,再带领公牛沿河谷而下,在公牛和母牛群之间捉住谢尔可汗;因为他知道,在饱食一顿、狂饮一番之后,谢尔可汗处于不利于搏斗的状态,也爬不上河谷的两岸。到这时候,他以自己的声音安抚水牛,阿克拉已经退到了牛群后面,偶尔呜呜叫一两声,催促殿后的水牛快走。他们绕了很长很长的圈子,因为不想离河谷太近,引起谢尔可汗的警惕。终于,毛格利把迷惑的牛群领到了河谷头,来到一块陡斜地插入河谷的草地上。在那块高坡上,越过树梢可以看到下面的平原;但是毛格利注意看的是河谷的两岸,他非常满意地发现,两岸几乎是直上直下,爬满了藤蔓,一只老虎要是想从这里逃出去,可找不着立足的地方。
“让他们喘口气吧,阿克拉,”他举起一只手来说,“他们还没有嗅到他的味道呢。让他们喘口气吧。我要告诉谢尔可汗是谁来了。我们让他落进了陷阱。”
他双手围拢嘴巴,对着下面的河谷高喊——几乎就像是对着隧洞高喊——回声从一块岩石上弹起来,再碰到另一块岩石上。
过了好长一会儿,才传来一只刚刚醒来的、吃得饱饱的老虎的吼叫,那声音慢腾腾的,睡意未消。
“谁在叫?”谢尔可汗问。一只孔雀拍打着翅膀,惊叫着从河谷里飞了出来。
“是我,毛格利。偷吃牛的贼,现在是到会议岩石去的时间了!下去——快把他们赶下去,阿克拉!下去,拉玛,下去!”
牛群在斜坡边缘犹豫了片刻,但是阿克拉张大喉咙发出了捕猎时的狂叫,他们就一头接一头飞奔而下,就像轮船穿过激流似的,扑腾得周围飞沙走石。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有机会停住了,他们还没有奔进河床,就嗅到了谢尔可汗的气味,立即吼叫起来。
“哈!哈!”毛格利骑在牛背上,说, “现在你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