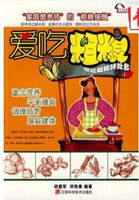张嬷嬷没得到二门口的消息,以为交待扁豆的话奏效,心里得意,急忙领头跪下求饶:“老夫人,奴婢们冤枉啊!姑娘去林府时好好的,回来没两天就不舒坦,到今儿个早上才发作。奴婢们已是小心翼翼地伺候,半点不敢不经心,求老夫人细查!”
凤梨等人连连磕头喊冤。
傅老夫人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抑扬顿挫地喝问:“你还敢狡辩!死鸭子嘴硬,凭你这句挑拨离间的话,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自个儿过来摸摸卿丫头的衣袖,到现在仍是湿的,这就是你‘小心翼翼伺候,半点不敢不经心’!我定南侯府买你伺候千金小姐,你就是这么‘经心’伺候的?你好,你好的很!”
张嬷嬷听到个“死”字魂飞天外,傅卿云的衣袖怎么会是湿的?
凤梨的脸瞬间惨白,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的水壶,是那壶水……当时她磕头磕得精神恍惚,原来那壶水浇到了傅卿云袖子上,傅卿云为什么不提醒她?
张嬷嬷不知就里,直觉认为是傅卿云趁她们不注意,故意泼袖子上的,在性命威胁下张口反驳:“老夫人明鉴,凤梨和忍冬扶大姑娘去炕上时,大姑娘的袖子明明是干的……”
傅老夫人大怒:“贱婢!你竟敢诬陷大姑娘陷害你个奴婢,也不瞧瞧你自个儿不过贱命一条,大姑娘打杀了你,你都得跪着谢恩,还敢攀诬大姑娘!徐嬷嬷,给我掌嘴!”
“是,老夫人!”
徐嬷嬷走到张嬷嬷面前,僵硬的脸面无表情,说道 :“张嬷嬷,老婆子得罪了。”
言罢,徐嬷嬷示意两个膀大腰圆的婆子按下张嬷嬷,左右开弓扇张嬷嬷嘴巴子,她扇的很有技巧,十几巴掌下来张嬷嬷才嘴角破裂流出血来,“啪啪啪”的声响令房内众人鸦雀无声。
傅卿云害怕地缩进傅老夫人怀里,卷了袖子以免凉到祖母:“老夫人,算了罢,那会子我晕过去,人事不省,袖子藏在被子里,我自个儿都没察觉,何况张嬷嬷呢?”
傅老夫人为傅卿云小小的动作而动容,这个大孙女真是太贴心了,她没办法不喜欢,沉声说道:“本瞧着你在病中,打算等你痊愈再处置,可我怀疑这起子轻慢主子的贱婢们能不能把你照顾到痊愈。你是我们定南侯府的嫡长孙女,哪能任由几个奴婢欺负至这般田地,且歇着,瞧你祖母的手段!”
说罢,傅老夫人命她的大丫鬟杜鹃放下帘子给傅卿云换衣服,淡淡瞥一眼神情惶惶的小林氏,庶女就是庶女,骨子里就是个低贱的,飞上枝头仍是个麻雀,永远没长进!张嬷嬷的话打量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谁的主意呢!
小林氏察觉到傅老夫人的不满,到了嘴边的话瞬间咽了回去,讷讷不敢言语。
徐嬷嬷打到三十多下时,张嬷嬷的嘴巴打烂了,潺潺的血水争先恐后地流出,张嬷嬷眼泪鼻涕流了一脸,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口中发出“唔唔”的声响,一句话说不出。
傅老夫人叫停,凌厉的视线一一扫过众仆,最后落在白檀身上:“今儿个我头一天回府就能遇到这种事,可知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得有多张狂!以前的账我没看见便罢了,既然张嬷嬷敢当着我的面攀诬主子,可见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丝毫没有悔改之心。今儿个的账我就一一跟你们清算,定南侯府金尊玉贵的小姐也是你们敢谋害的,赶明儿是不是要骑到我脖子上拉屎撒尿?”
傅老夫人的目光在小林氏身上停留一瞬,小林氏心惊,脸色煞白。
凤梨等人吓得大气不敢喘,七零八落地跪下磕头:“奴婢们不敢!”
傅老夫人转向整张脸肿成猪头的张嬷嬷:“张嬷嬷,你来说,方才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张嬷嬷打得不成形的嘴巴浸泡在血水里颤抖,说话舌头打结,眼中满是恐惧,耳朵里轰隆隆的全是雷鸣,赶忙跪下磕头:“老夫人饶命!奴婢只是想说大姑娘染恙,不曾有别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我胡思乱想,陷害你个奴婢?”
张嬷嬷全身发抖,恍若秋风中凋零的落叶,挂在光秃秃的枝头孤单地摇摇摆摆,她下意识地看向小林氏,眼神哀求。这个语言陷阱,她跳不跳都是个死,谁叫她暗示傅老夫人是傅卿云故意弄湿袖子诬陷她呢?
小林氏从未见过傅老夫人发这么大火,若是知道傅卿云背着她给傅老夫人送年节礼物,她肯定不会铤而走险,同意张嬷嬷的计划。
落到这步田地,是张嬷嬷咎由自取!所以,在张嬷嬷投来求救目光时,她撇过脸,脚步轻轻移动,躲在傅三夫人身后。
张嬷嬷绝望,又看见小林氏伸出三根指头,她瞬间匍匐在地上,小林氏在威胁她,她的三个儿子可在小林氏手里呢:“奴婢不敢欺瞒老夫人,奴婢的确没有别的意思!”
傅四夫人跳出来指着张嬷嬷尖利地叫:“你个嘴硬的下贱奴才秧子!你说大姑娘在林府好端端的,偏偏老夫人回府时大姑娘病了,不就是说老夫人跟大姑娘八字不对盘,冲病了大姑娘么?”
傅卿云换好衣服,听了这话,一下子撩开帘子扑出来,眼睛红红的:“老夫人,孙女不是因为老夫人回府才生病!孙女只是有些不舒服罢了,老夫人可千万别听信小人之言!”
傅老夫人赶忙搂住哭泣的傅卿云:“好孩子,我知道的,你养着,这起子小人,祖母一个都不会放过!等我处置了她们,再给你挑好的来。”
傅卿云感激地颔首,眼含泪,唇含笑:“老夫人信我,孙女就放心了。”
傅老夫人转回头,看向张嬷嬷:“张嬷嬷,你刚才的话在座众人听得清清楚楚,你狡辩也无用。来人啊,张嬷嬷挑拨离间,怠慢主子,导致主子病重,拖出去打八十大板!”
傅卿云适时露出吃惊和害怕的神色,又状似强迫自个儿镇定,十分信任依赖傅老夫人。
张嬷嬷大惊失色,半烂的舌头不敢打结了,声音跟老鸹的破锣嗓子似的惊恐嚎叫:“老夫人饶命!老夫人饶命!大姑娘求您饶了奴婢,奴婢再也不敢了,夫人,夫人救命啊——”
傅老夫人无动于衷,那两婆子一边一个,拎起张嬷嬷的两条胳膊就把她像拖死狗那般,拖了出去。傅老夫人的大丫鬟杜鹃使个眼色,行至门口时,有人塞条抹布堵上张嬷嬷的嘴,最后只剩下呜呜咽咽的声音。
一炷香的时间后,徐嬷嬷回来面无表情地禀报:“回老夫人,张嬷嬷没挨过八十大板,奴婢数到四十三板,她已是断气了。”
房内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顷刻后,个个噤若寒蝉,傅家的姑娘少爷们停下窃窃私语,纷纷看向傅老夫人,胆子小些的躲进母亲怀里。
傅老夫人让孙子孙女们围观,就是告诉他们,定南侯府的小主子们容不得奴才糟践。
傅冉云以帕掩唇,眉心纠结,警告地盯视白檀,却见白檀呆愣愣地跪在地上,不知在想什么。
傅卿云藏在茜纱帘帐后的眸子里寒光闪烁,轻轻舒口气,张嬷嬷终于死了,这个教养嬷嬷把她养成前世那副全身心信赖小林氏的性子,隔三差五地挑拨她和外祖母的关系,导致她最后失去外祖母的心,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她落得那般凄凉的下场,未必没有张嬷嬷的推波助澜。
傅卿云寻思半晌,怯生生地打破一室寂静:“老夫人,张嬷嬷毕竟是孙女的教养嬷嬷,有三个儿子,孙女是当做奶兄来看待的。孙女求老夫人恩典,让奶兄们领张嬷嬷回家入土为安。”
这种奴大欺主的奴才打死后,通常会卷个烂草席扔到乱葬岗上喂野狗去。张嬷嬷的儿子也是定南侯府的奴才,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胆子去乱葬岗上领尸体的。
傅四夫人称赞:“大姑娘真真心善!”
傅卿云隔着半透明的茜纱帐轻轻摇头:“四夫人谬赞,侄女只是……侄女原也未觉被冒犯,张嬷嬷向来是这个性子,从小教养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是她是个奴才,实不该冲撞老夫人,老夫人是我祖母,我孝顺还来不及,哪里容得她污蔑。我心里恨归恨,到底人死如灯灭,念在她教养一场的份上,实在不忍心她暴尸荒野。”
小林氏胸口起伏不定,好人全让傅卿云做了。
傅老夫人欣慰颔首,她没看错傅卿云:“徐嬷嬷,你就按大姑娘所言去安排罢。张嬷嬷那三个儿子在哪里当差?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嬷嬷长了个是非嘴,她那三个儿子也不是好的,不管哪里当差,都撵去庄子上去。”
后面这话就是对小林氏吩咐的了。
小林氏张了张口,傅老夫人根本没给她反驳的余地,一句话决定了张嬷嬷三个儿子的去留,她恭敬地弓腰束手:“是,老夫人,媳妇马上命人安排。”
在大家以为这场混乱以张嬷嬷的死结尾时,傅老夫人又开口了:“扁豆呢?传扁豆上来。”
扁豆听到传唤,脚步轻快地进屋:“老夫人大安。”
“扁豆,把你今儿个在二门上回我的话再说一遍。”
“是,老夫人。”
扁豆竹筒倒豆子似的重复一遍刚才的话,一字不差。
傅老夫人看向白檀,漫声问:“白檀——”
白檀“咚”地磕个头:“老夫人!”
傅老夫人挑高一边眉毛,更添凌厉:“侯夫人给你对牌,让你请薛大夫,你去哪儿了?嗯?”
尾音严厉地上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