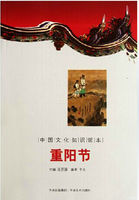东北长白山挖参人的禁忌很典型。挖参人(也称“放山人”)在放山时,先要烧香上供,敬长白山挖参人的开山鼻祖山鬼爷——“老把头”,要施行一些巫术,即在发现人参时,要有四句“喊山”问答的巫术语言和用“块当绳”(即红头绳)拴住人参的巫术行为。此外,还要遵守一些放山禁忌,如挖参人需要休息时不能互相喊叫,而是以敲树干为暗号,谓之“叫棍儿”,说“若是喊叫,麻达鬼会接应的”。实际上,大声喊叫,造成紧张气氛,影响挖参情绪。大树墩儿不准坐,说那是山鬼老把头的座位,坐了就鼻口流血。其实,树桩子潮湿,坐在上边会受潮生病。松树明子不准坐,说那是山鬼“老把头”的蜡烛;一端烧黑了的木头不准坐,说那是山神“老把头”的笔。谁做了好梦,早晨起来不准讲,怕说破了,不灵验了。不上山的“端锅”(炊事员)做好饭后,在棚里不能先吃,说如果一吃,那些挖参人就又饿又累。“端锅”也不能睡,如果一睡,挖参人的头就昏。
(3)在山里干活的忌避
在浙江西北部的山区,人们崇拜山鬼之深,已到了迷信的程度,尽管从祖宗到子孙,在程度上显得一代不如一代,山鬼依旧像赶不开的空气,包围着山里人,规范着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山鬼的威力具体表现在一些禁忌之中,人人都得遵守,谁违反谁准倒霉,因违反禁忌而得祸的事被说得活灵活现。在山里人眼里,禁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实实在在可以兑现的东西。譬如上山伐毛竹,砍下的第一件毛竹(用篾捆好扎好三、四支毛竹称为一件),不可立即拖运,要用一段小竹杆拄起根部这一端,靠在不打算砍伐的毛竹上,再挂上一双草鞋、一串纸钱,等到全部毛竹砍运完毕,才焚化草鞋纸钱,将这件毛竹拖下山来。据说山上神少鬼多,难免有个别胆大的鬼钻空子害人,草鞋是专门捉鬼的“白无常”穿的,挂起来能吓鬼,纸钱是利诱穷鬼不要胡作非为,否则人不烧化,穷鬼就别想得到它。同其他山区一样,山上想和别人说话,须先发出“呜”或“呜呼”声打招呼,不可唤姓名,被唤的人也不可应声,否则山鬼就要依照姓名害人。传说从前大溪村有几户人家,搬到大荷山花木坑居住,其中有个姓姚的人,晚上听到门外有人唤他的姓名,他应了一声,就开门外出,从此一去不归,音信全无,后来发现他死在平顶山,村里的人,包括死者家属在内,都相信因犯了被唤不可应声的禁忌,以致遭山上鬼怪之害,故不向政府报案。
大家深以此事为戒,遵守上山的禁忌更严格了。夜晚上山捕石蛙,走路只进不退,这样捕得的石蛙是山鬼所赐的,未捕得的石蛙是山鬼放生的,所以从原路回来时不可再捕,如果贪心犯忌,山鬼就要惩罚贪心人,使其迷路,在老地方走圈子。还有,在山上劳动的男女,若互相爱悦而避人幽会,一忌赤身暴露天光下,二忌下体朝向山峰,以免秽及天神及山鬼。应选择草木荫盛处作欢场,头部最宜朝向山峰,否则会引山神发怒降罚,轻则下体生疮,重则失足坠崖,说不定会丧命。
对崇拜山鬼的人来说,山鬼的力量既神秘又强大,并企求能更神秘,更强大,能更有效地保佑自己,故观察和分析事情,常会心不由己地带有倾向性,将偶然的遭遇当作必然的规律,是山鬼左右大家命运的力量显示。现在的浙江西北部的山里人,对山鬼畏而不亲,与对古代氏山神族图腾祖先神的崇拜,已大不一样了。
3.伐木者的山神崇拜
如果说山鬼是山里人主要禁忌、防卫的对象,那么,山神则是他们尽心尽意加以敬奉的。由于伐木有很多危险,“四头棒”、“飞棒”都可致伤毙命;砍伐完后树放不倒而出现“飞殿”、“搭黄瓜架子”、“吊死鬼”等情况,则更是容易出现伤亡事故。为此,大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的“木把”(东北伐木者的俗称)们十分敬畏和崇拜山神,认为山林被山神主宰。有趣的是,深居密林的山神爷,既无庙宇,也没有偶像。一般是用三块木板或石头,在伐木营地附近垒个小屋。若找不到木板、石块,便可用斧子在大树上砍个“企”形图案,以作山神庙和山神爷。据说,三块石头,正中一块是虎神,祭了它才不会遇上猛虎;左右两块,一个是五道神,一个是土地爷,均能消灾免难。原来木把们心中的山神爷就是老虎。接着,砍两支松明当蜡烛,折来一把山草当香火,插于庙前,再摆上馒头、糕点、酒菜等供品。然后,由“木把”的掌柜率众跪地祷告:“山神爷老把头,木把们给你叩头了,你就替我们消消灾避避难吧。”祭毕,木把烧起臭松和骨节草,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以作鞭炮鸣放。
如今,东北伐木虽已实现了机械化,伤亡事故大大减少了,但作为风俗的传统影响,人们还是不砍伐刻了山神庙记号的大树;不坐到未烧完的木材上,说那是火神爷的脑袋;早晨起来后也不准说晚上做了什么梦;吃饭端碗时不许把大拇指放在碗沿边上;也不坐被视为山神爷位子的树墩。
南方山区民间也信仰山神,但砍伐崇拜之俗就大相径庭了。浙江一带旧俗上山砍树,一般都腰插纸马,到达目的地后,将纸马用石块压在树旁,以祭山神,祭祀方法比较简单。在传统的砍树季节开山砍柴时,砍柴人要带三炷香、三张黄纸到砍柴地烧过、拜过,请山神保佑砍时平安,下山轻便。湖州地方上山砍毛竹时,从祭山神开始就不能随便讲话,天天如此,一直到砍完全部毛竹为止。两人在山上呼唤,都只能用“哦……哦……”的声音,互相应答,或用刀柄敲敲毛竹,不能互叫姓名。若是有人说了话,叫了人,出现了刀伤、蛇咬、跌伤等事故,便由此人负责医治,并要请酒。若大家遵守了山规,还出事故,则以为是祭山神不诚,必须重祭。
各地民间在砍伐成片树木时都比较慎重,要用方块肉、鸡或素食祭拜山神,祈求平安顺利。有的地方大批伐树时,要在山上用巨石三块,下放二块,上横放一块,在巨石前祭山神。如果砍伐时期较长,每月初一、十五两天都要用三牲祭山神。砍较大的树时,伐前要用墨汁在树身上定一点,弹三根黑线,以镇压树神不使作祟。有的还要举行祭树神仪式:选最大最粗的树为神,伐木工把工具放在树神下,祭后,开第一斧的人不能说话,向树神三跪三拜,开第一斧后,仍把斧头放在树神下,等树全部伐完后才能取回。而砍伐水口树、坟头树、龙山树、寺庙四周的树则更加慎重,一般要备三牲福礼,虔诚祭拜,有的砍伐前敬树神,除点香烧纸钱外,还要在树的周围撒鸡血和米,请树神退避,以免斧砍神身,并雇一老人先砍三斧。有的以白雄鸡斩头,将鸡血涂于树身,并雇乞丐先砍三斧,祭拜的肉要分给树周围的有关人家。
4.猎祭与猎忌
狩猎,这种原始性和惊险性浓厚的经济生活,在人们远没有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时代,积淀和传承下来许多崇拜和禁忌之俗。
狩猎者出猎前要举行祭祀、供献猎神的仪式。未进山之前,要宰鸡祭山神。进山后,到了猎场,还要用鸡、鱼、猪肉三牲礼供献猎神。彝族供的猎神叫赵彝,供祭时选一块奇险的石头当神位;傈僳族则尊卡玛女神为猎神,供祭时,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五色花纸,系上一尾小鱼,再以一支青松毛为神位;白族及汉族则用纸钱作神位;祭祀时,傈僳族猎人禁忌使用茶叶敬猎神,传说茶叶能遮住猎人的眼睛,使之打不到野兽;佤族头次使用狩猎工具,也一定要先祭山神和火神,同时还要祭鸟兽之神。否则,以为会打不到野兽野禽;壮族村民围山打猎前,必须祭祀山神,求山神庇护人身安全,让人们猎获到野兽。路过神山时,骑马者下马,戴帽者脱帽,背小孩者解下小孩。任何人不得对山神便溺。禁忌动神山上的树木、土石;鄂伦春族崇拜山神“白查那”(“白那恰”)。“白查那”是专司狩猎业的神灵。据说他日夜在山林中走动,所以猎人进山,绝对禁止高声喧哗,不然就会触犯“白查那”。在山岭路旁刻有“白查那”形象处,猎人们每经过这里,都要叩拜,敬烟献肉,或在“白查那”嘴边上抹点兽血。据说这样能使狩猎成功,打到更多的野兽,否则,将一无所获。鄂温克族也敬山神,并忌向山神树小便。
湖北神农架猎人的旧俗认为,打到一只野兽,特别是比较稀有的野兽,都是山神的恩赐。因此出猎的时期要占卜吉日,若按一定的口诀推算是不宜狩猎的日子,就决不出猎。若是吉日,出猎前,要烧纸钱,供上鸡肉和馒头,并跪拜、祝祷,有趣的是在行祭礼时还要翻斤斗。猎获时,不能随意抬取,必须用木签把猎物的脚钉在地上,祷告山神,感恩戴德,然后才可抬走。如若不照此办,俗谓下次打猎就会倒运。
有些民族打猎时,还怕受到其他人的灵魂或者猎神以外的神灵的干扰。例如,珞巴族狩猎时忌讳碰上外人。万一碰上外人时要迅速悄悄走开。下捕兽器尤忌外人看见。否则,以为外人的灵魂会把猎物夺走,致使狩猎无获;佤族主人没有用过的枪弩,禁忌借给别人。否则,主人自己将打不到野兽;鄂伦春族在出猎时禁忌在篝火上洒水,俗以为洒水会触犯火神,也会使狩猎失败,打不到野兽。
六、手工业的凶兆观念及禳灾方式
手工业在人类社会生产分工中是很晚出现的行业。也就是说,是从野蛮时代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才诞生和发展的。人们虽然对自然的神秘感、依赖感减少了,但是在生产中的危险感、恐怖感仍然存在。尤其是处在小生产状态下的古时人,不但安全措施较差,而且安全知识也相当贫乏,因此对自身安全存在着忧患意识是很自然的。为求得心理的平衡、满足,手工业者也施行一些祭祀和避忌行为。
1.木匠“魇镇”的迷信
“魇镇”又称“厌胜”,这是古代工匠生产与巫蛊迷信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迷信做法。如果工匠对雇主不满,又难以发泄,受这种迷信心理的驱使,于是就做一番手脚,埋下所谓的“镇物”,用以报复。
据《西墅杂记》记载,有一姓莫的富户,自从造好新房后,家中始终不得安宁,每至深夜,室内角力摔跤之声不绝,人人惊诧不已。莫姓富户百般无奈,多次请人禳祓而无效验,只好把房子卖给别人。房子被拆毁以后,只见房梁之间有两个木刻裸体小人,作角力状,深夜的摔跤声即由此而来。又有一韩姓人家,造房之后家中死丧不绝,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院墙毁蚀,偶尔发现其中有一方用砖盖着的孝巾。拿掉之后,家中从此就太平了。这就是工匠所设下的“镇物”。尽管这类记载荒诞离奇,不足为信,然而,木工瓦匠在造作时暗设镇物,诅咒雇主家败人亡的“魇镇”心理,至今残存。
在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工匠所下的镇物往往是生活中某种人或物的“模拟物”;而这些模拟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情状、动态,又会给这所屋宅带来类似的结果。
实际上,工匠们的这种“魇镇”术,乃是由原始巫术发展而来;同时,认为通过模拟的相似物便能使人致病招灾的观念,也是上古初民原始思维方式在后世人头脑中的遗存。英国近代着名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他的《金枝》一书中曾经指出:巫术所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同类相生”,或结果相似于原因,称“相似律”;一种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称“接触律”或“感染力”。基于这两种规律而产生的两类巫术形式,前者称“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后者称“接触巫术”。我们这里所谈的“魇镇”术,正是“顺势(模拟)巫术”的一种,它是由原始思维的朴素联想发展而来,认为“彼此相似的东西可以成为同一事物”,因此,试图通过相似的模拟物,对屋宅主人施加巫术影响,因而使其招致灾祸。这种做法在我们今天看来,其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的资料记载中,这种“魇镇”术都被说成是可信的事实,也就是说,不光是在造屋时下镇物的工匠们,而且连传说的记录者们,也都确信这种“魇镇”术确会具有预期的效验。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在现代人的科学思维方式真正确立之前,原始思维方式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过根深蒂固的影响。
“魇镇”术如此流行,也与木匠们视之为辟邪的手段有关。古时候,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对于临降于自身的灾祸疾病无法予以正确的解释,认为是由某种神秘力量所造成的,很难预防或避免。虽则如此,但却能通过某种方式将其转移到别的地方或别人身上,于是便有民间巫术中的“移灾法”或“移病法”出现;而“魇镇”术有时候实际上也是被作为工匠自身灾祸的“转移术”来施行的,如果不将魇镇术施于别人,则将祸及自身。如果以此来反推之,那么如果已将魇镇术施之于人,则可确保自身无恙——因为已将自己可能遭受的祸病“移转”到了别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