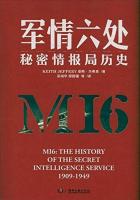进入癌症患者角色之前,我便得知,我患癌后是死是活,活多久,医生的决定权并不太大,我本人的决定权更是不太大。我已养成习惯,凡遇到事关自己的利害,但我并不掌握决定权,或掌握着很小的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决定权的事时,或说了无足轻重的事时,我就不上心,不关心它,或者不怎么关心它,并且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事情朝不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有一个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最不愿意接受的结局。比如在遇到调级、调职、调工资、调住房等问题时,我就持这样的态度,“祭”起我的这一“法宝”来。我觉得我这样地看事处事是对的,一者是适应了事物运行的规律,再者是我可不受大的精神损害,有时候我还会获得惊喜。我经常劝人别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不要干那些胳膊拗不过大腿的蠢事,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癌症很凶恶,致人以死命力特强。我敢说,没有一个癌症患者不希望自己能逃得这一劫的。事实当然是使很多的患者的希望要落空、要破灭。不然的话,癌症就不叫癌症,就要改名叫疖子,改名叫脓疮。遇到癌症这样麻烦的事,况且又是中晚期胃癌这样的麻烦事,我自然会按照我养成的习惯办,做好最坏的打算:了不得是个死。倒霉只倒这一次,不会再倒第2次死的霉吧。总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说是老顾你只死于癌症1次,没有完成任务,还得重新活1次,再死于癌症1次,才算圆满完成任务,永远安息。
瞎猫碰到了死老鼠。我干对了,原来我的行为在理,在医学之理,在医学之说,那就是患癌症后怕死怕不得。有医学权威说,在癌症的死亡者中有1/3是被吓所致。有医书介绍,整日恐惧和伤感的癌症病人生存时间短,治疗效果不好。在临床上,许多观察都发现,消极悲观的癌症病人治疗效果差,药物副作用大,并加速病情恶化,预后往往不佳。悲观失望,无异于坐以待毙。
恐惧、绝望、压抑等之所以为癌症病人所不可取,有医家认为:情绪低落后血液中免疫细胞减少,杀伤异物的能力降低,干扰素及其他许多与控制癌细胞生长的淋巴因子水平均不同程度的降低。这一切均有利于癌细胞生长和扩散。又有医家指出,长期恐惧、绝望、压抑的癌症病人自然会导致体内的细胞和血浆体系中的生物能量的活泼,结果使自己的体内成为癌生长和肿瘤扩散的肥沃土壤,正像流动的小溪通过连续不断地运动使其中的水纯化一样,在不流动的池水中,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生长则加快。
努力开挖能活的理由
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恐怕不会为人人所接受的。但是,求生的人要比求死的人多得多,就不会有人持疑议了。我有着强烈的求生欲,因为我已活得尚可,在我们的国家,接着活更有味道。在为即将有可能发生死的问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我努力地去寻找我不至于就死于胃癌的有利因素,更进一步地更积极地调整我的心理,斩杀胃癌,免遭劫难。结果发觉有利因素不在少处,我的夺命之战胜面较大。我胸中生命长久的希望的太阳高高地升起。
凭“第六感觉”,我发觉我不会死。在患胃癌之前,我连死的念头都未闪过一下,怎么现在一触及死就会立刻死去。不可能,坚决不可能。这次出现死的危机,不过是死神给我敲一下警钟,开个玩笑而已,并不准备真的就“下拘票”。我为了追求成就感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拼命地榨取它、消耗它,死神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忍无可忍之下用癌症来吓唬我一下,让我明白没有了健康就什么也不会有。往后要记取教训,切勿执迷不悟,我行我素。所以,我这次患癌只是有惊而无险,不必多虑。
小时候,奶奶对我说:苦命的人想死也死不了,因为你命苦,苦还未受够,债还未还清,怎么就会死呢?我觉得我就是奶奶所说的那种苦命人。我算了算账目,我的苦远未受够,“债”远未还清。乡下的父母累死累活供我上大学,我得回报他们。父亲早已故去,母亲却健在,我不能先她而去,置她的生计于不顾。儿女们更是嗷嗷待哺,我得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还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大学生,谋取生活的出路,报效国家。
我的一些亲人,如妹妹、堂叔和堂弟等,虽已得过我或多或少的关照,但杯水车薪,微乎其微,拖欠不少。众抬一好抬,一抬众难抬,了结“欠债”的心愿,有待较长的时日,10年、20年不行,也许是30年后的事情,我的苦日子还长着呢。
我们家男人的寿命都不长。我爷爷刚到60岁就寿终正寝。我父亲在53岁时撒手西归。据说,我爷爷的爷爷和爷爷的寿岁还不如我爷爷和我父亲的长。我们家里的人都企盼着后来的男人能在寿岁方面超过先前的男人,出个活到70岁、80岁的男寿星。我们家里的人自然祝福我能成为寿星型的男人,为我们家死去的和活着的男人争口气。我觉得我能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赶超任务。我现在有着优越而先进的医疗条件作保证,反倒活不过我祖父和父亲,岂不是笑话,岂不是天下无公理可言。我不会因这次癌症就死的。
我这人命大,特经死,一次的死,不会死彻底,且能死几回。小时候我曾得过两次恶病,每次都到了离“丰都城”只有半步之遥的地步,硬是未进得城去,成为“丰都城”的城民。
1969年出差新疆时,有一天两次遇到险情,每次都差点儿把老命撂在伊犁地区的边关哨卡,终究还是活着回到了北京。
一次在通过一段路况极差的盘山公路时,司机要是一犹豫一停车,连人带车就会滚下万丈深渊,包括我在内的车上4个人就会喂了虎狼。鬼使神差,司机猛踩油门,军用吉普车像受了惊的野马一般狠命朝前一窜,窜上了安全路段。又有一次,在通过一座窄小的木桥时,司机疏于减速,车子偏离方向,一心要跳河“自杀”,让我们4个人也跟着去填鱼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咯噔一声响,车后轮卡在缺了一块木板的桥缝中,动弹不得。死了几回未死掉,我就断定我是个“经死型”的人,往后还能“死”几回。我现在就烦神自己会因癌症真的死去,是没神找神烦,太多的超前意识,使顾德如已不是顾德如,成了典型的一个林黛玉,多愁善感。
我是一个穷孩子,长期过着拮据的日子。但是,我也曾“阔绰”过,我曾是一个健康的“富豪”。我母亲除早产、流产外,正儿八经地生下来13个孩子,留存下来的只有我、妹妹和弟弟3个人,其余皆夭折。这说明我和妹妹、弟弟是经优胜劣汰法则检验后保留下来的人的“精品”。我食量大,发育好,长得快,到高中1年级时已1米8左右。如此“巨人”,在我们那一带是很难找的,算得上珍稀物种。我只在幼小时生过两次大病,从读书上学到40岁这一段时间,我的病历表上没有医生填写过的字,我不知道门诊部、医院是管什么事的衙门,大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青年时代,我觉得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我的筋络里、血液中涌动,觉得有无穷的兴奋、畅快在我的肌肉里、骨骼中激荡。我似乎能听到我每时每刻因长高长壮而发出的啪啪的响声。大概是因为身体棒吧,我才有幸在解放军报社吃了七八年的夜班饭。我把我的身体比喻成一棵生长良好的粗壮大树,一次的狂风袭来,虽也能吹掉它的一些叶子,折断它的几根枝子,使它的根部泥土有所松动,牢固性受到一些影响,但要想将它连根拔起,那是白日做梦。像类似癌症这样的重病、恶病我还能经受几次,然后高兴了,我才会考虑病死的问题,自动为下一代人在这个世界上留出个空位子。
患癌之初,我也认为被医生确诊为癌症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后来我发觉医生判人死刑和法官判人死刑敢情是两码事:法官判人死刑,说一不二,到时候准把你拖出去在你身上钻孔不可;而医生判人死刑的权威性就不如法官的高,高兴了你可以不把它当回事,拒绝“服刑”,不会受到追究。然后,你可逍遥法外,像往日一样放心大胆地活着。我术后不久碰到这样一件事。我的一位上级的老母亲被某医院确诊为肝癌,并且已是晚期。这位上级认定医生已给他老母亲下了死亡通知书,便将他在京外工作的弟弟叫来北京,和老母亲作最后的告别。老太太却硬是和医生较上劲儿,几年都不走。后来竟痊愈了。亲友们也陆续向我提供了许多癌而不死的例子。其实,许多的医生也不认为自己说谁已患癌症就是给谁判死刑。
早期我接触的一些医书记载道,像胃癌、喉癌、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癌症患者如早期发现,及时治疗,生存率可达百分之二三十;中晚期发现,生存率较小;晚期发现,生存率更小。还有这样的记载,在晚期癌症患者中,竟有不治自愈的人。后来我又读到这样的文字:“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癌症已不是不治之症,早期癌症的治愈率可达40%以上,5年生存率达80%以上。晚期癌症5年生存率也在10%左右,有的长期带癌生存。”对癌症杀伤力的了解,使我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打从我离开娘肚子那一刻起,直到这次我患癌症,幸运的女神一直伴着我。由于家穷,我10岁才上私塾。从上私塾到小学毕业,我曾两度辍学,却都因有了好心人站出来说服了我的父母,才使我重新捡起了课本。要不是解放了,要不是学校设立了助学金,我根本不可能读完中学读大学。大学毕业分配,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关系一个人终身干什么的重要时机。我大学毕业分配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单位不要人,大学生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据说,只是在中央的指示下,解放军报社才奉命派人到复旦大学新闻系调6个人从军。解放军报社被同学们公认为是所有要人单位中最理想的单位之一。最理想的单位当然要挑最理想的人去。我是一个最不理想的人,是一个被一些人私定为名利思想严重、坚持走“白专道路”的顽固不化的人。可我很“馋”这个单位,在高中读书时,我就立志将来要当一名随军记者,像前苏联的波列伏依一样的随军记者,要是能去这个单位,不就圆了我的梦吗。我也顾不得羞不羞了,就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上赫然写上“解放军报社”5个字。我还真心想事成了。事后我认为这是幸运女神对我的又一次钟情,舍此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得通。我的癌症生在我成为解放军军官之后,也是我很幸运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是后来的变化,我像父亲一样在家当农民,48岁上得了中晚期胃癌,不要说1个顾德如,就是10个顾德如,也都一一“报销”了。癌症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狗杂种,但它毕竟没有凶残到艾滋病那种程度。这就使我来了情绪,心想:幸运女神与我相濡以沫几十年,在现在事关去留的我的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她不会狠心地弃我而去,置我的死活于不顾,而是要从癌症那里弄一个得以治愈的指标给我。我大可不必庸人自扰,只需等待幸运女神交给我指标的日子的到来。
虽然我和妻要求对我的中晚期胃癌问题进行“平反改正”未果,但我仍坚持不信医生的诊断是准确无误的,认定我的中晚期胃癌是一桩冤案、错案。我不是没来由的。不是常说吗,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医生出错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诸如将药棉、胶布、手术钳子等忘了从被手术者的内腔里取出,误开药方、错用了药而致患者命丧黄泉的事例,不时地在报纸、刊物和屏幕上有所披露。我的一位上级的说法就更有些耸人听闻了,他说:“哪一个医生的成功、出名,不是用许多无辜病人的生命换来的!”我想,私下里怀疑医生误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怀疑对了,岂不更好;怀疑错了,将错就错,起码可以自己欺骗自己,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只要不是另有他图,藉以向医院索赔,就可以怀疑,并且一直怀疑下去。这何尝不是抗癌的一“招”。当然,这是一个“怪招”。医生们就是知道了我在使着这一“招”,也不会有太多的反感吧:他们只希望我能活下来,哪会计较我使的小小恶劣伎俩呢。
我努力地挖空心思地搜寻各种各样的我能活下去的理由,甚至有些近乎荒唐、滑稽的理由也不忍心舍去。我并因此树立了我一定能活下去的坚强信念。我只是觉得这样做好,比悲观绝望好,就这样做了。我的行为是完全自发的,是完全属于经验主义的。后来我知道,这正是医家医理对癌症病人所期望的,是对癌症的康复相当有效的。有文章说:对患癌症后坚信自己能活下去和患癌后悲观绝望的两种人,科研人员进行追踪研究,发现确诊的癌症的各种条件(包括癌症类型,发现时间,身体一般状况,医疗条件,等等)基本相同的患者中,能勇敢地面对现实,态度豁达,积极配合治疗的人,比情绪低落,整日恐惧和伤感的病人生存时间长,治疗效果好,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最终能彻底战胜癌症。另有文章写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觉得自己患癌症无救的病人和一个认为自己不至于就死于癌症的病人,他们虽年龄相仿,患有同样肿瘤、病情严重程度及治疗计划也无不同,但他们的治疗效果却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心情不一样。有许多学者甚至着书认定,树立要活下去决心的癌症病人是能夺回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