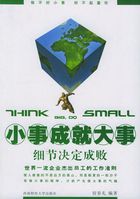第六节其他部落的源起
了解了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拉施特记载的可信的事实了。其他部落也有他们各自的发展史。我们主要考察的是12世纪中后期,也就是成吉思汗刚刚出生的那段时间。
塔塔儿人在蒙古地区的东边生活、放牧,经常在客鲁涟河南边或东边和中兴安岭之间出没。一般人觉得他们是通古斯血统,但伯希和经过考证确认他们应该是蒙古系。公元731年-732年,在和硕柴达木的阙特勒突厥有一块石碑,碑文中所说的一个有时称九姓塔塔儿,有时称三十姓塔塔儿的联盟部落,应该就是指塔塔儿人。在12世纪,他们分为了几个部落,并且成为一个组织不算紧密的联盟,包括察阿安塔塔儿、阿勒赤塔塔儿、阿鲁孩塔塔儿等。
成吉思汗的氏族和跟随他们一族的蒙古人,在塔塔儿人的西北方、客鲁涟河和斡难河上游之间放牧,这些部落主要是泰亦赤兀惕部落。伯希和曾说过,“蒙古”是室韦各部落的其中一个名字。他们在客鲁涟河下游的周边地区和兴安岭的北部游牧,唐朝的时候好像就叫作“蒙瓦”或者“蒙兀”。伯希和认为,“室韦人几乎肯定是属于蒙古语族的”。
喀尔喀(合勒合)河穿过捕鱼儿湖,汇入客鲁涟河。捕鱼儿湖的旁边,即塔塔儿人生活地区的东边,在12世纪的时候住着翁吉剌惕人,他们与成吉思汗一族和泰亦赤兀惕关系都不是很密切,所以可以和这些部落互通婚姻。
成吉思汗一族的祖先因为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之间,他们部分是猎人、部分是牧民。成吉思汗本人也是这种生活方式。拉施特认为,泰亦赤兀惕是蒙古的主要部落,他们和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因为他们生活在森林里面,偶尔会被人家叫作“林木中人”,只因为生活在森林里的部落文明程度还不如草原牧民。兀良哈部落也生活在森林里。拉施特说:“他们以广阔的森林为家,不住帐篷,没有牲畜,以狩猎为生,轻视游牧民族。用树枝编成房子,其外用桦皮作为遮盖。将木板系在脚下,叫作‘察纳’,持手杖于雪中行走,像撑桨划船于水中,用于在冬天进行雪中狩猎。”斡亦剌人也是蒙古族裔,他们也是在森林里面生活,住在贝加尔湖西南面。斡亦剌的名称意思是“亲属”“同盟者”,至于他们族群的血统是由什么成分构成,就没有办法考证了。
另外一个居住在森林里面的猎人部落则是蔑儿乞惕人,他们可能是6世纪时拜占庭历史学家们口中的木乞里人。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以至于他们的血统是属于蒙古还是突厥都没办法确定。他们生活在贝加尔湖南边,色楞格河下游之上,与蒙古人杂居。根据事实判断,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从一个蔑儿乞惕人首领处抢来了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而另一个蔑儿乞惕人首领从成吉思汗手中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所以蔑儿乞惕人也可能属于蒙古系。赤洛克湖沿岸即现在的脱只-哥萨夫斯克附近的札剌儿人却是从事游牧的,他们应该属于突厥系,在蒙古人传说中的英雄海都时期曾经臣服于蒙古人,渐渐成为蒙古部落的一部分。
第七节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
客列亦惕人在蒙古人的西方生活,他们居无定所。我们考察黄金一族的历史,他们的领袖一般都在土拉河的沿岸黑森林驻扎着。但是根据拉施特的说法,他们放牧的范围很大,东至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甚至到达了长城附近。客列亦惕人与乃蛮人活动区域的西方是一条河,《秘史》记载,这条河叫“涅坤”。人们的研究认为,他们生活的腹地是上鄂尔浑河、翁金河和土拉河附近,属于突厥族系,并不是蒙古人。伯希和先生认为,“现在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属于传说中的原始蒙古民族,也并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受到突厥人影响的蒙古人,还是被蒙古人同化的突厥人。但许多客列亦惕人的称号是突厥称号,而他们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脱古鲁勒的名字也更像是突厥名字,而不是蒙古名字。”叙利亚研究者巴·赫伯拉厄思认为,客列亦惕人是在公元1000年稍晚成为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的信徒。根据传说,客列亦惕人的一个国王在草原里头迷了路,圣瑟治显圣让这位国王得救,当地的信奉基督教的商人怂恿他,让他去请马鲁地方的聂斯脱利大主教埃伯耶苏派遣一个教士给他洗礼。巴·赫伯拉厄思还找到了埃伯耶苏写于1009年寄给聂斯脱利教教长约翰六世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封信件的内容表示,有20万客列亦惕人还有他们的国王都一起受到洗礼。但是,伯希和却认为时间有可商榷的地方,还有“客列亦惕”几个字,也有可能是巴·赫伯拉厄思后来加上去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12世纪客列亦惕的统治者已经转而信仰聂斯脱利教,也有了基督教名字。
根据这一证据,客列亦惕人很有可能曾经盘踞在突厥-蒙古的腹地。也就是鄂尔浑河上游和土拉河上游,肯定也想要借此为跳板争夺这一地区的霸主地位。在成吉思汗之前两代,客列亦惕人的首领马古思不亦鲁(基督教名为“马可”),与戈壁东部支持女真人的塔塔儿人进行了一场战争,却不幸战败被俘虏。后来,他被献给金国国王,受木驴刑罚而死。他的妻子忽都克台亦里克发誓为丈夫报仇,于是带着100袋游牧人最喜欢的由马乳酿制而成的饮料“忽迷思”来到塔塔儿首领纳兀儿的住处,说要给纳兀儿送礼。实际上却在每一袋“忽迷思”中都藏着一个战士。在纳兀儿设宴款待忽都克台亦里克的时候,100名战士突然出现,刺杀了纳兀儿。土拉河流域是客列亦惕人活动的中心地带,而塔塔儿人则在客鲁涟河下游的南岸活动和生活。可以想见当时客列亦惕人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蒙古地区的东面。马古思死后一直到脱斡邻勒掌权的这段时间,客列亦惕人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忽儿察·忽思和古儿罕都是马古思的儿子,后来忽儿察·忽思继位,传给儿子脱斡邻勒。他在成吉思汗的帮助下,在蒙古地区成为霸主。
乃蛮人生活的地区还在客列亦惕人的西方,也就是上鄂尔浑河和纳伦河以西的地区。杭爱山西部即现在的乌里雅苏台地区,阿尔泰山的乌布沙泊以及科布多地区,也儿的石湖和斋桑泊都是乃蛮人所管辖。伯希和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乃蛮很可能是被蒙古人同化的突厥人,他们的族名虽然很有蒙古味道,但他们的各种称号则是用突厥语言。”乃蛮人相信的宗教是珊蛮教(即萨满教,曾经长时间在中国北方各民族流行)。志费尼则认为他们之中也有人对聂斯脱利教有所接触。居住在他们南方的畏兀儿突厥人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化。成吉思汗的前辈,乃蛮人首领亦难赤·必勒格(《拉施特书》的叫法是“亦难赤埃格都忽汗”,在突厥语中,“亦难赤”意为“可信赖的人”,“必勒格”意为“智者”)十分勇猛,“敌人们从来看不见他的背影和马屁股”。
萨满面具
萨满教是因其神职人员——“萨满”而得名的。萨满师在每次仪式时必以火献祭,作法时身着萨满服,手执萨满鼓、精灵佛像等,通过唱歌和一系列的原始舞蹈与萨满教派的神或仙进行沟通。图为萨满面具,它同萨满服一样,也是萨满师作法时的通灵工具。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地处西南的部落,也有着一定的文明程度。首先要说的是畏兀儿突厥人,他们在塔里木北边的绿洲、别失八里、吐鲁番、库车等地居住和生活。受到佛教和聂斯脱利教的交互影响,他们产生了一些文化成果。另外要说的是哈剌契丹人,他们是契丹人的一个分支族裔,在前文已经讲过,他们离开中原,在突厥斯坦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
第八节蒙古部落的解体
畏兀儿突厥人和哈剌契丹人生活在草原的南边或者蒙古本部的境外。其他的蒙古地区与突厥人或回鹘的汗王们统治时期相比,文明更加落后了。中古初期“斡耳朵巴力”或“宫帐城”等东西,在塔塔儿人、蒙古人、客列亦惕人或乃蛮人出没此地的时候,消失殆尽。不过,突厥人或回鹘人所称的“城”实际上也只是可以移动的营帐,蒙古人把它叫作“古列廷”(蒙古语中,古列廷有“圈子”“栅栏”“固定或流动的营盘”等意思),这样的营帐,头领到哪里就往哪里迁移。但是这样的移动营帐“城市”,在成吉思汗出现的年月都已经绝迹。蒙古的社会组织是家长制的氏族,以“斡孛黑”著称,以及其狭义“牙孙”即支族。到了成吉思汗早年,这样的社会组织基础已经开始崩塌,变得只是以家族作为单位存在。这就让人联想到分散居住的澳大利亚斯克鲁布人。在12世纪的蒙古草原上,我们很少看到营帐和车辆组成的移动“城市”,常看见的只有“阿寅勒”(很少家庭组成的固定营地,多数只有一个家族)。成吉思汗小时候,他的长辈抛弃了他和他母亲、兄弟,他们的生活很艰苦,靠钓鱼、打猎维生。这实际就是“阿寅勒”的一个实例。
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论点并不能让我们信服,但是,从事实上看,成吉思汗的崛起与蒙古社会的等级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蒙古贵族称为“把哈秃儿”或“把阿秃儿”,即“勇士”或“那颜”,大多数为“那雅特”即贵人,或称“薛禅”即贤者。蒙古一般平民叫作“那可儿”,大部分是“诺古特”。成吉思汗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就源出于此,分为战士和亲信。蒙古的一般居民,叫作“哈剌出”“阿拉特”。奴隶则是“孛斡勒”“兀纳罕-孛斡勒”。理论上,大汗统治着所有的蒙古臣民。森林里面生活的部族比较喜欢用“别乞”这个字眼,如斡亦剌人、蔑儿乞人(“别乞”意为强壮、结实和强有力。符拉基米尔佐夫将女性称为“别姬”)。由于部落争斗,有的部落会被击败而奴役,有的则会请求庇护而成为藩属,因此各个部落之间也有明显的等级。札剌儿人和成吉思汗的祖先的关系,以及翁吉剌惕人和斡亦剌人向成吉思汗输诚(意为献纳诚心),也是这一种情况的有力证据。
实际上,在12世纪中叶,蒙古草原已经混乱不堪,而且政治社会结构松散,似乎随时会崩塌。泰亦赤兀惕和若干其他部落里已经没有领袖来控制局面。各部落陷于混战泥潭。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和成吉思汗的争斗,以及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争斗都是这一背景的佐证。从成吉思汗的情况可以看出氏族和支族互相争夺牧地和营地(“嫩秃黑”)的情况:如果某部落的首领死去,剩下妇人和幼子,那么这一个家族的营地很可能会分裂。因为蒙古人只能和外族通婚,所以他们要与其他部落的异性结亲,或是谈判(如成吉思汗的婚姻),或是抢夺(如也速该的婚姻)。蒙古人基本上以此维持平衡:也速该把蔑儿乞人首领之妻诃额仑抢来做妻子,蔑儿乞人也把成吉思汗之妻孛儿帖从他手中抢走。拉施特对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的情况的描述是:“儿子不再听命于父母,弟弟不再服从兄长,妻子不再顺从丈夫,富裕者不再帮助本部落的首领,盗贼、抢劫、叛变者四处可见。牲畜和马群毫无安全感,常常因过度疲乏又得不到休息早早夭亡。到处都是混乱的情形。”也许为了表彰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功业,这段话有所夸大,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根据《秘史》的记载,成吉思汗成长的时代,确实是混乱的、凶残的、黑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