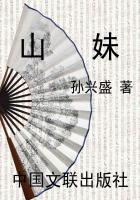在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媒体对在美国的中日两国侨民的不同反应的报道,颇值得我们思考。
1894年7月3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的前一天,《旧金山早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讲述了唐人街华人对中日战争的反应。这篇题为《唐人街的华人》的报道如此写道:
如果有人以为唐人街正在为来自北京与神户的战争消息而处于激动的痉挛状态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不了解唐人街的华人。即便是中国的领事晚觉也睡得非常好,而且,按照东方的传统,他还会在下午小睡一会儿。
《旧金山早报》的记者原本想直接采访领事,但是,因为这位领事的英语水平不够好,他转而采访了领事的秘书王先生(Chang Liang Wong)。
文章写道,王先生体格肥胖、为人和蔼可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对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感兴趣。当记者问他对局势的看法时,他说自己一无所知。在接受采访当天,领事馆正好收到了“盖尔号”(Gaelic)轮船从上海送来的中文报纸,但是,这批报纸的印制时间已经是两个多星期以前,而且几乎没提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说其中刊载了些微与战争有关的消息,也是为了表达了那种“麻烦将过去”的信念。
不过,王先生确实收到了一份最新的海底电报,证实了在被击沉的运输船(指“高升号”)上的两千名华人死亡的消息。
这篇报道写道,当被问及有何感想时,王先生笑了,并很快回答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告诉他战事情况前,王先生不相信在东方有任何战争。他对美国报纸所写的消息全然不信。“他把整件事当做一个笑话来看。他在膝盖上摆了一本大书,他胖乎乎的手指懒洋洋地翻着书页。每次提到两千名中国士兵溺水而亡的事情时,他都会发笑。他看上去非常聪明,但对战事完全漠不关心”。
在讲到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的反应时,这篇文章写道,对杜邦大街上“圆滑而自足的中国商人”的一份调查说明,他们普遍有类似的怀疑。他们不相信有战争,尤其不相信已有两千名华人死于沉船。即便他们相信,他们也不关心。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Sim Kam Wah公司的陈兴(音译,Chen Sing)。记者写道,陈兴的脑子是清醒的。他说,他们在当天收到“盖尔号”船送来的三封信,两封来自横滨,一封来自河北,三封信都对战事作了展望,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因为这些信件发自两周之前,他并不很看重它们,他更愿意阅读最新的电讯。因为他与日本和中国都有关系,他急切地想了解是否真的已经宣战。
陈兴如此判断局势:“如果两千中国军人死亡属实,则必然已经开战。日本一直在备战,每个月都在备战,日本是好战的。中国比日本有更多的兵船,更多的船只和更多的钱,但她不好战。日本没那么多兵船、船只和钱,但现在比以前更强大。所以,我认为日本刚开始时会赢,但最后中国会赢。”
唐人街华人对战争的冷漠,与在美国的日本侨民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引起了《旧金山早报》编辑的浓厚兴趣。因为就在《唐人街的中国人》一文的左边,编辑安排了一篇发自萨克拉门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的简讯,题目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文章写道:
上周六(1897年7月28日),许多日本人在农民礼堂(Grangers Hall)集会。他们下决心筹集大笔资金,并将资金送回国帮助军队继续与中国作战。他们委派委员们立即筹集资金。
在加州——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与日本人对战争的迥然态度,很快又引起了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的注意。9月20日,中日正式交战50天之后,这份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加州爱国的日本人》的特稿:
居住在旧金山的日本侨民正在展示爱国主义。当与中国作战的第一条消息传来,在这里度假的所有日军士兵立即销假回国作战,侨民们发出了募捐单,并筹集了4000美元,这笔钱已汇回东京作战备医疗之用。
这篇特稿写道,在加州的日本人大多是身材瘦小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城市里做活儿以支付学费,同时练习英语。这些学生决定,他们应该挣更多的钱,所以,大批学生去了乡下帮农场主采摘水果。这个工作的酬劳是每天1.5美元。他们的酬劳的绝大部分将汇给国内政府,也有部分酬劳汇给学生们的家庭,以资日常急用。
作者在文章结尾如此评论:“这些日本人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中国人很关注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负感(national conceit),认为中国能击败任何东方国家或欧洲国家。他们拒绝捐献资金,拒绝为他们的政府提供自己的贡献。”
1895年4月15日的《太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日本人的团结与爱国精神大加赞赏,称其为“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精神”。文章如此写道:
华盛顿一位军事官员在谈到中日战争时说,这场战争中最惊人的事情是日本的精神。他不记得现代的任何冲突中有过任何类似的事情。所有人都意见一致地团结了起来,所有人都渴望这场战争,准备为胜利奉献出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所有其他能量。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这种事几乎都不会有先例。
在我们自己的战争中,总会有强大的反对力量。在为统一而战时,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北方都有一个强大的“和平党”(peace party),几乎每个州都有很多“铜斑蛇”(copperheads,指南北战争时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北方的很多政治领袖合起来给政府添乱;在美墨战争期间,很多美国人反对政府;在1812年的美英战争期间,政府经常遭到反对者的严重阻碍;即便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也有很多美国“特洛伊”(Tories),他们为反独立而战。在所有这四场战争中,有如此多的公开发对者,美国的成功一定被认为是令人惊讶的。
而当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时,4000万日本人就像是一个人。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与别国交战时,几乎总有一个敌人在国内捣乱。英国进行的几乎每场战争,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对中国的战争,到在印度的镇压印度兵(Sepoy)的战争,在国内都有强烈的反对者。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似乎都是如此。
并非是说日本绝无“铜斑蛇”与“和平党”。必须补充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对爱国主义事业、对天皇——其帝国的代表——的忠心似乎有些过度。每一个强健的人都渴望加入陆军行列;每个士兵最自豪的希望是他会被置于战斗的最前线;父亲愿意失去他的儿子,妻子愿意失去她的丈夫。
在帝国议会中,有保守的、激进的以及其他派别,但是,所有人都站在一起,一致投票支持战争,足额划拨所有战争款项,支持每一项必要措施,没有论战。日本各宗教的信徒都为国出力,僧侣也跟他们一起。社会各阶级,从世袭贵胄、好战的武士(Samurai)到商人、农民、劳工以及人力车夫,都因战争而团结在一起。本国媒体——包括很多有影响力的报纸——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出现一篇破坏这个“日出之地”(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的“好战和声”的文章。整件事是显著而没有先例的。
还必须被记住的是,日本人没有奴性,同时也不是猥琐的人种。他们与那些最强的种族有相同的个人素质。他们是文明的,机智的,拥有良好的艺术感觉。他们十分勤勉,比东方世界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有事业心。他们有一部宪法,有一个比较独裁但并不暴虐的政府。即便是在旧秩序之下,他们也遵循着很多基本的天赋人权。
日本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像伊藤博文(CountIto)和陆奥宗光(Viscount Mutsu),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他们以高妙的能力进行谈判。内阁部长会议或枢密院从没有传出过不和谐的声音。自战争开始以来,掌权的这些人一直处于和谐之中。
可能最明显的事情——迄今为止所了解到的——陆军或海军的指挥官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嫉妒或阴谋。带着国旗从朝鲜打向北京的最杰出的陆军将军们,以及摧毁中国最强大的海军的日本海军上将们,似乎完全脱离那些“低级性状”(basertraits),这些性状在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之间经常出现,经常给他们自己的政府以及他们从事的事业带来坏处。
如果还有什么事情比日本指挥官之间在战时的和谐更加引人注目,那就是在购买武器或军需品时没有欺诈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经常使其他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丢脸。各种军事物资的装备业务似乎都在带着必须赢得世界尊重的荣誉感来进行,他们为所有欧洲和亚洲国家,为整个基督教世界装备出一个榜样。
这篇文章的作者感叹道,日军的纪律很难被超越!“不久以前曾在横滨停留的一位美国人说,如果说日军中有逃亡者,那他只听说过有一个,那人当时处于恋爱之中。日军队列中还没有发现一个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