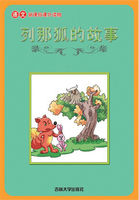自2006年到2008年在各地做生意的温州人纷纷嗅到了投资的商机,2009年我去了杭州读书,人们对温州的印象已经都集中于炒房团等各种投资团。与二十年前的武林门事件相比,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但当我自己念叨起“温州”这一词时,我首先想到的永远都不是皮鞋、房产、电器,而是邻里乡亲的寒暄和各色各样的美食。
我会想起雁荡山石壁上的火山熔岩泡,或者是楠溪江里一竿竹篙顺流而下;灵霓大堤刚建成的时候,一家人驱车采风至洞头诸岛,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肥美的海螺;或者不需要去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只需要往菜市场里走一遭,那些生鲜与虾干鱼干混杂的鲜咸味,就是我家乡的味道。
也许你们看到的是土豪挥金如土,但我看见的是那些烫着头发打麻将的老娘客,说起儿女丈夫、家长里短。
这次回家,又看见许多新建的大楼拔地而起,新区一路向北延伸到我必须开导航的地方。凌晨1点到的家,阿公打来电话说准备了大鱼大肉,中饭一定要去他家吃。
酒足饭饱后穿过长长的小巷来到奶奶家,一路上遇见很多人,一开口便问:“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有空来找我啊。”
听到熟悉的平舌音,走过建设路上的老梧桐,看见打着移动广告的红色人力车来回穿梭,我知道,我又回来了。
当我终于成长起来,成长到开始思乡,成长到一张简单的、家中的小床也足以平抚我内心的浮躁与无力,我才明白灵魂深处那温和却又无时不在的牵引。
这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城市,这是一个不俗可爱的城市。
溯洄
文 /王君心
讲故事的人用故事偷走了一个孩子。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只记得小小的镇子,旧旧的氛围,烛影般漾开和乐与安逸。讲故事的人在巷口坐下,用漫不经心的语调开始讲述一个故事。路过的人停下了,巷子里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围在巷子外头,站在低矮的屋檐下静静地听。故事很长,直到全镇的人都赶了来,也只是开了个头。
讲故事的人不动声色,沉稳、低哑的嗓音淡淡叙述。说到一句玩笑话,笑声似麦浪在人群中倒去,划破湖面般的寂静;说到悲哀处,成百上千人的叹息似落雪般扑扑簌簌,掩盖一切声息。
讲故事的人平静地结束了故事,时间已不知驻足多久。人们打着哈欠,伸伸懒腰,相互招呼着,搬起凳子散开了。等到讲故事的人收拾好行囊,空寂寂的巷口只剩下一个孩子。孩子的眼神空洞,显然是陷在了故事里,入了迷。讲故事的人不再有吹笛手的能耐,可捎走一个孩子的本事还是有的。他拍拍孩子的肩,牵起他走,没入巷子。
孩子跟着讲故事的人,涉过无尽的日子,看过无数个或喧嚣或哑然的小镇,听过无数个闪烁莹润光泽的故事。岁月飘散了他的记忆,也将他本身淡化为一个单调黯然的字符,于千万的文字述说中安静走过。
讲故事的人老了,孩子依然是孩子。讲故事的人将自己葬在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里,松开孩子的手,孑然远去。
孩子一个人走着,不知去向何方。他看不到任何事物,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觉得手腕上好像系着一根细细的红绳,牵引着他不断朝一个方向走去。这条路上不是只有他一人,他感觉得到,四周有千千万万的人影。这些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身形,似一尾尾鱼在温和轻柔的流水中,向着同一个地方游去。
渐渐地,有风凉凉地拂过眼睛,似露珠润着视线。淡淡的影像浮现在眼前,孩子举起手腕看着,没有红绳,却停着一只红色白点的瓢虫。他的手一颤,瓢虫飞走了。孩子紧跟着瓢虫,跑着,跑进一段记忆里。
这是世间最初留给他的影像。古朴陈旧的老屋,沉静的木墙与房梁,窄窄的窗口撇进一线光亮,在光线中蒙昧的尘埃中散发着岁月过渡的安详。屋外,门边贴着大红色春联。年幼的孩子由爷爷抱着,舞着胖乎乎的小手指认那些看不懂的字符。浓墨的黑似梅枝般遒劲,喜气洋洋的红让孩子无端感到欢喜。
院子里栽着奶奶精心打理的花草,酢浆草的小花是一派和煦的黄,溜过草叶的猫的身影,是熟透了的麦子般丰盈的颜色。院子里的绿似兰草般淡淡的。出了院子,一眼望见屋后的大山,苍莽雄浑的绿层累铺叠,像潮湿的苔藓覆上青石一般,柔软地染上孩子的心。起伏的远山是虚渺的青色,淡化在发白的天际。再仰头,天空是凉凉柔柔的蓝。
屋后不远处有一片竹林,苍翠的绿是无数竹叶的层叠。孩子顺着记忆跑入竹林,这是他撒欢儿的地方。脚下积了一层厚厚的枯黄落叶,踩上去一片酥软。竹林的影子似群鸟般悄然移动,不知在林间晃了多久,一只红色白点的瓢虫落在孩子的手背上。视线从瓢虫上挪开,就看见了站在眼前的哥哥,责备又宠溺地拍了拍孩子的脑袋。
回去的路上,犯困了的孩子由哥哥背着。他们绕了一条偏远的路,路的一侧是平静的水田,安稳地拢在环绕的山里。路上的行人都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像是过日子。夕阳在天边的云堆里晕开柔红,落在水田、屋檐、行人身上的却是清透明净的、粼粼闪光的金色。黄昏的气息充满倦意,红色瓢虫晃过眼前,孩子沉沉睡去。
醒来,又回到了独自一人的路上。
揉揉蒙眬的双眼,已经能看清四周的人,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踱去。再远一点儿,背景是柔和的光雾蒙蒙地融成一片,分不清远近,也辨不出距离。
右前方静静地走着一位老人。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浅褐色的朴素着装,微微驼背,拄着一个木拐杖。孩子走上前。讲故事的人很少与他对话,日复一日的沉默似乎绊掉了他的声音。现在,他尝试了好几次,终于断断续续地问出了声:“你好。请问,我们这是去哪里?”
老人侧过身来,看上去丝毫没有被这句突兀的问话打扰到。语气和目光都是亲切而慈蔼的:“去教会我们感知的地方。”愉悦的神情在皱纹遍布的面颊舒展,眼里闪烁着细碎的光。
“教会我们感知的地方。”孩子在心中默念。他好像听见了什么,似清冽的溪水汩汩浣过耳畔,像遥远的牧笛声,清越悠然。
有风拂过山林,无数树叶掀动的声音,是视线之外不息的和音。鸟叫声,一声声轻灵似剥去光芒的种子;蝉鸣,夏日里不饶不休地焦灼着耳朵;雨声,密实而安然地落在心上。
“嘎——叩!”伴着清浅的水声,有人在井边打水;“突、突、突、突……”是谁家的车子开过门前?剪影般的叫卖声依稀从远方飘来。
夏日黄昏,垂着丝瓜的藤条下,裁去白昼的暑气,老人们聚在一处聊天。嚼着方言,比芝麻大点儿的事也能说得津津有味。老人们时常叨念:“我们祖上是从河北一带迁过来的呀,我们说的是正宗的古汉言。”“锅”念作“鼎”,“热水”是“汤”,“俳优”是句粗语。孩子曾听见奶奶愤恼无奈时叹一声:“丫(好)殆啊。”
“……门环里的话,我都听到了。”
耳畔响起的声音牵回思绪。孩子有点儿迷糊地看着身边的老人,不明白她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老人不再开口,只是微笑。孩子恍然忆起,她是邻居家的婆婆啊。
孩子记得,婆婆种了满院子的三角梅,6月末,殷红桃红朱红簇拥着花的长廊,美得能绊住时光的步伐。婆婆会泡好喝的甘菊茶,会耐心地听他把一件小事叽叽咕咕、颠来倒去地说上半天。
后来,就在他被讲故事的人带走前不久,婆婆生病了。大人们说,是很严重的传染病,不让孩子进婆婆的屋子了。孩子闷着脑袋,绞尽脑汁地想啊想啊,总算憋出了个法子。婆婆住的宅子前大门上挂着两个古旧的大门环。孩子想,婆婆的耳朵那么灵,不如把想告诉她的话说给门环听,说完敲一下门环,声音就被扣下了。
之后的每天傍晚,他都来宅子的大门前,把话说给门环听。从“又学会了几个字”“萤火虫让哥哥骗走了”,到“木瓜结果了”“吃上了最喜欢的蛋燕”……多小的事情都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原来这些话婆婆都听到了。孩子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顺着回忆流淌的和声留在耳畔,孩子闭起眼睛倾听,他想从这些和声里找出一个声音。一个温热的、盈润的,如蜜桃般柔软饱满的声音,像拂晓时的风一样轻轻唤着他的名字。他多想听见,可偏偏,在那么多的声音里杳无踪迹。
想起这个声音,鼻尖就好像嗅到了淡淡的馨香。温软清浅的香气,像是小时候无意间翻出的一只樟木箱子,泛黄的信笺和晕染纸上的字迹熏着岁月熨帖后的味道,很好闻。孩子隐约觉得,在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弥漫了这样的香气。樟木的气息,湿漉漉的微凉,似绿荫洒落。悠悠的木香里,渐渐透出一股果香,越发丰盈浓郁。
孩子睁开眼睛,他站在一处晒果场边上。被熟红色润透的柿子紧挨着摆在竹编担子上,另一边是满满的紫黑色李果,浸透了秋日的暖阳显得一派丰润。饱满的果实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细盐,似初冬的薄霜。在煦暖的阳光下晒制果干,甜美的果香揉入一点儿咸味,和着脆爽的凉风扑面而来。熟悉的感觉像被清水浣洗的卵石一一浮现,孩子仿佛能看见晒好了的柿饼和李干,深棕色的果实散发着饱含阳光的浓郁滋味。那么亲切,那么熟悉。
孩子有点儿累了,打了一个好长的哈欠。眼前的景物像被秋阳融化了,他又回到一个人的路上。婆婆也不见了。
一只奶白色的猫从脚边擦过,米黄色的斑纹似阳光的吻痕。孩子感到好奇,忍不住叫出了声:“喂!”
“怎么?”猫听见了,回过身来。
“请问——”他顿了顿,忙说,“你知道我们这是去哪里吗?”
“当然。”猫有点儿郑重其事地回答,“去一个我们最熟悉、最依赖、最依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