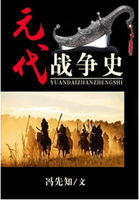李克农同志的住地警卫
李克农同志是我们党和军队在隐蔽战线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那些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们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重要情报,保障了我们在正面战场上的胜利。我们党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之所以能以小胜大,是和李克农领导的情报工作分不开的。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克农是我们的老首长,从延安到北京,李部长都直接或间接领导着我们的警卫工作。进城后他的职务很多,但我还是和延安时期一样叫他李部长。进城后他住地的警卫也是由警卫一师负责。
负责首长住地警卫任务的部队不仅要站好岗放好哨,还要在情况允许下,很好地照顾首长,在李部长住地负责警卫任务的部队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对李部长的深厚感情,下面的部队也都知道。
1961年下半年,李部长当时住在景山后街一个胡同的院落里,警卫任务由警卫一师二团担任。一天,负责警卫任务的连指导员给我打电话,他要我到李部长这里来看一看,虽然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还是感到了有什么事情。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了李部长的家里。在门口,那个连指导员告诉我:“自从首长的夫人去世后,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想问题,也不出房间,酒也喝得很厉害,我们劝了也不管用,所以才向你报告。”我听到这一情况后心里一沉,我知道李部长和他的夫人的感情非常深,他们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的生死关头,都闯了过来,在病魔面前却无能为力,阴阳两分离,这样的打击对于意志再坚强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残酷的。
我来到李部长的客厅门前,看见了很多酒瓶子,进到客厅后,李部长坐在那里,抬起头说:“老古你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李部长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李部长没有说话,只是苦笑了一下。
我又说:“大姐走了快一年了,你要想开一些。”
他说:“老古呀,你不知道阿,忘不了呀。”
我说:“那你也不要喝那么多酒嘛,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他说:“不行呀,不这样过不去呀。”
李部长的话虽不多,但我却非常理解李部长的心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再劝他,我们两个人都不讲话,就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最后我站了起来,说:“李部长,你还是要多多保重身体,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告别了李部长,走出了客厅的房门,我擦了擦眼里的泪水,对指导员说:“李部长的心情不好,你们可要照顾好他,有什么事情要报给我。”
我离开了李部长的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李部长就去世了。
兴国老表萧华要求不换警卫
萧华同志也是江西兴国县人,他13岁就当上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我在家乡时就听过萧华给我们作报告。红军时期萧华也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我那时在总政治部给杨尚昆当警卫员。他在总政治部的时间不长,又去了红军少共国际师当政委,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警卫工作的需要我们也有过接触,我们下面的警卫部队也知道我和萧华很熟悉。
1964年,由于警卫一师警卫任务繁重,上级决定对一师的警卫任务做调整,将天安门以东防区的任务移交给其他部队,这其中也包括首长住地的警卫任务。
部队换防进行得很顺利,只是总政萧华主任还想用警卫一师的部队,但下面的干部做不了主。萧主任就对他们说:“叫你们副师长来一下吧。”
二团团首长将萧华主任的话转告给了我。我第二天来到南池子萧华的家里。
我刚一进院子就向警卫连队的干部了解情况。萧华看见我进了院子并没有进楼,而是在院子里同警卫部队的战士和干部谈话,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对我说:“老古啊,你到我这里,进门也不上来。”我看到萧主任在叫我,就笑着说:“哎呀,我也是刚进门嘛。”
萧华说:“你赶快上来,赶快上来。”
我来到他的房间后,说:“萧主任有什么事情这么急?”
萧华说:“你们的人是不是要走,我这里你们是不是不管了?”
我说:“是啊,准备交给二师了。”
萧华说:“你们在我这里搞得很好嘛!为什么交给别人呀?你的部队在我这里很长时间了,他们也给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赶忙抢着说:“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他们做得好是应该的,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萧华说:“我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他们都熟悉我这里,我也熟悉他们,我这里的警卫是不是就不要换了,还用你们的人呀?”
我说:“哎呀,用谁不是都一样吗?”
“你们的人在我这里时间也不短了,我已经习惯了他们,再换别人怕不习惯,你们是不是就不要走了。”
我笑了起来说:“你是首长,你就定吧,你说留下我们,我们就留下来。”
萧华说:“那就讲好了,我这里还是你们管,人员也不要换了。”
我说:“行。”
看到萧华主任那副认真的样子我笑了起来。从此警卫一师继续担负萧华主任住地的警卫任务。像这样的事情很多,首长和警卫部队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或者是部队表现出色得到了首长的表扬。这些都反映出我们这支警卫部队还是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时期中央警备团的光荣传统。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萧华同志了,直到1978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党员预备会上,我们见过一面。那一年我被组织上推荐为政协委员,萧华是人大代表。在开预备会的上午,我和我的女婿王俊生(他是北京市选出的人大代表)两个人从北门进入人民大会堂,在大礼堂门口碰见了萧华,我说:“萧主任,好久没见你了,你还好吧。”
萧华说:“还好,还好。”
我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不少委屈吧?”
萧华说:“不要提了,向前看吧!”
他又把吴崇汉陪他一起在西北转了一圈的事情告诉我。吴崇汉也是江西兴国人,在西安办事处的时候他给林老开汽车。
我们三个人一边谈一边就来到了大礼堂前区后面,我们刚坐下,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同志走过来问候萧华,而且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坐在了我们周围。这时有一个老同志过来和萧华打过招呼后说:“萧华同志,你要注意喽,可不要搞成兴国帮呦。”萧华左右看了看笑着说:“你可不要乱讲哦。”他的话刚一说完四周的同志们都笑了起来。我也看了看周围的人,凡是我认识的人,差不多都是我们江西兴国县的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大院孩子们的特殊保护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对它的认识不足。因为历次的运动都没有多长时间就结束,这次可不一样,一下子就搞了十年,而且涉及的面也很大,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运动开始之初,警卫师也派出干部参加北京市的工作组,但由于学校反对工作组,他们就陆续都撤了回来。我们师派出去都是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很高的干部,他们是在执行北京市委的工作部署,到底错在哪里,当时他们不知道,所以回来后情绪都不高。我也劝他们不要想得太多,回来后先好好地休息休息,不要急着搞工作。后来我知道了工作组犯的是压制革命师生搞运动的错误。
学校里都在搞运动,小一点的孩子们没有学上了,整天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到处乱跑,大一点的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搞运动,也让家里的大人很不放心。为了管住这些小孩子们,一天杜泽洲副政委对我讲:“老古,现在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孩子们整天也不上学,在院子乱跑,这不是个办法呀!”
我对他讲:“那你就找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吧。”
老杜就叫政治部从干部队找来两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干部,把上小学的孩子们组织起来,给他们上文化课。大一点孩子怎么办呢?师里决定男孩子放到仪仗营当兵锻炼,女孩子们放在267医院锻炼。至于这些孩子们吃穿的费用,吃由家里交伙食费,军装从后勤部的仓库里挑一些好一点的旧军装给他们穿,这些军装还是老式黄颜色的军服,和现役军人的军服是有差别的。
这些孩子们在下面连队得到了锻炼,也避免了在社会上乱闯。由于他们穿着黄颜色的军服进出营区,很容易让人看出他们的特殊性,所以引来社会上一些小孩子们的羡慕,他们有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同学。这样一来,这些社会上的孩子们也闹着要穿军装到部队中锻炼,特别是一些女孩子们。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允许后,就开始上告,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小孩子们全部都又拉了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老杜又对我讲:“老古,咱们老头同女娃娃们打一场篮球吧。”
我看着他,想:“这个老杜在搞什么名堂,和小孩们打什么篮球嘛!”他见我没有讲话又问:“怎么样?”
我说:“好啊,你组织吧!”
我没有想到他还真组织起来,他除了找到我,还找了焦万有副师长、陈祖江副师长和向前同志。老杜找来的这几个人是在延安时期就一起打球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1966年的时候,向前准备调到外省军区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知道他要调走,就对警卫师说:“你们不要把向前调走,这个人我要。”北京市考虑到部队和地方工资的差别,向前去北京市委后晋升两级,任北京市副秘书长兼农委主任。向前虽然调走了,但他的家还住在警卫一师的院子里。
比赛是在一天的下午,老杜早早地来到球场,并对我的女儿古东东讲:“东东,把你们女娃娃组织一下,和我们老头子打场球,怎么样?”女娃娃队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我到球场的时候,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了,球场上老杜和焦万有在练着球,我问老杜:“怎么,就我们三个人?”
老杜说:“老陈来不了,向前一会儿到。”他刚说完,就看见向前往这边走。
老杜喊着他:“老向,你快一点嘛,就等你啦!”
向前快走了几步来到球场,他一边擦着近视眼镜的厚厚镜片,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段绳子,拴在眼镜的两条腿上,然后再套在头上,防止在打球时眼镜掉下来。我看到他和延安时期一样时,就笑着说:“老向,你这是有备而来呀。”他也笑了起来。
我们老头到了,但还缺一个人,老杜就把在场边看球的警通连的一个战士叫了过来:“你来参加我们老头队。”
这个女孩子队里,只有古东东一个人打得不错,她是高中生,又是学校篮球队的,其他的人就不行了,我们老头几下子就赢了不少。老杜看这种打法没有意思,就把在场边看球的杜新生叫了过来,加入到女孩子队里,这是他刚上初中的二儿子。
这下子女孩子队里加入了一个十来岁的小伙子,跑得又快,他上来后连蹦带跳地就将比分追了上来。老向看到这一情况的变化,在一旁着急得喊:“老杜,你要看住你儿子嘛,不能老让他这么打呀!”
这下老杜认真起来了,他跑不过他儿子,就采用我们一拉二抱犯规的办法。
这下把他儿子搞冒火了,杜新生把球往地下使劲一扔,说:“你们这么赖皮,我不打了。”说完就要走。老杜看到他要走,就喊他:“你敢走!你走,老子就揍你!”
老杜这么一喊,这个新生也乖乖地回来了。这一下子,场上场下的人都笑了起来,老杜自己也大笑了起来。
这场球还是我们老头队赢了。球赛刚一结束,陈敏和杜洪生带着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子就把我给围住了:“古伯伯,古伯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打过篮球,我们也和你们打一场球吧。”
我说:“你们去找我们队长吧。”
他们一下子把老杜给围住了,嚷嚷:“杜伯伯和我们打一场吧。”
这个时候,警通连的战士们也在一旁说:“副政委,也和我们打一场吧。”
老杜看到这一场面得意地大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说:“我们哪里打得过你们呀!”
老杜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小孩子们打球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就不往外面跑了。他们在警卫师的院子里不仅打球,还组织起来在礼堂里演节目,所以这些孩子们没有参加社会上的打砸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些从延安警备团过来的人,陆续从警卫一师调了出来,我是在1966年底调走的。在这里,我和同志们共事二十多年,相濡以沫,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这份感情里不仅有行政首长,也包括政治部门的首长,如肖前政委、张廷桢政委、邓波政委、郭永彪政委,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但并没有看不起我们这些文化水平低的同志,而是相互尊重。我和郭永彪在一起工作也就三年多的时间,但在感情上同其他同志们一样深。
全国开始大串联后,到北京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环境也变得复杂了。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学生大串连之际搞破坏,我们的警卫任务也相对繁重起来。周总理对于这一问题很敏感,在此期间,我曾多次执行过总理布置的有关警卫任务。
加强伍云甫同志住地的警卫任务
伍云甫同志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他的资历很老,长征路上,他就是红军搞保密工作的领导了,我也是在长征路上认识他的。
1937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他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那时虽然是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们的监视和破坏。所以他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也面临很大的危险。后来他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搞统战工作。
1966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找到我,问:“伍云甫同志你熟悉吗?”
我说:“熟悉,长征路上我就认识他。1937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他当过警卫排长。”
周总理问道:“你们熟悉就好。你们师在西单有没有部队?”
我说:“有,在西单商场南边,四团有一个营部,东面电报大楼、西边民族宫都有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