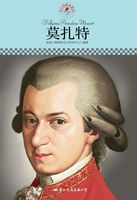常德会战中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使张恨水很感动,但是他当时还没想到以此来写一部军事抗战小说,于是以自己不懂得军事,没上过战场的理由婉谢了,他的答复是:“是的,7年来(那时是抗战7年)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这是文人的耻辱,对不起国家。我们实在也应该写一点,像常德这种战役,尤其该写。本来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战役可以写的,有上海一战,宝山之役;津浦一战,台儿庄之役;晋北一战,平型关之役;桂南一战,昆仑关之役;湘中三次会战,长沙之役;最近湘西一战,就是常德之役了。这都是我们认为光荣的。尤其是昆仑关和常德,我们终于是把敌人赶跑了。可是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我又没到过战场,我无法下笔,大而在战时的阵地进退,小而每个士兵的生活,我全不知道,我怎么能像写《八十一梦》,凭空幻想呢?”(《虎贲万岁》中《自序》)。
这两位抗日英雄却一定要他写,并且说可以充足地供给材料,在无可推辞的情况下,张恨水只好答应从长计议,将来再说。其中的一位抗日英雄在离张恨水不远的地方住下了,此后他便常常到来和张恨水聊天,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
几个月后,这位抗日英雄又旧事重提,其时,张恨水正担任重庆《新民报》经理,琐事很多,答说没有时间写小说,仍然婉辞。但是这位抗日英雄极其诚恳地说:“我为57师阵亡将士请命,张先生不能拒绝。”几天后,他将两大包袱材料送到张恨水家,里面有地图、相片、日记、剪报册等三四十种材料,一一呈于张恨水面前。
这一来,张恨水再也无法拒绝了,只好答应先看材料,有工夫再写。
1944年11月,张恨水已辞去重庆《新民报》经理一职,重新乡居,便抽暇看了一部分。那两位抗日英雄便轮流做客张恨水家,问张恨水材料看得怎么样了,张恨水说看是看了,有许多地方不懂。他们就张恨水不懂的地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往往一个问题,可以解释两个小时。他们口讲指画,不厌其烦,并且亲自在茅屋里表演作战的姿势,甚至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一一地详加叙述。张恨水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更为57师阵亡将士的壮烈事迹所激励,决定将之写出来。
张恨水于1945年春季正式动笔写《虎贲万岁》。他根据油印品、地图、笔记、照片,边翻看,边动笔。有不大明白的地方,记下来,等那两位抗日英雄来了,问清楚了再写。那两位抗日英雄也就常常来看原稿,不对的地方,随时加以指正,就是极小的细节描写也不放过。张恨水为了进一步掌握写作此书的素材,还特地在重庆市找了两位经历过这次战役的常德籍老百姓,来自己家里作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
张恨水笔下的《虎贲万岁》很注重纪实,该小说从师长到伙夫全是真名实事,时间地点也同战史完全吻合。他饱蘸浓墨,以从容而又激荡的心情叙写了抗战史中光辉的一页。他细致地叙述每个零星战役中的人员、攻防、装备、死伤,从众多细节的铺陈,建构出74军57师骁勇壮烈的形象,许多悲壮却平实的大场面描写使人无法不为之动容。如果说张恨水通过一个个体战士的死里逃生抒写出一曲生命的颂歌,那么通过一个战斗集体的视死如归,他将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内在的磅礴气势和潜在的威慑也完整地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张恨水在《虎贲万岁》的《自序》中说:“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8000人实在已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下83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57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改变了我的作风。”
小说快要完稿时,余程万非常高兴,特地派人送来一笔相当丰厚的谢金,但是张恨水坚辞不收。抗战胜利后,余程万正驻守南京,要请张恨水吃饭,也被谢绝了,但是却接受了他一件礼物:一把从日俘手中缴获的战刀。
1946年,《虎贲万岁》单行本出版。《虎贲万岁》出版后,57师扬名中国,也大大地提高了余程万的知名度。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书后,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的“虎贲英雄”。此时抗战已胜利,余程万的军队驻扎在南京。
一次他去上海游玩,见到了这位苏州小姐。很快,这位叫吴冰的苏州小姐成了余程万的二太太。
国民党兵败逃往台湾后,余程万没有随残败的蒋家王朝去孤岛台湾,而是把家安置在香港,在香港定居。他做起了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同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当铺。他的元配夫人邝琼华,寓居在香港九龙尖沙咀市区,而二夫人吴冰,则在香港新界屏山乡间办了个农场种菜养鸡。
余程万在内地期间,积累下不少财富,到香港后,加上他善于经营,生意很是红火,其财富引起了盗匪的觊觎。1955年8月27日晚上近12时左右,余程万的屏山寓所遭匪徒入屋行劫,二夫人吴冰和佣人全被捆。一会儿,从九龙市区回家的余程万也被匪徒所擒。屋里的动静太大,引起邻居的警觉,并悄悄报警。警察来后,与匪徒发生枪战。黑暗中,余程万中枪死亡。警方公布说,三名劫匪中,一人被击毙,两人逃脱,余程万被劫匪打死。
但据其副官说,余程万当时被劫匪当作了盾牌,事后,他看过老长官的遗体,胸腹有一排子弹,相信是冲锋枪或轻机枪所致,而劫匪没有这种装备。余程万究竟被盗匪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去追究。关于劫匪身份,亦有不同版本:有人认为是台湾特工,因为在香港,余程万在与黄埔老友闲聊论及老蒋时常多怨气;也有人认为是黑社会头目,看中了二太太的美貌。
警方花港币两万元缉凶,最后不了了之。一代抗日名将余程万,竟落得如此之结局!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43号的一处小四合院(也就是如今的95号)。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作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鲁迅先生的经典幽默
鲁迅先生一生中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融讽刺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尤其是他的打油诗辛辣有加,妙趣横生,且入木三分。如鲁迅先生曾写的《南京民谣》打油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揭露国民党的内部摩擦,对他们伪装正经的行为进行辛辣的讽刺。格调幽默风趣,语言通俗活泼,生动形象。
鲁迅先生还曾写过两首鲜为人知的打油诗。这两首诗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诗歌欣赏册子中极少选有。
这两首诗都写于20世纪30年代。一首是咏大学者钱玄同的,诗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以肥头,抵挡辩证法。”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反封建文化的先锋,曾以“金心异”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过不少激进文章。其中有一篇主张人超过40岁就应统统去死,从而使社会年轻化,而后来他却不能与时俱进,退化为保守主义者。作为一名北大教授,钱玄同还曾扬言,北京大学要开设辩证法课,除非砍掉他的脑袋。鲁迅先生与钱玄同曾是好朋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发表于钱玄同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后两人因人生观、社会观不同而分道扬镳。鲁迅先生用寥寥20字,便将钱玄同先偏激后保守那可笑的面孔刻画得惟妙惟肖。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其兄钱恂是晚清的名人,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过外交官。大家所熟悉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是钱玄同的二公子。钱玄同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的讲课也以幽默着称。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学生听了后,都笑得前仰后合。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着的,他所着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
鲁迅的另一首打油诗是咏资深编辑、翻译家赵景深的,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赵景深是二三十年代着名的文学编辑,扶植过许多文学青年,有不少作家的处女作就是在他主编的刊物发表的。他还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由于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错误出现。一次,他将milkeyway(银河)误作“牛奶路”。又一次他将zentaur(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先生对赵景深译作中的这两处错误,写了以上这首打抽诗,善意地嘲讽、批评了这位翻译家治学上的不严谨态度。
鲁迅曾留下了大量的书信,现存有1455封。这些书信不仅记述了鲁迅的友情、亲情传达,文债往还等,还聚焦世事、人情、学问,不仅洞悉,而且常常迸现出思想的火花,总是让人眼前一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上海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也是货色之一。”他这样揭露一些丑人:“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借此扬名的。”他厌恶那些“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虽然改穿西装了,内容也并不两样。”鲁迅热爱关怀的青年,是柔石一类的青年,但他也鞭挞另外的一种青年:“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发……”
读这些书信,可使我们认识了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鲁迅,一个“圆整”而非“平板”的鲜活的伟人。
有趣的是,鲁迅在信尾所用的问候语常常十分俏皮,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写信,自然少不了在信尾写上问候语的。鲁迅早期的信多用文言文,结尾常用“此颂曼福”、“即颂时馁”等句。后来,鲁迅用白话文写信,如收信人从事着译工作,信尾写的是“即颂着祺”、“即请撰安”等句。是教师,用“并请教安”;是学生,用“即颂学安”。如是夫妇,便“即请俪安”。如是离家在外者,用“即请旅安”。写给母亲的信,要“恭请金安”。如果在春节时写信,会“即颂年禧”;若是春夏季节写信,就用“并颂春祺”、“顺请暑安”。此外,鲁迅还根据不同的信,在信尾写“日安”、“时安”、“刻安”等问候语。
鲁迅曾写给许广平不少书信,仅《两地书》原信就保存下来了68封。这些书信中,体现着鲁迅惯有的幽默,信尾问候语也很风趣。1925年7月16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就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和许广平讨论,信尾用的是“顺颂嚷祉”的问候语,祝福她在吵嚷中得到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