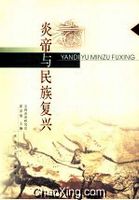过长川坝已走了两天,仍然无边无际。沿途遇到一些沼泽地,同样长着青草野花,但马帮在头骡、二骡的带领下,总是左拐右绕,鱼贯而行,显得小心翼翼。我问锅头阿兀丕楚,为什么不走直线前进,缩短路程?锅头告诉我:这种沼泽地,看上去与我们现在走的路没有什么分别,下面也都是黑油油的泥土,但它是不知经过多少千年的腐草沤积而成,如果不小心踩上了,便会整块整团地陷落,深的地方人畜货驮会被完全陷没,救助起来也非常困难。以往有些牲畜货驮就是误踩上这种地方而遭受损坏,因此过这种草地是非常危险的。他告诫我千万不可贪图近路而走出马帮队伍。我听从他的话,紧紧跟随着马帮,顺利地通过了危机四伏的沼泽地。我佩服头骡、二骡的识途能力,它们的重要性也由此可知。
在长川坝,我们还看到过大约300只左右的野羊群,灰黄的毛色,在头羊的带领下,向远方奔驰而去。奔跑的蹄声有如轻雷滚过,异常壮观。我十分喜欢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野羊群的出现,使我激动不已。据说藏北草原上的野羊群更多。如今,从报纸上得知它们也没有逃脱被捕杀的命运,心里很是不安。当群羊出现时,马帮里有人想开枪射杀,却往往被锅头大声阻止。他说:藏族有个规矩,在旅途中是绝不容许杀害野生动物的,因为这会影响旅途的吉祥如意……一番话,使我陷入沉思,我在沿途看到大雕、秃鹫、苍鹰翱翔在高高的蓝天,还看到高原湖泊上轰然起飞的水禽那么自由自在,原来是藏胞的一片深情给它们留下的生存空间呀!
在长川坝我还看到草地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穴,不时有百灵鸟从洞穴里飞向蓝天鸣唱;又见到有松鼠大小的野鼠从同一洞穴钻出,双手放在胸前,形态可掬,蹲坐着面向东方晒太阳取暖。藏族同胞说,这是野鼠双手合十在朝拜太阳神。
因为洞穴潮湿,它们需要每天出来晒太阳。人们称这种情况为“鸟鼠同穴”。这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特有的现象。冬春季节,大雪纷纷,草原一片白茫茫,迫使它们分工合作,互相依存。它们在较好的季节里,分别外出觅食,贮于洞中,以备冬天食用。延寿果是西藏的名贵特产,用纯酥油煎食,其味香甜,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是极好的馈赠礼品。这种果实即将成熟时,大部分都被野鼠和百灵鸟衔到洞里贮藏,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所以,卖延寿果的人,除采摘外,大都是从野鼠洞里挖掘得来。
有一天傍晚,天空浓云密布,风也停了,草原一片沉寂。不久,便飘起了鹅毛大雪。一钻进帐篷,暖烘烘的,下雪天更催人入眠,躺下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惊醒时,似有重物压着,十分闷热。翻身欲起,可连手也抬不起来,我们大声惊叫。锅头阿兀丕楚也大声喝道:“别怕,用力翻滚出来就行了!”我们一个个从帐篷下面翻滚出来,原来一夜的大雪把帐篷压垮,我们都被深埋在雪下了。我们齐力将雪扒开,拖出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等待天明。好难熬啊!在高原上,黎明前的气候特别寒冷,风虽然小,但吹到脸上就犹如刀割一般。根据这次亲身经历,我曾写成了一首绝句:
一马平川望眼迷,鸟鼠同穴世间稀。
代薪牛粪冰溶水,夜雪消魂盼早曦。
在旅途中,如果遇到连日的雨雪,行李、马垫受潮,加重了骡子的负担,人也特别难受。一遇天气晴朗,锅头就选择宿营地休整一两天。于是我们在草地上扯起帐篷,燃起牛粪,煮上腊肉、香肠,在挂面里加上生蒜、辣椒,美美地打上一顿牙祭。然后把行李、马垫铺开来暴晒,牲口则自由地放牧在大草原上。
我们仰面躺在开满鲜花的草原上,看着蔚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听着百灵鸟的歌唱,讲故事、说笑话,旅途的劳累一扫而空,倍觉舒畅。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接受了大自然的洗礼后,得此清闲,才真正体味到苦尽甘来的无穷乐趣!
锅头阿兀丕楚,时时事事为我们和马帮操心。他从牧民那里买来上好的酥油,一饼一饼地放进大铜锅里熬成酥油汤,加上红糖,平均地分给每人一碗。他的那份,也同其他人完全一样,甚至还要少些,而绝不会多于别人,这就是马帮的规矩。而各人所得的那一份,可以一次吃完,也可以分几次吃。酥油汤捏糌粑,营养丰富,味道清香,还用牛角筒将酥油汤灌给骡马,以补充牲口的体力。
到了草地的边缘,在一个小岸壁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洞穴,野鸽在那里做窝。夜间,拿着手电筒去捉野鸽,可以手到擒来。在荆棘丛中,还有肥大的箐鸡,这些野味,常常是马帮的佳肴,味道可口,遗憾的是缺少一杯美酒。
走完了长川坝,又从一个小峡谷中穿过,两边悬崖高耸,我们看到在高处钉有铁桩子,桩上系有铁环。这又是什么人爬上去钉的呢?它有什么用呢?这真是一个谜。传说这是大禹治水时系船的地方。这个传说虽然不可靠,不过从长川坝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可能曾经是个大海。
翻工布江达阴山
过了长川坝,前面仍然是重重叠叠的大山。过工布江达的阴山时,气候特别寒冷,这里山谷幽暗,阳光难以照到。举目东望,天空黑雾蒙蒙,在依稀的阳光照射下,就像是细罗筛筛下的黑色粉末,徐徐地向上飘落,据说这就是所谓的下黑霜。经过这个路段时,绝不能贪恋马背,应该下马步行,因为在马上的时间一长,手脚受冻麻木,血液循环减慢,会因头晕而从马背上跌下来。锅头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用棉被将其裹紧,反复搓揉,将其发热复苏,直到恢复正常为止。如果烧大火烧烤,手指、脚趾就会坏死脱落。
这一段路找不到干柴,也没有牛粪,生火就成了大问题。可是,阿兀丕楚还是有他的办法,他手持长刀从草丛中砍来阔叶灌木,塞在火塘里,哪怕只有一点点火星,也会慢慢地冒出烟来。再用土制的羊皮鼓风器不断地鼓风,渐渐浓烟四起,熏得人眼泪直流。突然间,“轰”的一声,这些湿柴就像浇过汽油似地猛燃起来,真叫我心慌不已。我们架上铜锅,化雪煮水,奇怪的是水比往日煮沸得更快。
锅头讲了一个传说:古时佛教祖师宗喀巴路过这里,无薪可烧。他就施展法术,把酥油洒在这里的灌木丛上,从此以后,烧火就没有问题了。后来知道这是因为海拔高而气压低的缘故,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在旅途中,吸惯了烟的人缺了烟是很难忍受的事。但锅头却有办法,他们找来一些大黄(一种药材)的干叶,搓碎后拌以从烟杆里掏出的烟油,大口大口地抽吸过瘾。遇到回程马帮的相识人,除问候和祝愿平安之外,就要他们转让香烟,但得到的往往是馈赠,而不肯收取分文钱财,多么难能可贵啊!
雪域地势高峻,气候多变。有时,眼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山风吹来,霎时便乌云密布,暴雨迎面扑来;有时,狂风大作,雷声隆隆,雨点夹着冰雹倾盆而下;有时,莫名其妙地纷纷扬扬飞起大雪。初秋,阳坡上的积雪易化,但阴面和山坳里的积雪就很难消融,而且还会结上一层薄冰,被人和牲口踏碎后,一阵山风将它吹跑,滑过冰面,发出爽朗朗的清脆响声,十分动听。
半天的山路跋涉,我已感到筋疲力尽,多么想休息一会儿,忽然一个雪坡又出现在眼前。我只好跟着马帮继续前进。积雪越来越深,我跟在马帮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特别费力。劳都们各自照看着自己的骡子,将一匹匹陷在雪地里的骡子拉的拉、推的推,刚把一匹推上来,又有一匹陷了进去。有时,要两三个人一起拉缰绳、提尾巴,推推搡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累得人困马乏。
骡马驮着沉重的驮子,经几次雪地摔跤,惊吓加寒冷,浑身瑟瑟发抖。锅头走到前面探路,发现积雪很深,眼看这么大一群马帮,骡肚已陷贴于雪中,再要冒险往前赶,后果将不堪设想。锅头大声命令一个劳都到身后的村落里去请牦牛运输队,要他快去快回,越快越好。
不久便见一片黑压压的牦牛朝我们飞奔而来,领头的牦牛带领着牛群向前挤跑,它们用头角挑起积雪往前开路,只见雪尘纷纷落向两边,不久便开出了一条雪地壕沟。我们同牦牛运输队的藏胞一起,迅速从骡背上卸下货驮,转放到牦牛背上,劳都们又接着用生姜、红糖喂骡马,使其恢复体力。
牦牛,真不愧为“高原之舟”,它们在雪地上如履平地,而且不会迷路,哪怕是走在悬崖边上,也不至于滚落深谷。
转眼,牦牛运输队已经爬上了雪坡,只见白的雪,黑的牛,黑白分明,对比强烈,加上牦牛运输队扬起的纷飞雪尘,组成了一幅悲壮而苍凉的动人画面。
马帮沿着牦牛开出的雪壕沟前进,喘着粗气,打着响鼻,偶尔发出一声声嘶鸣,此刻显得那样凄凉。我的乌拉靴内已经湿透,双脚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每一步都迈得那么沉重。
过了雪坡,眼前是一片绿草,牦牛运输队已经下好驮子,牦牛和骡子也已放牧在草地上。看到人畜都安然无恙,大家才长长地舒一口气。
我们吃着午餐,当一碗碗酥油茶下肚后,大家又乐开了,围着火塘,开怀大笑。藏胞讲,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远离村落的地方,必将人死骡亡,明年又见白骨一堆。双方调嘴弄舌,免不了幽默一番,甚至弄得对方十分尴尬。但藏族有个规矩,不能向对方翻脸发脾气,而要用自己的智慧去“以牙还牙”。
这既是一次毛骨悚然的历险,但又是一次难忘的高山聚会。
牦牛队临走时,没有多要我们的一分钱,他们认为敲磕患难者的钱财是不道德的,菩萨也不允许。我们在高山上依依惜别,一再道谢,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
牦牛返回,扬蹄晃脑,狂奔而去,雪尘飞扬……
近三个月的艰难行程和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增强了我吃苦耐劳和临危不惧的精神,回想自己一生的经历,应该说是得益于这次茶马古道之行。
渡拉萨河
到了墨竹工卡,拉萨就临近了。几条河流从远方汇合奔涌而来,到此分为几岔,然后再汇为一股,朝拉萨方向奔流而去,最终归入雅鲁藏布江。这一段称为拉萨河。拉萨河上波光粼粼,河旁地面宽阔,空气湿润,田野是一片葱绿。
我们露宿于拉萨河畔,附近的村落里有许多专门从事渡河的河工。我们在村里遇到一位老人,四川口音,是几十年前流落到此成了家的,老伴是藏族,他说“我们是大同乡”,因而受到款待。老阿妈也很热情好客,她还风趣地说:“多喝几碗酥油茶吧!酒会醉人,茶不会醉人。”老人还为我们请来了牵马过河的引路人和渡船的船工,说定酬金后,决定第二天为我们效劳。船工熟悉地形及河水的深浅,哪里有险滩急流,哪里有漩涡礁石,哪里能过,哪里不能过,都了如指掌。如果涉过拉萨河的岔河前进,抵拉萨还要三天路程;要是坐船而下,到拉萨只要一天。
清晨,太阳刚刚出山,一位体格健壮的大汉,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到我们面前,交代了一些蹚水过河需要注意的事项后,便带头骑马下河。随后,驮着货驮的骡子也被顺次赶下水去,一匹接着一匹地缓缓前行。浅水处,骡蹄溅起水花,“哗哗”有声。到了中流,骡子自然扬起头颅,水太深时,它们也会游上一段。我骑着马,河水浸到膝头,冰冷刺骨。我在马上瑟缩发抖,心情紧张,只是紧紧拉住缰绳,不敢稍微放松。如果在激流中遇上了大漩涡,还会有连人带马一起被冲走的危险。过了一条岔河,就有一片沙滩,锅头已事先准备好柴火,在沙滩上生火为我们取暖。这样反复过了几道岔河才到达对岸,此时的我已筋疲力尽,无力动弹了。我们烧起了篝火,火焰在风中摇曳。几碗酥油茶下肚,才又提起精神。
当晚我们就露宿在拉萨河畔,晴朗的夜晚,篝火照映着拉萨河,火光在水波中莹莹动荡,头上的繁星正对着我们眨眼睛呢。
天蒙蒙亮时,从拉萨河畔的芦苇丛中传来了野禽的叫声。接着,斑头雁、麻鸭等一群群从我们的头顶飞过,一直飞向远方。
拉萨就要到了。雄伟的布达拉宫已经在望,金色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哲蚌坝子宽阔,田园如画,劳都们唱起了欢乐的歌,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啊,这就是拉萨!这就是我心里不断念叨着的拉萨啊!
到了拉萨,锅头阿兀丕楚和劳都们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重新整理行装,上好驮子,又要把货物运回遥远的丽江去了。在这近三个月的行程中,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善良而纯朴的品质,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特别是锅头阿兀丕楚,这位奔子栏的藏族大哥,他身上流露着藏民族的一切优点,永远是我的良师益友。当我握笔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总是索回在我的脑海里。我多么思念他啊!
当他们重新踏上回程的漫漫长路时,街上又响起了我熟悉的马帮铃声和马蹄的杂沓声。我向他们一一表示谢意,祝福他们一路平安!我久久地握住阿兀丕楚的手,眼睛湿润了,叫喊也哽咽了……阿兀丕楚却平静地对我说:“我会把你平安到达拉萨的消息告诉给你的亲人……”
在拉萨的阳光照耀下,浩浩荡荡的马帮运输队伍渐渐走远了,我站立在高处目送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迷蒙的地方……
(此文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的随马帮入藏的回忆文章)
我的自述
赖敬庵
我出生于1903年,父赖耀彩,母李爱月。五岁时随父母到中甸,辛亥革命回丽江,进私塾读书。时年十二,颇向往于读书成名,屡求父母续进学校,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