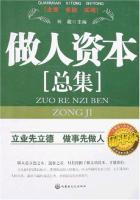所谓“受命”就是得到天子之位(“尊为天子”),得到厚禄、荣誉和长寿。以“大孝”之德而闻名的舜,被看成是这种道德因果必然性的例证。这样的命运,在儒家那里又是同正义性的“天”联系在一起的。儒家相信,“天”是正义和善的根源,它公正无私地佑助人间的有德者,就像《周书》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那样。孟子认为,尧不能将天下授与给舜,授与天下给舜的是天。只是,天不是直接说出,而是用“行和事”表现它的意志,这实际上是说舜获得天子之位是“天命”。孟子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子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与这种道德因果必然性不同,儒家还有一种不同的命运观,即有德者在事业上不必是通达的,也可能却是穷困的,《穷达以时》就代表了这种命运观,它称之为“时命”。所谓“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也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所谓“遇不遇,天也”,所谓“穷达以时”,其中所说的“世”、“天”、“时”,都是指“时运”。
《忠信之道》说:“不期而可遇者,天也。”按照《穷达以时》的看法,有“贤德”的人不必有其“位”。“贤德”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命运的是遇不遇的“时运”。舜能够成为天子是他遇到了尧:舜耕于历山,陶埏于河浒,遇尧也。
但舜之所以能够遇到尧,是他遇到了好的时运。如果舜只是有贤德而没有时运,他仍然不能够得到选拔。在孟子看来,尧和禹其子的贤与肖,都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天命决定的。普通百姓要有天下,不仅要具备舜和禹那样的贤德,还要有天子的推荐。孔子不能有天下,首先是缺少推荐人: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万章上》)
孔子在周游中怀德不遇,还屡遭挫折,他就将之归结为“时运”不济。孔子还深有体会地认为,不遇的君子往往身处两难之境,有时连性命都保不住。敦煌残本隋李文博编撰的《治道集》,其《愍诚臣第卅六》录《孔子家语》孔子的话说:孔子论诗,至于正月之六章,惕焉而[惧]曰:彼不遇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违上离俗则危身。时不兴善,己独由之,非妖则妄也。故贤者既不遇,又恐不终其命焉。桀杀龙逢,纣杀比干,皆其类也。
按照以上儒家的第一种“命运观”,有德的“舜”必然获得帝位,他的贤德就是他的命运的决定者,《论语·尧曰》所说的“历数”在他身上,也就是说他的贤德为他赢得了天命的肯定: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这里的“历数”指“天命”。按照儒家的第二种命运观,有贤德的舜要获得帝位,还需要“时命”的帮助,而这不是舜所能够决定的。《唐虞之道》的命运观,当属于第二种。按照作者的看法,即使出生在帝王之家也有贤德的尧,要成为天子都需要“命”和“时”,那么作为平民百姓的舜要获得帝位就更需要“命”了。舜是一位“知命”的人,他身居简陋的住处也从不忧虑:古者尧生为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命,虽]秉于大时,神明将从,天地佑之。纵仁圣可与,时弗可及矣。夫古者舜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忧,登为天子而不骄。处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登为天子而不骄,不专也。
《唐虞之道》建立在尚贤、尚德之上的“禅让”,由于引入了“时命”的条件,又使得政治继承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如果舜出于对自己的自信,提前预见到他一定会受命,或者如《中庸》所说“大德者必受命”,那么他接受的命就属于第一种道德因果必然的命了。而舜的“知命”,当是《忠信之道》所说的“不期而可遇者,天也”的“命”,而这种“命”则是一个人自己不可知、也不可左右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命”。
禅让与退休和养生
按照古代中国的王权政治,帝王在位一般都是终身制,而没有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之下的任期问题。古代中国帝王在位的时间,因他们自然生命的长短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彼此差别很大,这就意味着被确立为政治继承人的太子,并没有明确的接班时间表。在大部分情况下,什么时候接班取决于在位皇帝寿命的长短,但这是事先无法测定出来的。从理论上说,尊贤、尚德的“禅让”,可以不受在位帝王自然寿命的限制,只要选拔出可以继承王权的真正贤者,在位帝王就可以将王权转移给他。传说,尧时的一些贤人和隐者,看破了红尘,甘愿过一种宁静的隐居生活,其中就有巢父和许由。尧曾让位于许由,但个人主义的许由不接受尧禅让。还传说,尧将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以他需要治疗他的“幽忧之病”、没有时间治天下为理由拒绝了。
《吕氏春秋·贵生》记载: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这一类故事可能是道家为了塑造隐士的形象而想象出来的。正如我们上面所述,舜正式继承帝位是在尧逝世之后,这说明尧坐天下是终身制。《孟子·万章上》记载,孟子的弟子咸丘蒙请教孟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孟子断然否定了这种传闻: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哉,是二天子矣!”
同样,舜实行的也是终身制,禹是在舜逝世之后才继承帝位的。
跟这种历史记载和传说不同,《唐虞之道》传达了一种有点“任期制”和“退休制”的帝王政治: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
“致政”的意思是“交政”,即退休(一般的任职退休称“致仕”)。《礼记·明堂位》记载,周公在成王幼小时代成王执掌政权,成王长大后周公将政权交还给成王,其所说的“致政”意味着“还政”: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
《唐虞之道》说古代的圣人从五十岁开始“治天下”,经过二十年后到七十岁时退休,这是认为,古代帝王有任期制,任期为二十年。其所据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称之为“七十致政说”。在《管子·戒》篇中我们也看到了“七十致政说”: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
照《戒》篇的说法,圣人信奉正义,他到了七十岁就交出政权。以上文献记载的“七十致政说”,既指明了帝王任期的期限(二十年),也指明了帝王退休的年龄(七十岁)。按照《礼记·内则》的说法,人到了五十岁,他就步入了衰老期,到了七十岁他的体力就明显不支了。《礼记·曲礼上》列出了人一生不同的年龄阶段和相应的人生经过,认为人到了七十岁就是老人了: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髦,七年曰悼。悼与髦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大夫七十而致仕。
人到了五十岁,就要开始注意养生了,到了七十岁就更应该养老了。帝王从五十岁开始执政,二十年后到了七十岁,此时交政退休,在古人看来,这是同人的自然寿命和体力相适应的。《唐虞之道》在“七十而致政”后接着说: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了。
由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帝王之所以要七十岁退休,是因为他到七十岁就已经衰老了,已不适合继续居于帝位了。在这个时候,他禅让天下贤者,这不仅有利于天下,而且还可以“养其生”。真正懂得天下之政的人,是在恰当的时候禅让天下,同时又能够养好自己的身体: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知之政者,能以天下禅矣。
由于《唐虞之道》的作者是在宣扬尧舜禅让的具体背景下说明圣人“七十而致政”的,所以他似乎认为尧、舜就是七十岁而退休的。但总体上说,《礼记·内则》、《管子·戒》和《唐虞之道》等记载的古代圣人“七十而致政”的任期和退休,与其说是一般历史叙述,不如说是一种制度设计。按照上述的历史传说,尧、舜、禹实行的都是终身制。从这一点来看,《唐虞之道》又把尧、舜的禅让理想化了。《容成氏》记载说: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这里说的“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按照七十而视为老的标准,其年岁当与《唐虞之道》一致。
不管如何,《唐虞之道》等佚文在将“禅让”同任期和退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又在让贤的意义上附加了按期让位和退休的条件,从而使政治继承有了明确的时间表。按照《唐虞之道》的思路,帝王到了七十岁,身体自然衰老了,适应这种变化而退休,对他来说不仅意味着能够养生,而且还意味着他不专权自利。
这里暗含着帝王即使到了七十岁,他主观上可能仍然不愿意放弃权力和退休。
如果没有严格的任期和退休制度,执政者实际上是否退休,就变得不确定了。
对于帝王退休为他们养生带来的益处,一种传说认为,古代帝王都是身先士卒的最辛苦的劳动者。《庄子·在宥》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
因此,帝王让位和退休,对他们来说就是从艰苦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韩非子·五蠹》篇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苦,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苦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照此说来,帝王“让天下”和“传天下”没有任何高尚的地方,反而是从为天下服务变成了为自己考虑了。与此相反的传说是,在位的帝王不再是体力劳力者,他们是清静无为的人——“恭己正南面”。荀子还将黄老学的“无为而治”变成了“安逸而治”。这样,帝王不仅不辛苦,反而是天底下最会享受也有条件享受的人了。他们不需要通过退休而养生,他们在位期间实际上一直就在养生。
《荀子·正论》说:
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
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代皋而食……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
古今一也。
这样,《唐虞之道》“七十致政”而养生的说法,在荀子那里自然就不成立了,也不能作为帝王退休的理由了。荀子是不主张帝王退休的,他主张帝王终身制。他认为帝王身体虽然老了,但他们的智能并无衰老,他们仍然可以执政到死去。
“七十致政”指的就是帝王年老退休和禅让年龄,而荀子说“老而禅让”是虚言,也就是具体否定“七十致政说”。我们推测,“七十致政说”,可能是儒家或子学对君主任期的一种制度设想,至于执政者是否愿意按此去做,就另当别论了。
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政治权力的转移是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古代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有不少大的冲突都是由王权转移引起的,虽然王权世袭已是基本的政治制度。与之相比,没有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禅让”,就更容易引起政治危机。在远古中国政治生活中,即使“禅让制”确实存在过,但其具体的政治实践,也伴随着其他复杂的因素并受其影响。《唐虞之道》等“尚贤的禅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念,而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