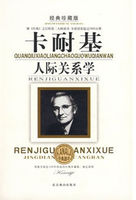1.打手心好痛
爸爸总说我是个机灵鬼,专挑好日子来到这个世界。
你看:日本军用飞机在重庆满天扔炸弹的日子,你不出生;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陪都重庆的夜空,满天的烟花爆竹,庆祝抗战胜利的晚上,你呱呱落地了。
新生婴儿的哭声为胜利更增加了喜庆!
生于陪都,庆祝抗战胜利!于是,“包陪庆”成了我的名字。
抗战胜利后,爸妈回到上海。上海的家我住过四年,房子位于法租界,很大也很漂亮。二妹陪容也就在此诞生。
举家刚到香港时,居住的条件并不好。记得在西摩道三楼,是我们立足香港的第一个家,共有四间房子,爷爷奶奶一间,爸爸妈妈一间,我们姐妹们住一间,姑姑们住一间。
一般人觉得老大责任感重,因而没有排第二、第三、第四的轻松观点。但我觉得做人做老大也有相当的安慰。
确实,论聪明,论长相,我在四姐妹中都不突出,细想想,只因为我排行老大,长女的身份,确实更多地抓住了爸爸的眼球,妈妈曾告诉我,她和爸爸婚后七年才生下我,难怪爸妈对我特别疼爱、特别关心。
记得自从有了妹妹后,不论我是三四岁的孩子,还是上小学后,爸爸对我最常说的一句话:“你是老大,是大姐,事事都要成为妹妹的榜样。
记住,‘长女要第一’,你做得好,妹妹们也学好,你做得不好,影响妹妹学坏,那问题就严重了,知道吗?!”
真的,“长女的责任感”,从我懂事起就不断被灌输、加强,于是,几十年来,早已成了我做一切事的前提!
爸爸的眼光总是超前的。往往,人走在当代,他的眼睛却总看清远方,总是把世俗观点远远地抛在身后。
20世纪初四五十年代的世俗观念,尤其是宁波人的观念:男子传宗接代、成家立业;
女儿无才便是德,嫁汉要服从丈夫,媳妇亦要等男人吃完才能吃,女子衣服更不能与男子衣服一同洗。
爸爸的观念不同!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中学毕业前一晚,爸爸对我说的一番话:
“陪陪(我的小名),在这个世界上,男也好,女也好,都要学会用自己的双脚站立,都要经济独立,一辈子不要靠父母和家庭背景,不要依赖丈夫和别人。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多读书,努力学习和积累知识,好独立谋生。因为你是老大,对你就要更严格一点。”
那时,爸爸还只是与上海来港的四五个朋友开设一家很小规模的贸易公司,在家的时间相对多些,每天回家的时间也早些。
于是,每天下班后,爸爸第一件事便是检查我的作业。
他耐心地听我背书,一篇课文,无论是背漏或背错一个字,他便非常认真地说:“老大,你再默读几遍。”
遇到考卷没得100分,或者作业本上老师打了红叉叉,爸爸总是先让我认真订正后,再叫我伸出右手,他拿一根木尺,打我的手心,而且总是错几个,就打几下。
有时我委屈地掉着泪嘟囔:
“爸爸,我这次在班里考第二名,为什么还要挨打?!”
“记住,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对你的要求,都是争第一!”
回想起来,恐怕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挨过爸爸打手心,当时手心真的很痛!
记得我曾举着红肿的小手跑到妈妈那里,妈妈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妈妈很心痛,她捧起我的手轻轻吹了吹,深深叹了口气:“陪庆,爸爸的话都是对的,都是为你好,因为你是老大,一定要成为妹妹的榜样,你要不想爸爸再打手心,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爸爸妈妈口径一致,使小小年纪的我,没有了撒娇钻空子的可能,只有加倍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争取第一!
确实,手心疼痛很快消失了,但是,爸爸妈妈事事要我“争第一”和“大姐必须严格”的要求,却在我心中牢牢扎了根,成了自己终生的标准。
2.与打牌、搓麻将终生为仇
记得小时候,我们还与阿爷阿娘(宁波人称祖父为阿爷、祖母为阿娘)住在一起时,我们家的客厅里经常摆开麻将桌,阿娘和她的朋友们,你赢了,我输了,又说又笑,常常玩到深夜。
爸爸对阿娘非常孝顺,当面从没说过什么。只是不准我们孩子在旁边看。
有一次,爸爸帮助我检查作业,听着外面稀里哗啦搓麻将的声音,长叹一口气对我说:“爸爸是最恨打麻将、打牌这种游戏了,又浪费时间,又会耽搁事情,尤其是赌钱,真害了不少人。”
“耽搁什么事?”我奇怪地反问:“阿娘成天没事待在家里嘛,根本谈不上耽误事啊。”
爸爸皱着眉头,陷入了回忆:“记得我小时候,从学校放学回来,一进院门,就听到堂屋里搓麻将的声音。进去一看,你阿娘手里搓着麻将,用脚推着你两岁小姑的摇床,你小姑在哇哇地哭,她也顾不上抱!‘玉刚,你回来了,正好抱抱妹妹!’我闻到一股焦煳的味道,就问你阿娘:‘亚姆(宁波人称妈妈为亚姆),是什么东西烧糊了?’‘老天,一定是饭烧煳了!’你阿娘打麻将正在兴头上,不愿离开桌子,就对我说:‘玉刚,你去替亚姆看看!’我揭开锅一看,雪白的大米饭全糊成黑炭了!只好全部倒掉,再淘米,重新煮饭!那一天,我们全家很晚、很晚才吃上饭!当时我便在心中暗暗发誓,一辈子不打牌,不搓麻将!将来也绝不让我的妻子、孩子打牌、搓麻将!”
我知道,爸爸一辈子确实是做到了,无论是他看到亲戚、朋友中谁打牌、打麻将,他都会劝人不打,建议对方做些运动、看看书等更健康的活动。
其实,除了爸爸,恐怕家里谁都知道,与他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妻子、我们的妈妈却一直打麻将。
我们当女儿的都能理解妈妈:妈妈不爱交际,不爱逛商店,文化又不高,没什么嗜好,只想与几个老同乡搓搓小麻将,过日子罢了,完全不在乎输赢。所以也不敢向爸爸投诉。
但妈妈也非常了解爸爸,知道他一日辛苦工作回家,需要安静。一到五时半,无论输赢,妈妈一定放下手上的牌,撤掉麻将桌,送走朋友们,让家里一切恢复正常。如果是在朋友家里打麻将,时间一到,她也一定告辞,赶回家中。
所以,无论爸爸六时回家,还是七时进门,妈妈总在家里等候。爸爸也未必不知道妈妈搓麻将,但见她始终掌握着分寸,不因此误事,也不过分,便也不再苛求什么了吧。
妈妈是个典型的宁波媳妇,不仅节省勤俭,更是个贤惠孝顺的女性,孝父母,孝丈夫,孝子女,孝外孙。吃饭时总是让家人先吃,如菜有余,她才开始自己吃,所以吃得总比其他家人慢。她是一位保守的贤妻良母,只是为丈夫,为儿女而活,一辈子是顺着丈夫之意,使他没有不高兴的地方,永远是坐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静静等候。
3.做人要正直、勤俭、富有同情心
记得有一回,七岁的我坐在饭厅里与父母用餐,刚好阿姨(从上海带来的阿姨)进厨房去了,我学爸爸拍手呼叫:“阿英,阿英!”
“叫阿姨干什么?”刚从房里走出来的爸爸很严肃地反问我。
“你有脚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自己不走进厨房?!
你是人,阿英也是人,她年纪比你大,比你干得更累。你小孩子,没有资格差使工人!知道吗?要有同情心,要了解他们的辛苦。阿英的丈夫离开她和孩子,使她为了生活,只能离开儿子做家佣。”
“知道了!”我答应着站起来,自己进厨房去盛了一碗饭。
这位阿姨叫舒翠英。1946年,她31岁那年到我们上海家中工作,1948年,是她抱着二妹和我们一家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当时我们刚到香港做新移民,爸妈也幸好有阿英帮忙做家务。
阿英为人老实简朴,只食素,忠心耿耿在我们家做了三十余年,带大了我们四姐妹。
阿英也是宁波人,妈妈非常信任她,爸爸从来没有说过她的不是。她唯一的儿子在宁波乡下,常有来信。阿英不识字,信都是我读给她听的,也总是我替她写回信(直到1972年我出国留学之前)。她儿子信中提到的都是多么思念妈妈,多么想尽孝心,让年老的妈妈安享晚年的话。阿英感动得直流泪,执意要回去看儿子,爸爸妈妈和我们四姐妹怎么留也留不住,只好放她回大陆。
结果她回到上海,多年存的钱都被儿子骗去,后来,儿子也不幸染病身亡,阿英只有与她老姐姐相依为命。
至今,我们姐妹无论谁到上海,都会抽空去看看阿英,和她聊聊家常话,也尽力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另一位家中不可少的是爸爸的司机老李,他是天津人,从上海时就跟爸爸,到香港后,他也没成家。每天驾车送我们上学。往往我因怕同学们看见我坐车上学,过意不去,便叫老李离开学校两条街就放下我,自己步行上学。
老李退休后,爸爸一直安排照顾他的吃、住和医疗保健,直至他去世,他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家。
我们家里四姐妹,无论在家境平平时,还是家境优越时,从来不知道浪费为何物。不许挑食是妈妈定下的规矩,家里上顿吃不完的菜,绝不允许倒掉,妈妈第二天会自己吃。
直到1983年,我从来没回过宁波老家。在我稚嫩的心里,宁波仿佛是“咸”和“穷”的代名词。每当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我心里总是暗暗庆幸:阿弥陀佛,幸好我是香港人,我的筷子永远不用直“笃”那些咸极了的腌制品!什么臭豆腐、臭冬瓜,什么咸菜、咸虾酱等,都是小孩子不爱吃的。真不明白为什么祖母、妈妈却当作宝贝。
宁波人节俭,称为“做人家”。从小就听祖父母、妈妈说:“要‘做人家’,我们宁波是很穷困的,食物不可以浪费。”
一个没有资源的浙江省,全靠头脑和双手干活,勤俭,是必要的。宁波市的穷困,可以想象的,基本是一家大小都吃不饱的日子多。也难怪那么多宁波人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位于海边的宁波,盐是不缺乏的,以盐来防腐,放在海鲜、蔬菜里,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是环境所致。
妈妈从小教导我们要“做人家”,我们的衣服大多数是她缝纫的,连毛衣也是她亲自编织的。我曾问妈妈从哪里学来,她说:“自己学,自己看嘛。”妈妈可真聪明,一看便会。她的创作力可强呢!我穿过的衣服传给二妹,二妹穿过的给三妹,三妹穿过的给四妹。可怜的四妹总是穿最旧的衣服。难怪她现在穿得最新潮。
妈妈自己从不丢弃东西,无论是漂亮的盒子、丝带,她都留下来,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废物都能利用。普通纸盒被她用花纸一包,变成优雅的器皿,用来放麻将的筹码;旧窗帘被她一剪一缝,变成别致的供旅行用的高尔夫球套。妈妈为我们做衣服,自制购物袋,补袜子,旧物改新物,现代的环保意识在妈妈的日常生活中早就实行了。
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回到宁波老家,以后回去次数越多,越深刻体会到故乡人的真感情。宁波人直接、爽快、热情,也越能理解爸爸那种“儿不嫌母丑”、“月是故乡明”的深情!
在节俭上,宁波人不光吃得节省,穿得也十分俭朴。
记得我上初中时,看班里有的女同学脚下的皮鞋经常换,今天是红的,明天是黑的,鞋样子也十分新潮。晚上回家,我走进爸爸的书房,对正看着报纸的爸爸说:“爸爸,我要买双皮鞋。”
爸爸头也没抬,语气平静地问道:“告诉爸爸,你脚下穿的是什么?”
“是鞋呀!”
“有鞋还要买鞋?”
“可我们同学有好几双皮鞋嘛!”
“记住,鞋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摆阔的,有鞋穿就不用买鞋!”
爸爸是说到做到,他自己也非常节俭,一直是穿一件补过好几次的破旧毛巾浴袍去游泳。虽然衣柜里放着好几件朋友和女儿买给他的新袍,他都不穿。他说:这旧袍又随意,又轻便,又舒服。
妈妈常说,穿补过的衣服,只要干净并不丑,只有穿不干净的衣服才丢人。
妈妈自己从不穿什么名牌,能省的地方,她都十分节省。
妈妈的手也灵巧过人,她自己买了新布,找了样子,在家中,她用缝纫机车,只用了一个下午,经过妈妈的手,点石成金,一下便成为我们姐妹合体的新衣服,旧布就做成睡衣、睡裤。
妈妈又亲手织了毛衣和毛裤给我们穿,这也是为了省钱吧。但我们姐妹们也都感受到妈妈每针的慈爱、每线的温暖,觉得比买来的更有意义。后来妈妈又织毛衣给孙子女。
身教重于言教,更胜于言教。
因为爸爸、妈妈自己做得好,也严格要求孩子。我从小就对像阿英这样的普通底层大众充满真情,不是俯视的施舍,而是真正把他们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下决心长大后,要为大众、为社会尽力做事。因为社会里有很多像阿英、老李这样的人,默默地付出贡献,我的舒适,来自他们的劳力。回报社会,是我的责任。
记得是1963年,一个炎热的夏天,英国和记公司英国老板的太太Lady Clague带我去观看香港穷人住的木屋区,位于铜锣湾。
其中的一幕令我永远难忘。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父亲在工厂干活失去双手,母亲也要外出打工。女孩背着瘦小的弟弟,肩上挑着两小桶水,她右手扶着肩上的担子,左手还拉着三四岁的小妹妹,赤着脚,喘着粗气,爬上山路回家,还要给一家五口煮饭吃。
这就是香港20世纪60年代的木屋区。一般山上没有水电供应,更不用说卫生设备了。当时香港没有禁止童工的政策,也没有规定儿童必须受教育,也没有劳工保险,父亲一旦工伤失业,生活顿失依靠,于是母亲也要外出工作,留下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
香港穷苦市民的真实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也开始对社会工作发生兴趣,想着如何去改革社会,缩小贫富间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