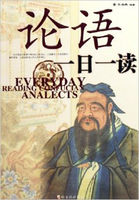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浙江海宁人,着名武侠小说家、社会活动家、报人。1941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院外交系,1947年考入《大公报》,做译电员。1948年随《大公报》到香港。1952年《新晚报》复刊,调任该报副刊编辑,曾以林欢为笔名,在副刊上开设“下午茶座”。1957年,加盟长城电影公司,根据郭沫若《虎符》改编的第一部剧本《绝代佳人》曾获文化部金章奖;此后又导演了《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两部电影,还发表若干历史评论、散文、翻译作品。
1959年创办《明报》,1967年创办《明报周刊》。90年代还曾加盟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1955年,他首次用“金庸”的笔名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获取成功。到1972年10月24日《鹿鼎记》连载毕宣布封笔,一共写了《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越女剑》等十五部武侠小说,其中十四部被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经发表,即引起很大反响;小说风靡全球华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金庸热”,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突出的表现有以下四点:首先是持续时间长,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金庸热”五十多年长盛不衰。其次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小说读者不但在港澳台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此外金庸小说也被译为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再次是金庸作品带来很多的衍生品,除了文学作品以外,其武侠小说还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等;而且每次的改编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最后是其读者的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
很多研究者对金庸的小说作了极高的评价。冯其庸在《金庸研究》前言中说:“古往今来,情节之离奇变幻若此,而又真实可信引人入胜若此,创作之长篇巨论而又精警出尘若此,恕我见闻鄙陋,觉得就古今小说来说,还无第二人。”章培恒先生认为金庸小说成就要超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写了近十部金庸研究专着的陈墨先生认为:“金庸的小说与《石头记》(《红楼梦》)同属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作品。”他认为金庸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北京大学于1994年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在授予仪式上,着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教授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
伴随赞誉声而来的是一批学者文人的批评,他的小说被斥为精神鸦片、四大俗、总体格调不高,等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金庸的武侠小说研究、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王朔看金庸、金庸被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士生导师等事件,文坛内外掀起了一阵阵“金庸评论热”,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乃至为人、学养、道德、学问都进行了轮番评论。
第一节“金学”与江南传统
1985年,张放在《克山师专学报》第4期上发表的《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第一篇金庸研究论文。1986年,红学家冯其庸认真评述了金庸小说广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为“金学”是有道理的。1986年底,在深圳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有李云扬《评金庸新式武打小说的艺术魅力》等,可以说这是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论文首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研讨会上。1991年,大陆研究金庸的专着开始出现。陈墨可以说是最早的金庸研究的专家,他的《金庸小说赏析》是大陆第一部金学研究专着。陈平原在1990年就开设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相关课程,专着《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准备和写作时间从1989年夏秋到1990年底。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同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严家炎自1995年起就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两家权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有关金庸研究的长篇学术论文,《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推出了金庸研究专刊,1997年6月杭州大学金庸研究中心召开了“金庸学术研讨会”,在学术层面上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这些事件标志着我国大陆学术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199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彼得校区举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庸开始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关于“金学”的问题,学者朱国华显然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将金庸研究冠之以‘金学’的美名,与其说反映了学者们开辟一个伟大学科领域的雄心,倒不如说是将商品社会推销商品的包装策略移用到严肃的学术研究上,以图产生广告效应。”他将金庸研究和鲁迅研究进行了对比,“一位武侠小说家所写的小说,是否能带动一门学科的建立,在作出肯定的答复之前,我们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急急推出招牌来,而是先要看看自认属于金字招牌下的货色如何。很遗憾,姑且不谈质量,即便只谈数量,把包括《点评金庸》之类的专着都计算在内,金庸研究的专着至今也不会超过二三十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鲁迅研究。自二三十年代至今,专着、论文汗牛充栋,不知几十倍几百倍于《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有自己吸引了无数精英人才的鲁迅学会,有高质量的《鲁迅研究月刊》,可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从来没有呼吁过要将鲁迅研究升格为‘鲁学’。”朱国华将鲁迅与金庸研究着述的多寡来评判的说法当然可以讨论,但他对武侠小说研究能否带动一门学科的建立的批评却不无一定的道理。
毫无疑问,一门学科的建立当然与研究者及研究成果的多少有关,但最关键的,我们认为还是在于这门学科能否顺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绽放出新的生命力,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并且融合一些新的东西。金庸小说研究能否成为“金学”,关键在于金庸的小说能否提供这种资源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否融合新的学术潮流。金庸武侠小说中许多门派,比如“金乌派”、“雪山派”、“古墓派”、“明教”等等,这些门派的创立并不是以人数的多寡来确定的。金庸从中体现的武学思想也是不论尊卑,而是彼此平等,强者不能欺凌弱者。武侠门派当然不能和文学研究相提并论,但是文学研究中对“显学”的过度阐释也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武侠小说等大众通俗文学研究在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通俗文学思想性、文学性等方面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对所谓雅文学的刻意追求有关。所以,我们认为,对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既不能过度拔高,也不能嗤之以鼻,应该抱持一种理性的、宽容的态度。
与严家炎称其“在文学领域发动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同,更多的论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文本研究、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影响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面对金庸小说进行肯定。陈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分文化知识录与文化精神论两大部分,分门别类地将金庸小说中的史、地、易、儒、佛、道、兵、琴、棋、书、画、花、酒、食、俗、功利、侠盗、忠孝、智愚、汉夷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精神进行了阐释论证,从总体上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对金庸武侠小说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陈平原写道:“在20世纪的中国,佛、道因其不再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而逐渐为作家所遗忘。除了苏曼殊、许地山、林语堂等寥寥几位,现代小说家很少以和尚、道士为其表现对象,作品中透出佛道文化味道的也不多见。倒是在被称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中,佛道文化仍在发挥作用,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致可以这么说,倘若有人想借文学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王一川则说:“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极深的意义。
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韵有了重新构建,而且作品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他与别的武侠小说作家不同,靠的是文化。”冷成金则更进一步,他说:“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喜爱并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是由其内在的品质决定的。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在金庸小说中有很多武功路数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解说的,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降龙十八掌”直接从《易经》中转化而来,《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六脉神剑”和中医人体经络学说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吴秀明、陈择纲认为:“而金庸则不然,他不仅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非凡的智慧,将中国文化最精妙重要的儒道释各家许多关于人生理想观念的东西和气功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化入武功描写之中,还与主人公独特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存生命感受结合起来。”
行文及此,我们有必要宕开一笔,对金庸武侠小说与江南文化之间的关系略述一二,以便将上述问题的探讨再推进一步。从总体上讲,江南文化可视作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潜在文化因子,它对小说创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苏联美学家卡冈认为艺术对文化有两种主要功能:一是成为文化的自我意识,二是成为每种具体文化在同其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密码”,代表它所归属的文化,并向其他文化的代表揭示这种文化。作为艺术重要门类之一的小说有揭示文化“自我意识”、解开文化“密码”的优势。对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密码”的表述实际上已潜在规定了文化的可区分性与地域特征。那么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他是如何揭示江南文化的“自我意识”与“密码”呢?
金庸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流入东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桕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射雕英雄传》)
在这段话中,金庸不仅点出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大致的时段,而且以一种信手拈来的笔调将钱塘江畔的江南风景徐徐展开在人们面前,这在以前的武侠小说中是很少见的。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中几乎都有很多对江南风景的描写,在金庸的笔下也有很多对大漠风光、南疆北域的描写,但读起来总没有他笔下的江南风景那么贴切,那么自然。如下面这段对海宁观潮的描写: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
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海宁人,对海宁的钱塘潮自然是非常熟悉,即使是身在香港。可见他在书写下这段文字时,是怎样情不自禁地引发了浓烈的江南情怀;只有如此,他才会写得这么贴切而有气势。这种景物是非熟悉之人、非江南文人所能写的。在这里,景与人合一,景与情交融;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绝对分开,也不可能分开。
除了对风景的描写之外,金庸更着力表现的是江南民情和风俗:便是此时,只听到欸乃声响,湖面绿波上飘来一叶小舟,一个绿衫小女手执双桨,缓缓划水而来,口中唱着小曲,听那曲子是:“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滩,笑脱红裙裹鸭儿。”歌声娇柔无邪,欢悦动心。(《天龙八部》)
乾隆命坐舫划近看时,见灯上都用针孔密密刺了人物故事,有的张生惊艳,有的丽娘游园。更有些舫上用绢绸扎成花草虫鱼,中间点了油灯,设想精妙,穷极巧思。乾隆暗暗赞叹,江南风流,非北地所及。(《书剑恩仇录》)
段誉进入江南第一眼见到的江南风情就是采莲女子划着小舟,唱着采莲曲,江南柔和、婉转、清新的形象立时展现。而硖石灯彩始于唐,盛于宋,已经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它以细巧精美见长,在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灯纸上需用针刺五十余孔,被称为“江南一绝”,具有非常浓厚的江南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