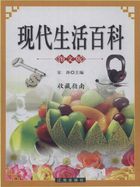上面指出《探源》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考证,但它并不以此为限。它指出:“使人家破人亡的淫妇式的女角不会在小说(指《金瓶梅》)中占有地位。这样的角色只能见于《水浒传》或短篇话本中一些比较简单的外表的性格描写。试图了解潘金莲的行为,特别是她用以表达她的极端孤寂情绪的那些词曲,在小说开头,一个全然不同的典型性格就已经在作者的心中形成。”它又说:“《金瓶梅》比它以前的现存小说在叙述上具有更严密的组织。”“如果说《金瓶梅》是女祸故事,那小说是无可挽回地铸成大错。但那不过是用来和作者所创造的新型小说遥相对照而已。新型小说要求对人物有更加细致的描写,比起旧式小说应该是另外一种细致。”所有这些都表明,论文作者把《水浒传》和其他话本小说作为原有的旧式小说,而《金瓶梅》是以心理描写见长的新型小说。前面说,《金瓶梅》的个性和个人心理的描写特别和西方思潮合拍,是它易于为西方接受的原因之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封建时代中出现的个性和个人心理的描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加以肯定。从小说发展史上看,《金瓶梅》的写作技巧比《水浒》有所提高这是一回事,《金瓶梅》是否在总体上超过《水浒传》
那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宜混淆。说《金瓶梅》的写作技巧比《水浒》有所提高,并不排除在另一些方面如典型化的深度又可以不及《水浒传》。《金瓶梅》第八十七回武松诱骗潘金莲和他成婚,从而在洞房之夜杀死她,同以前所写的英雄性格不调和。这还不过是易见的较小的瑕疵。《水浒传》对中国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所作的深刻反映以及它反过来对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所起的深远影响决不是《金瓶梅》所能比拟,而这种影响正是属于全民族的伟大作品的重要标志。
我看到《金瓶梅》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采用李开先《宝剑记》传奇第五十出,韩南教授还找出其他几个片段;同时我又注意到李开先《词谑》评论元代各家杂剧,全折引录,不加贬语的只有十几套,其中就有小说第四十一、七十一回分别全文引录的《两世姻缘》和《龙虎风云会》的两个第三折。这些事实说明《金瓶梅》作者对元代杂剧的看法和李开先的评论十分接近。此外还有其他迹象促使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后来逐渐注意到《金瓶梅》所存在的种种明显的疏漏和缺陷,如小说第十九回和第五十二同居然有一半相同的少见情况等,我在论文《金瓶梅成书新探》中把结论修改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只有他本人或他在戏曲评论和实践上的志同道合的追随者,他们可能是友人,或一方是后辈或私淑弟子,才能符合上述情况。”“从上述以及不胜备述的众多错失看来,《金瓶梅》的写定者如果是一般的明朝文人或名流,那他主要是发起刻印此书,作了一些修订,但并未始终如一进行彻底的校改,大体上仍是他所见的原有稿本(此书前半部的加工程度显然比后半部为高,本文所举失误的例子以后半本为多就是证明),或他颇费心血的写定本又被后人窜改成现在的样子。
另一可能是写定者接近书会才人,是社会地位低微、科举不得意的文人,他或他们并不具有较高的文史修养和文字写作水平,以致文字上疏失甚多。”这是我和韩南教授的第一个分歧。他认为《金瓶梅》多处引用李开先的《宝剑记》同小说的作者问题无关。
韩南教授如此详尽地列举了《金瓶梅》所引用的小说、话本、清曲、戏曲等资料,不可能不想到一个问题:作者有什么必要这么做?他在结论中指出:“我们注意到作者有时要有相当长的创作才能将某较早作品的片段引进正文。有时作者只是为了微不足道的描写、人物和事件的细节而求助于早期作品。有关之处极为微细,为了前后衔接又需要费尽心思。常常是这样情况,自己撰写反而更简捷可行。”然而作者毕竟是这样不惮其烦地东摘西引,这到底为的是什么呢?韩南教授没有直接回答,但也并不回避。“作者仰仗过去文学经验的程度远胜于他自己的个人考察”,这是他的第一条结论。对此我不敢苟同。尽管“小说没有一个部分没有引文”,事实是所有这些引文都不是《金瓶梅》的主体,即《金瓶梅》之所以成为《金瓶梅》的主要成分。
即使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塑造曾得到《如意君传》中武则天形象的启发,一个是简单、粗糙的仅具轮廓的人物;一个是有着整个复杂心理和丰富个性的艺术形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又在第二条结论中说:“作者开拓了为读者、不为听众而写作的小说领域。”“小说的特点在于接受如此众多的来源,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与其说它适应早期作品,不如说它超越早期作品。”我认为《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开创性贡献有二:一是世俗中的普通人物从此成为长篇小说的主角;二是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打破单线发展的型式,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到此成熟。
《金瓶梅》“接受如此众多的来源”,对它的上述成就很少有积极作用。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在前人启发下所完成的独创性的描写,而不是它所引用的那些片段。《金瓶梅》如果“开拓了为读者、不为听众而写作的小说领域”,那是它本身的描写,而不是它听引用的那些清曲、戏曲以及其他说唱形式,它们只能使听众发生兴趣,却不会使读者感到满意。韩南教授只看到别的作品引进《金瓶梅》的事实,他没有想到也有相反的可能,或它和别的作品都从第三者引进的可能(他曾提到后一种可能,但未予重视)。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作《再论栀水浒传枛和栀金瓶梅枛不是个人创作》,这就接触到我和韩南教授的第二个分歧,他认为《金瓶梅》是个人创作,我则认为他的审慎客观的考证恰恰和他的看法相反,它们为《金瓶梅》世代累积型作品说提供了更多的例证。
韩南教授指出:“《金瓶梅》所用的《水浒传》版本现已失传”;“就《水浒传》、史书和话本而论,他(《金瓶梅》作者)无疑得之于抄本、印本或阅读以上本子之后的记忆”;“从它(《宝剑记》)的印本和小说引文的许多微细出入,有迹象表明《金瓶梅》的引文来自实际演唱”。以上事实,我认为与其说是“作者常听演唱,甚或自己也唱,因而默记在心,足以信手写出”,不如说它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更为恰当。
我钦佩韩南教授博洽、明辨的考证,正因为如此才乐于利用偶然的机遇翻译他的大作,并不揣冒昧提出以上商榷。《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它是个人创作抑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看来不会很快取得一致。可以肯定的是,《金瓶梅探源》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必将有助于问题的最后解决。
华裔学者是海外汉学家的重要组成之一。他们既要精通所在国的语言,在文化上和当地人融合无间,又要在研究领域中和国内学者争一日之短长,难度之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由于他们的主观经历以及众所周知的种种复杂情况,他们和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和误解。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四个现代化和开放政策的执行和贯彻,彼此间的关系正在日益改善。从根本上说,华裔学者必将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者。无论对他们的故国和他们所归化的国家都将作出只有他们才能作出的贡献。本书选了他们的三篇论文。他们已在国内(大陆)发表的论文,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了。
郑培凯教授是华裔学者的后起之秀。按照国内的习惯看法,他正处在人到中年之初。他的论文《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习尚》所涉及的范围极其明确而有限。在它之前,戴不凡先生看到《金瓶梅》多次提及金华酒,遂以为小说作者是金华兰溪人,以为兰陵即兰溪;张远芬先生主张《金瓶梅》作者是峄县贾三近,因之把金华酒作为兰陵酒的别名;台湾魏子云先生则以为北方无黄酒,而金华酒是黄酒。同一种酒,因各人手法不同,天南地北,随意附会,使人莫衷一是。郑培凯教授的考证可说小题大做,无一遗漏。他统计全书写明酒的品种的场合共五十三处,都在第十五回之后。他指出西门庆喜欢品尝不同酒类,同他玩弄女人喜新厌旧的习性有关;书中几次写到烧酒的场合都和潘金莲、王六儿这两个情欲特别强烈的女人有关。这就把酒的描写和人物塑造联系起来。论文作者引证多种明代记载,全面地考证了当时人饮酒习尚,指出:“我们若考虑到金华酒在嘉靖年间在北方最为嘉尚,而万历年间三白酒风行,南方士大夫对金华酒多有贬辞,那么,对书中盛称金华酒可以得到如下的解释:本书描述嘉靖年间北方人的饮酒习尚真实准确,而这种习尚不适合万历年间的南方习尚。”论文对《金瓶梅》成书的年代和地域提供了确切有据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