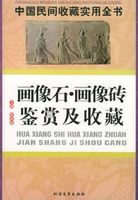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可以看到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的记载,英国工业革命由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引起。中国无论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和后代各式各样的“奇技淫巧”都不可能掀起一场工业革命。
史学家把资本主义萌芽安在中国历史的身上,早的在唐宋或宋元,迟的在明清。引经据典,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作为门外汉,我却难以想象萌芽可以长达数百年以至上千年之久,既不黄萎,又不成长。
我不想走向极端,只要对欧洲的封建社会和我国的封建社会都有如实的理解,封建社会这样的词汇还是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问题。两者的同和异都是客观存在。只看到同的一面而不看到各自的特征,这是要不得的;同样,只看到各自的特征而对两者的共性视而不见,也并不恰当。
三、汤显祖和东林党的异同
清初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案》卷五八至卷六一以四章篇幅专门论述东林学案。他深有感叹地写道:“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
顾宪成于万历二十二年以吏部文选郎中廷推内阁大臣人选忤旨,削籍归无锡。十年后,东林书院重修完成,才在这里聚众讲学,议论朝政。
而上文所说的那些大事至少有一半发生在东林书院重建落成之前,有关人士也并不都是东林人士。试列举于下。
一、首相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称夺情。事在万历五年(1577)。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以及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先后因反对夺情受廷杖,被谪戍罢黜。
二、御史魏允贞上疏,主张内阁大臣子弟春试中式,应待大臣致仕后,才可以参加殿试。魏允贞贬为许州判官。户部主事李三才赞同他的主张,谪为东昌推官。事在万历十一年(1583)。
三、“言国本”,指皇位继承人之争。《本纪》云,万历二十一年,“诏并封三皇子为王,廷臣力争,寻报罢”。三王并封指安妃生的皇长子和得宠的郑贵妃生的皇三子同时封王,皇长子的皇位继承权发生动摇。《明史》卷二三一《顾允成传》所记事实较详。引录如下:三王并封制下,(礼部主事顾允成)偕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合疏谏曰:册立大典,年来无敢再渎者,以奉二十一年举行之明诏。兹既届期,群臣莫不引领,而元辅王锡爵星驾趣朝(据《宰辅年表》,王锡爵今年正月还朝),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勿言,慨然独任,臣等实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锡爵私邸,而三王并封之议遂成,即次辅赵志皋、张位亦不预闻。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议,元子封王祖宗以来未有此礼,锡爵安得专之,而陛下安得创之。当是时光禄丞朱维京、给事中王如坚疏先入,帝震怒,戍极边。维京同官涂杰、王学曾继之,斥为民,及是谏者益众,帝知不可尽斥,但报遵旨行。已而竟寝。
以反对三王并封为主的争国本一案,是顾宪成、允成、张纳陛等后来的东林诸贤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要事件,但它发生在东林书院重建之前十一年。与其称他们为东林党,不如称他们为清议派比较符合事实。
《明儒学案》将他们列为东林学案,首先从学术史——理学学派的角度加以考虑。尽管东林学派同政治斗争关系密切,但毕竟首先是学派而不是政治派别。两者应加区别为宜。这样也就避免了《东林学案》卷首所表示的对东林一词所作的随意延伸的不安。
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以南京为陪都。南京同样设有中央级的各种官署,虽然编制略有缩减。后来一些失意或失宠的臣僚往往安置在这里,南京及其周围各地如无锡自然成为清议派的孳生地。清议派并不在野,至多失败之后暂时或长期在野,但他们又是当权的内阁首相的反对派。《明儒学案》卷五八曾有一段典型的记载:娄江(指首相王锡爵)谓先生(指吏部主事顾宪成)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论亦有怪事。娄江曰:何也?
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相与笑而罢。
区区六品官敢于顶撞内阁首相,不仅因为这是他主管范围内的职责所在,同时也倚恃着舆论力量的支持。
汤显祖在万历五年、八年前往北京参加春试,都因为谢绝首相张居正的笼络而名落孙山,他在张居正去世的次年才中进士。才名大而得意迟,为了世俗的考虑,他在考试时曾隐瞒年龄,将三十四岁改为二十八岁,可见他感到的委屈有多大。汤显祖以海若士为号,借《仇池笔记》的记载,对鳖相公有所讥刺。但要注意:汤显祖对张居正不满并不针对他的政治革新,而是对他的专横作风有反感。张居正身后受到追夺官爵和抄家处分,汤显祖曾特地对他被流放的儿子张懋修致以恳挚的慰问。
三王并封事起,汤显祖恰好自贬所徐闻典史量移为遂昌知县。就当时官场地位升沉的一般情况而论,这是他调回朝廷的一个中间步骤。当时他连普通的一名京官也不是。量移是鉴于犯官已经受到惩处,酌量从宽发落,由边地调任内地。他珍惜调回朝廷的机遇,没有对三王并封事直接发表评论。
他在《论辅臣科臣疏》中曾为首先举报科场作弊案的御史丁此吕、李用中辩护。矛头虽然针对首辅申时行,次辅王锡爵也有同样的被人议论的把柄。高桂、饶伸弹劾王锡爵之子衡顺天(北京)乡试第一,《论辅臣科臣疏》也在弹劾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时捎带了一笔。万历二十一年,汤的至亲好友国子监司业刘应秋来信说,上面虽然有浙江巡抚王汝训和人事主管吏部考功郎中和文选郎中顾宪成的积极设法,他们想得很周到,怕一下子恢复原职难以通过,不妨先调回南京刑部或太仆寺丞,它们和礼部主事品级相同而名声略差,但都未能成功。赵南星和顾宪成本人也被罢官。
不妨提醒一句,王锡爵是三王并封诏书公布前,唯一受皇帝密诏的事先知情者,他因此受到士大夫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批评指责。刘应秋的来信说:
“太仓(王锡爵)甚不喜兄,不知为何?”实际上是上面说的王锡爵不喜欢汤显祖替他的批评者丁此吕、李用中、饶伸等人说话。王锡爵是汤显祖的座师,汤显祖难以对他说三道四。有人以为《牡丹亭》讥刺王锡爵的女儿焘贞,那是主观想象,难以作准。单以应天巡抚周孔教为王锡爵重新返任首相,而在王家上演《牡丹亭》以作劝驾,就可以证明那是无稽之谈。万历三十七年,汤显祖对东林名士丁元荐的书信曾不指名而确定无疑地流露了他对王锡爵的怨毒之深。信说:“(丁的家乡)长兴饶山水,盘阿寤言,绰有余思。视今闭门作阁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汤氏写此信时,王锡爵刚病死,汤氏还没有得到消息。但王锡爵毕竟是汤的座师,私人的意气是有节制的。汤显祖《答吴继疎(仁度)》信中特地替友人王宇泰(肯堂)分辩说:“王宇泰兄学深而行朴。宜相朝夕。彼护太仓(王锡爵)自是师友之情。弟最疾夫卖恩为名者,仁丈以为何如。”
汤显祖和东林诸贤的书信来往,见出他们交谊很深,都以道义为重,却很少涉及党派之争。
汤显祖《与顾泾阳》短简说:
都下觏止,似澧兰之咏公子,山禾之唱王孙。量移括苍(遂昌),每过司理之庭,朱丝冰壶映人心目。天下公事,迩来大吏常窃而私之,欲使神器不神。旁观有恻,知龙德须深耳。
“司理之庭”,指万历十六年顾宪成曾为处州推官。遂昌是处州的属县。
“天下公事”当指三王并封议,大吏指首相王锡爵。末句则希望他斗争不要过分,适可而止。
差不多同时,汤显祖以理学着作《粤行五篇》寄给高攀龙。高攀龙的回信说:“又惊往者徒以文匠视阁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后来汤氏在《答高景逸》书中说:“无欲主静,谈学所宗。千古乾坤,销之者欲。”这是他们双方的接合点,实际上也是当时所有理学家的共识。汤显祖在这封信的结尾,谨慎而明确地表白了他和理学家的分歧:“有欲于世者未必能动,无欲于世者未必能静。”差点没有说出来的是他对假道学的反感。假道学当然不是指他们本人,而是指东林的末流。
汤显祖和东林党的异趋,应该同他和东林党的共识,同样受到注意。
否则,就会给人以错觉。可惜我以前就犯了这样的片面性。汤显祖《与王止敬侍御》的信中提出“君子群而不党”和他共勉:这是中国古代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信条,朋党被看作是坏事。汤显祖对东林党始终是诤友的态度,保持了独立自主的评论态度。他在给同年好友犹龙马梁园的信中说:“泾阳兄书大有义味,而细欠商量,乃致疑然并作。”万历三十八年淮抚李三才被劾,顾宪成从东林书院上书事实上的首相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为他力辩,引起一场风波。顾宪成在《与汤海若》书中感谢汤显祖的批评:“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幸老兄一言判此公案。”三年之后,汤显祖《与岳石梁》(和声)信中谈及此事,一方面为顾宪成说好话,主持公道,另一方面也指出:“凡过处的是泾阳本色,余或未尽然耳。”
汤显祖晚年里居,逐渐置身于官场之外,有些情况他已经不太了解。
他给东林巨子张纳陛的信说:“爰立既新,来誉斯始。文章礼乐,舍门下其谁。”(《与张文石》)爰立指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首相赵志皋去世,十一月沈一贯晋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九月沈鲤、朱赓俱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此信对沈一贯的政治面目认识未清,以为张纳陛有乘时再出的机遇,显得对朝廷人事很不理解。
六年之后,江西参政姜士昌对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和沈鲤以奸忠同罢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是使“浊泾清渭混为一流,后来无所惩劝”,姜士昌得贬官处分。汤显祖才修改了自己的看法。
《明史》卷二一九《朱赓传》说他“醇谨无大过,与沈一贯同乡相比。昵给事中陈治则、姚文蔚等,以故蒙诟病云”。张汝霖是朱赓的女婿,汤氏《问棘邮草》两卷本,署徐渭批释,张汝霖校:张汝霖在江西先后任清江、广昌知县。他和汤显祖关系不错,他通过临川知县,请汤显祖为他的岳父朱赓七十大寿求序。汤氏的谢绝极为婉转,但没有应允。“忽以令君之言,欲为相公之祝,聊以笑小者之为,小制何如大制;岂容代大匠之作,小年不及大年”。这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既不使对方难堪,又不作违心之事。
作为泰州学派创立者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又是汤显祖的老师。
高攀龙盛赞他“邃于理如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汤显祖首先是文人,他不是理学家。他直截了当地归纳了王学的精髓:“性无善恶,情有之。”
(《复甘义麓》)情有善恶,不能全部归之于人欲。因此,他的这封信接着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这样他就在自己所虔信的理学和他的终身事业之间得到平衡。情和理既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关系,也存在着可以统一的一面。
至于汤宾尹和韩敬的科场一案,这是汤显祖晚年和东林党的一大分歧,我想可以从他的超然立场得到说明,他认为以韩敬之才无需作弊,其他浙党、皖党的党派之争,他一概不加考虑。这就接触到真正的汤显祖其人了。